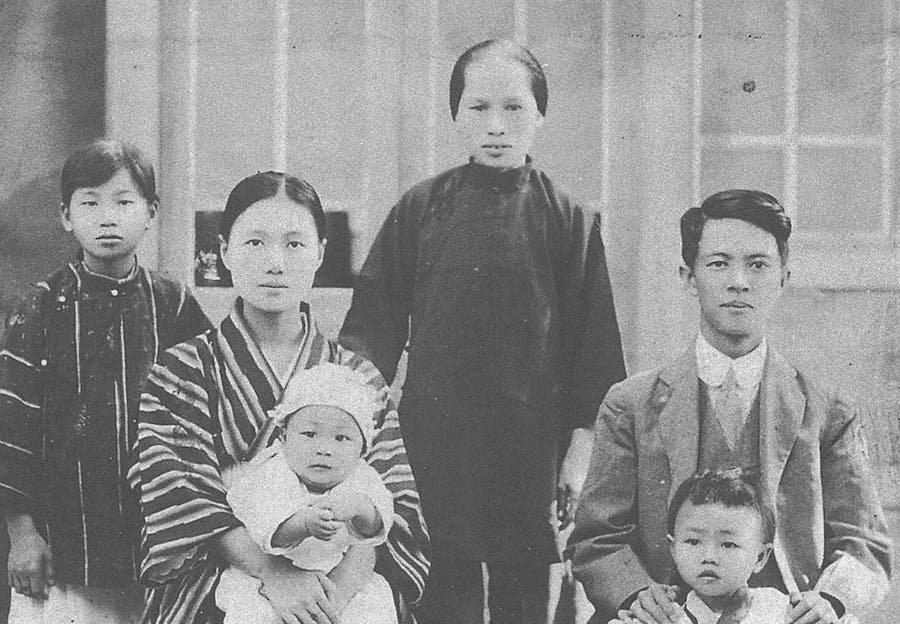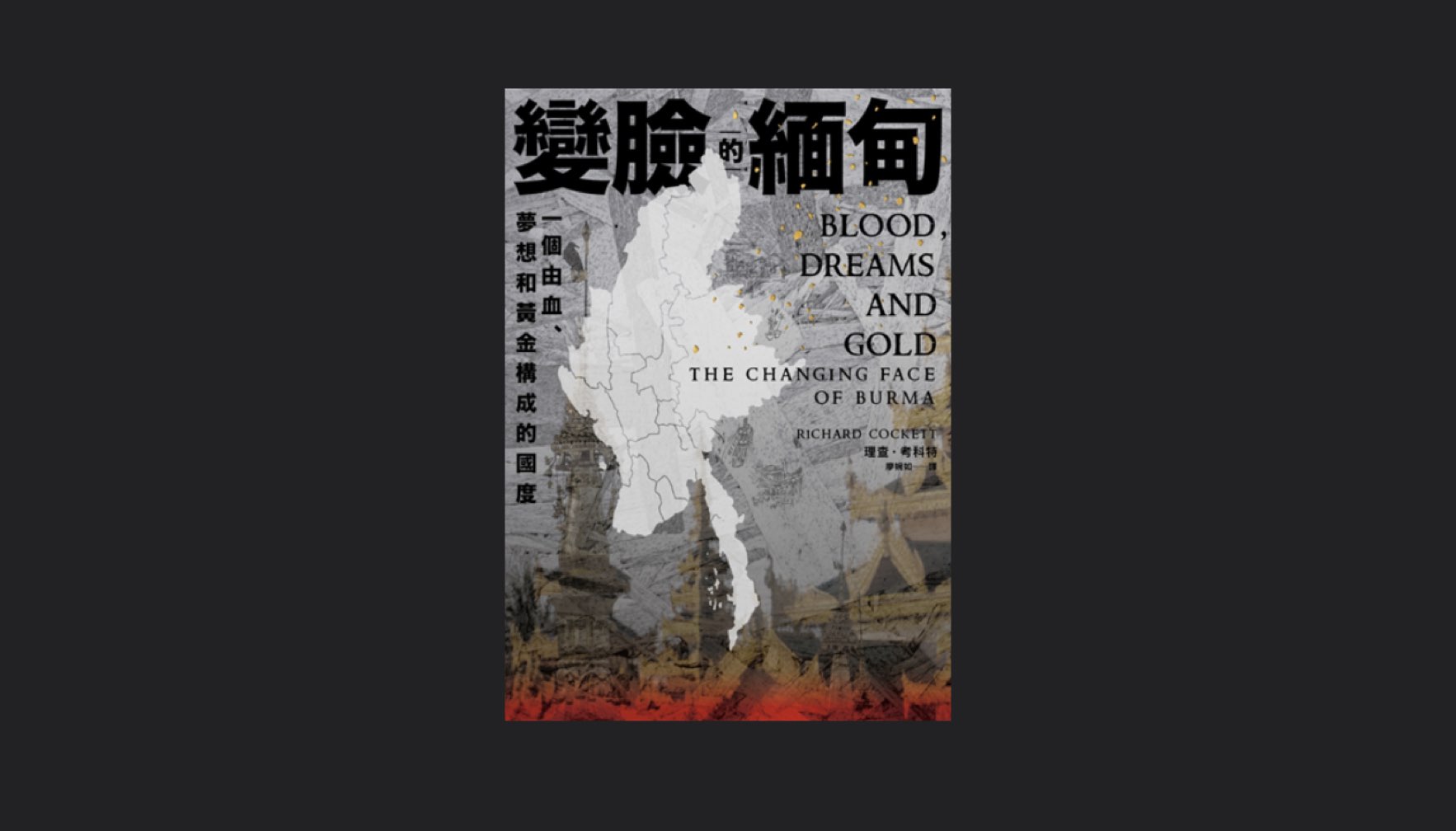這本小書是德里克(Arif Dirlik)過世前一年來到臺灣演講的紀錄,包括五篇講稿和一篇訪談。要說這本小書,概括了德里克各方面的學術成果,以至於「晚年定論」,那是遠遠不夠的。但是透過裡面的兩種聲音,或許我們得以捕捉到他學術工作上最為矛盾,也最為動人的一面。從而知道,兼治中國近現代史、後殖民研究、全球化理論的他,在多產的作品背後,想說的究竟是什麼。
在七十五歲回望既是研究對象也是自身經歷的二十世紀,德里克的講稿與訪談呈現出兩種不同的聲調。在講稿中,如同過去的研究,他將讀者帶入一個深邃的理論迷宮,探討了帝國主義、後殖民主義與全球化研究的根源與流變。那嚴謹的概念分疏與辯詰,近乎一位修行者。另一方面,在「我真討厭講自己的事,太太老抱怨我都不說說自己的事」的訪談裡,我們第一次聽到了這位老頑童的笑聲,言語的機鋒,流洩著風起雲湧時代變遷下的活潑空氣。
講稿使讀者得以在層層觀念與制度構築的當代世界裡,辨認出自己身處的迷宮。訪談則使在迷宮中的我們,想起為什麼踏進來,要往哪裡去。那迴盪在迷宮裡的笑聲,說著,貫穿理論分析的,是對於五十年來世界變化的感慨,也說著,正是這感慨,始終讓他堅信迷宮有著出口。
一、在革命風暴中轉向歷史研究
德里克的研究工作,始於劇烈動盪的一九六〇年代中期。那時,從紐約、倫敦、巴黎、羅馬,到華沙和布拉格,再到北京和東京,在冷戰世界的不同陣營裡,發生了相近的浪潮。二戰結束經過二十年,社會經濟變遷,鼓動著年輕的一代人,對僵固的秩序提出不同意見。
從多年之後返顧,那股不定的風暴,在德里克還沒發現的時候,已經孕育了他將耗去後半生的課題。那既是二十世紀國際革命運動的高潮,也是對革命幻滅的開始。蘇聯的極權統治被揭露後,年輕人質疑著傳統的共產黨路線,但也仍然想像著一個不同於眼前的世界,批判一切霸權。但是,隨著風暴平息,街頭壁壘撤去,青年穿上西裝上班,剩下的只有赤軍等武裝組織與嬉皮公社的實驗。「禁止一切禁止」的無政府主義,用盡一個世代的能量衝擊體制,同時也衝垮了從整體上理解世界的設想。
到美國留學念物理的德里克,在土耳其便是學運領袖,做為這股風暴的同時代人,選擇了一個靠近又隔著距離的位置。如他回憶的,難以確定該做什麼,那就先念個歷史,在這個開放的學問裡,看看自己最後會怎麼決定。這個打算,從不確定開始,走向對確實答案的探求。這使得他與風暴隔著一段距離,避開一口氣改變世界的幻想,也避開了後來的幻滅,而得以在解構的瓦礫裡,尋找仍然擲地有聲的一塊。
「我對中國史完全不瞭解。中國似乎發生了某種大變化,我想搞懂它。」整個一九七〇到八〇年代,德里克投入近代中國的歷史研究。當同時代的西方青年,對中國革命與毛主義寄予天真的無限期待;或許是土耳其學運的經歷,他敏銳地感覺到中國革命的複雜性,試圖把握西方思想理論與中國現實相遇的過程,看見其中的教條與扭曲,也看見其中因應現實、帶給人們真正抵抗力量的創造。
在博士論文《革命與歷史》(Revolution and History)裡,德里克探討了一九三〇年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如何運用歷史階段論來回應國族危機。從奴隸制到封建時代,然後是資本主義,最後是社會主義……來自西方的理論帶給人們信念,透過歷史保證未來,但也帶來困惑,普遍的法則怎麼會跟中國歷史格格不入?商朝和周朝究竟是奴隸還是封建時代,秦朝以下是封建還是前資本主義,現在的中國又走到哪裡?人們提出各式各樣的歷史分期,彷彿都對,也都削足適履。而面對當年革命者留下的材料,德里克並不評斷哪個更正確,他關注的是西方理論與中國現實的差距。圍繞著那差距,他勾勒出一個思想充滿張力的年代,革命尚未定型,人們仍在爭論未來。
《中國共產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中國革命中的無政府主義》(A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田野和工廠裡的學校》(Schools into Fields and Factories),在接下來的幾本書裡,德里克為中國共產革命畫出一幅不同於官方版本的思想史系譜。這條線索揭示著,在中國共產黨成立、走向黨組織的絕對權威一元領導之前,圍繞著無政府主義,曾經有過更開放、更具民主精神的辯論、設想與實踐。在其中,德里克打破了「革命史觀」,同時留下了革命的意義。中國革命沒有帶領人們走進社會主義天堂,但也不只有極權專政,現實的複雜,始終與教條理論與強制權力拉鋸著。而在中共建國過程中,同樣面朝革命,卻被黨國歷史刪去的各種思想,或許有著給今天的困惑的回答。
二、「告別革命」沒有回答的問題
但是,同樣從一九六〇年代的起點出發,中國自身的歷史車輪,以及人們思考革命的方式,在德里克重構中國革命思想系譜之際,卻悄然往另一個方向全速前進。當德里克終於找到能夠說服自己的答案:中國革命不只是那樣,而有著另外的可能性,他卻發現,人們正在忙著告別革命。
一方面,中國政府選擇了市場經濟的改革開放之路,不再想像「改男造女態全新」的人間烏托邦。事實證明,僵化的計畫經濟體制,違反人性的激進政治實驗,並不是歷史的進化。從中解脫的無數民眾,在社會主義國家的邊緣地帶,開始經營自己的生活,迸發出巨大的經濟能量。重新加入世界貿易體系的中國,吸引了大量的外來投資,成為世界工廠。大半個世紀的革命,彷彿不過是一段歷史的彎路,與今後再無關係。
另一方面,做為當年風暴的回聲,後現代主義與後殖民主義,席捲了一九八〇年代的西方理論界。沿著對當代社會的批判,返顧近代世界的形成,學者們說,以啟蒙理性為名的現代化進程,並沒有帶來解放與幸福。相反的,理性計畫從西方中心的視野出發,並不顧及底層、邊緣與異地的人們。文明的名義,只是帶來更大的壓迫與災難。他們不相信宏大的歷史敘事,解構中心與本質,強調文化的多元性質,關注地方社區的生活,強調個別群體的心態認同,推崇雜揉的社會風貌。他們說,帝國與革命從來不像宣稱那般主宰了歷史,人們總是用自己的方法顛覆了當局者的語言。
被捲入近代世界的無數人們,他們並沒有那些菁英宣稱的理想,沒有想過未來的美好社會,只是在世局的變換中,勉力撐住自己搖晃的生活。但是,察覺這點之後,接下來我們該往哪裡去?
在這裡,同樣試圖打破二十世紀歷史目的論的迷思,德里克發現自己的答案,與後殖民主義顯得非常靠近,卻又截然不同。在五十歲,一般學者多半已固定了領域,累積了業績,進入學術生涯的後半場。然而這個困惑,卻使從物理轉到歷史學的德里克,再一次轉換了跑道。整個一九九〇年代,他全力投入後殖民與全球化理論,寫成《革命之後》(After the Revolution)、《後殖民氛圍》(The Postcolonial Aura)、《全球現代性》(Global Modernity)一系列論戰著作。
乍看之下,這些和先前的革命研究愈來愈遠,但當我們沿著訪談,看到德里克人生與時代的交錯,便會發現這是同一條道路。正是為了思考革命留下了什麼,思考第三世界往哪裡去,他必須思考革命在這個時代的被遺忘,意味著什麼。
他提筆寫道:「在近代世界的形成中,肯定歐洲中心主義的歷史作用,並非賦予它權力,而是去認識,它以何種方式繼續參與到當前世界。一廂情願地,從文化對立面予以否定,並不能讓它消失。」
當人們看似從「現代」的壓迫中脫身,尋求自己的天地,早先是一個第三世界國家的學運當事者,然後用了半輩子研究另一個第三世界國家革命的德里克,敏銳地感受到,否定西方中心主義的「現代」文化霸權,跟打破這種文明標準在政治經濟結構上的宰制,其實是兩件事。
他指出,後殖民主義否定中心否定結構,認為那不過是一種假象,雖有一定的批判效果,卻也因此無法進一步分析,在遠較結構複雜的日常生活中,結構怎麼具體產生作用。結果表面上看似基進的批判,反而失去了分析力量:局限於地方社區的變遷,卻無法看到外在結構的影響,複雜的歷史過程,也變成了非連續性的偶然。
更有甚者,在後殖民文化批判取徑下,具體的政治經濟結構失去了理論上的重要性。直到一九七〇年代以前,西方左翼思想中,在「帝國主義」的概念下,文化與政治經濟一直放在一起分析。但到了這時,當做為答案的「社會主義」與「革命」被放棄,做為問題的「帝國主義」,也不再是分析的焦點。
然而,結構問題並非從文化面向就能消解,相反的,在資本與生產的全球化進程中,這些結構前所未有地進入每個人的生活。儘管其中的權力相對關係改變了,權力的基本模式卻只是改換了面貌。東亞強勁的發展,彷彿讓全球經濟關係重新洗牌,西方不再獨霸,各國平等參與到全球經濟中。但這種平等只是各國都有了全球資本主義的進場門票,各國的人們都有機會被跨國資產階級平等地壓迫,而不是構想不同於全球化體系的另一個政治經濟方案。
德里克說道,過去,按照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陣營,全球地圖被分成第一、第二、第三世界,如今上面的線條是重劃了,但壓迫仍然存在。第一世界的大都會裡,有著貧民聚集的區域,第三世界的城市裡,也有著跨國企業的資產階級。但是新的變化卻在新理論的視野裡消失。冷戰時期美蘇的競爭,是兩種現代化方案的競爭,現在各國競爭的卻只是全球資本主義規則下的勝利。先前,在美蘇之爭下隱身的「發展主義」(developmentalism),至此,以一種中立、科學的姿態,成為無可動搖的標準。政治經濟結構的衝擊比過去更為迫切,在新的全球化框架下,這些卻難以分析了。
帶著感傷的語氣,德里克將之稱為「共謀」。儘管並非出於本意,當代基進思想的批判,卻在告別革命的出發點下,與全球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站到了同一邊。那和聲齊唱,每個國家都有同樣的機會建立自己的主體性,卻沒有發現,主體性從來都是在不平衡的權力關係中掙扎而誕生。而當人們與這新的架構發生衝突,他們將發現自己失去了「革命」的選項,再無從開口詢問,那影響他們生活的,看不見的遠方力量究竟是什麼。
三、又來了的德里克,又來的「中國」「歷史」
這樣,走過革命風暴的起落,走過歷史研究與全球化理論,我們跟著德里克來到二十一世紀。
「德里克他又來了,再也不做中國史了。」
在訪談裡,德里克大笑著引用這句話,但也帶著苦笑。這句話既體現了時代的變化,也體現了時代的荒謬。表面上,他的確不再繼續早年的中國革命研究。實際上,他的研究仍然比誰都更關注「中國」與「歷史」。改變的並不是德里克,而是選擇遺忘二十世紀革命歷史的當代中國。
伴隨中國成為全球資本主義中的贏家,在學術生涯最後的十多年裡,德里克兩個階段的工作,重新交會在當代中國上。他批評中國用孔子學院的文化活動在海外推銷官方觀點,也批判中國政府對天安門事件的掩蓋。但這些並不只是接續全球化理論,轉向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也不只關乎知識分子的道德良心。他對當代中國的文化剖析,仍然貫穿著歷史與結構的關懷。從二十歲到七十歲,這些研究一直是一體的。對他來說,只有透過歷史的維度,才能在這個全球化與後殖民的世界,從表面的文化符碼中,看到深層的結構變遷;也只有經由歷史變遷與全球空間,才能試著把握當代「中國」的存在。而這些唐吉訶德式的戰鬥與探索,始終是為了追尋革命在當前的意義。
從對後殖民理論與全球化狀況的反思出發,德里克高度懷疑所謂的「中國特色」。他指出,強調中國特殊性的論調,看似反對了西方帝國主義霸權,標榜文化的主體性,其實是全球化之下,威權政府自我合法化的當代產物。西方學者帶著殖民的愧疚,試圖重新「在中國發現歷史」,卻被第三世界的御用學者拿來粉飾獨裁。對外,文化特殊性並未挑戰全球化的資本運作邏輯,反而渴望在其中獲取利益。對內,這預設了文化的均質一體,反過來壓制不同的聲音,以特殊國情反駁所謂「普世價值」的批評。
他說,這種觀點把文化給實體化(reification),忽略了「中國文化」的主體性並非亙古不變,許多所謂的「特質」其實是建立在與近代西方的互動之中。當「歷史」進程被化約,由官方欽定,成為去歷史的文化本質,那麼過去被宏大敘事掩蓋的個別聲音,便再一次失去開口的機會。與後殖民主義者不同,德里克看到,東方主義並不是西方殖民帝國的專利,也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受到中國政府的歡迎。殖民並沒有結束,而是在全球化的時代由中國政府自己對人民動手。他說,「問題不是東方主義,而是東方主義在不同社會、政治環境中的力量及其具體涵義。」
在此,德里克對當代中國的視角,與流行的觀點拉開了距離。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四不像奇幻動物般的名字,他不否定,也不支持,而是考察這個概念怎麼產生,怎麼運作。他寫道,需要帶回這些概念底下的歷史,需要一種真正徹底的歷史主義。德里克心中的歷史,不是民族國家當權者標舉的整體文化,而是「複雜日常生活中的歷史性」,如果真有所謂的另類現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那將不會源自僵固的文化本質,而來自「充滿現實的每日文化活動的現在」。
當歐美左翼知識分子試圖在中國身上捕捉反美國霸權反資本主義的幻覺,以至於分不清楚社會主義思想與獨裁的中國共產黨;保守主義的右翼學者,陷入文明衝突與麥卡錫主義的恐懼幻象;德里克依然是當年那個初入歷史研究、注視中國問題的土耳其青年,對革命飽含熱情又帶著冷靜,在中國政府、歐美左翼右翼的包圍下,回答道,社會主義與中國都不只是這樣的,告別革命還是太早的事情。
而這一對各種簡化都抱持懷疑,又對拋棄結構分析感到不滿的歷史目光,也許,正是這本小書將帶給臺灣讀者的意義之所在。德里克來臺演講過後的兩年裡,美國選出了川普當總統,中國和土耳其通過修憲,讓現任領袖變成毛澤東與凱末爾之後最有權力的領導人,而二次政黨輪替的臺灣,則在跛足改革的爭議中,從學運的錯覺中醒來,開始感到疲倦。資本全球化的經濟結構日益衝擊一般人的生活,也一天天讓沒有出口的焦慮困惑,在人為操作中湧向封閉保守的政治路線。
在這樣的二〇一八年,我們怎麼理解眼前四散碎裂的思想和文化狀況?怎麼分析各種認同、心態與看不見的結構的關聯?面對從宏大敘事解放出來,卻也失去整體理解的日常生活,重新捕捉其中的歷史性,將文化放回到政治經濟結構來理解,這份德里克未完成的藍圖,或能提供一個初步的答案。
身在臺灣,這個充滿多次殖民歷史的島嶼,我們不斷糾結在各種象徵符碼之間,一邊的人們主張,種種政治經濟問題都來自威權時期的文化遺留,另一邊則爭辯說,空談文化認同不過是狹隘的政治鬥爭工具,拚經濟才是要緊。比起這些,將「臺灣」放回到它的殖民過往,放回到它在二戰後全球經濟生產線的變遷,思考在上面建構的各種公共制度,覆寫在上頭的層層文化概念,或許,我們將能夠找到一個更靠近現實的歷史認識。在這後革命時代,沒有人類歷史發展階段的指引,沒有永遠不變的文化本質支撐,但這從頭來過的工作,或能讓我們看清楚問題:在全球化狀況下,「臺灣」是什麼?我們需要一個什麼樣的「民族國家」?在未定的「中國」與變動的「美國」之間,「臺灣」處在全球政治經濟結構的哪個位置?然後努力嘗試在生活的困惑無力與公共的政治行動之間,連接起有待跨出的那一步。
在這工作裡,我們將會發現,對於這個島嶼,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全球化理論,這些概念剖析並不只是學術遊戲。日常的複雜與歷史的厚度、文化概念與政治經濟結構,總是不斷交會,我們不只是跟著外來的各種主義,而被帶進迷宮的,這個迷宮一直是我們每天生活的現實世界。然後在撕下牆上層層疊疊的理論和概念時,或許你會聽到遠處傳來德里克笑聲的回音,像是說著,這個概念爆炸的時代並不像表面上那樣無從著手,在多年前的中國革命研究裡他不是已經說過了嗎,那後來被稱之為革命的,從一開始就沒有清楚明白的路,正是因為無所依憑,人們才必須往前方走去,看清楚自己在哪裡。
本文作者為臺灣大學歷史學博士

本書主要內容,即為相關的五篇講稿,以及一篇深入專訪,從中不僅可見德里克快人快語的一面,也能看到他學思歷程的幾番轉折:從六〇學運狂飆年代的親身參與者,到七〇、八〇年代的中國共產革命研究者,九〇年代轉而投入後殖民與全球化理論,然後據此進一步分析解釋「後革命」時代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