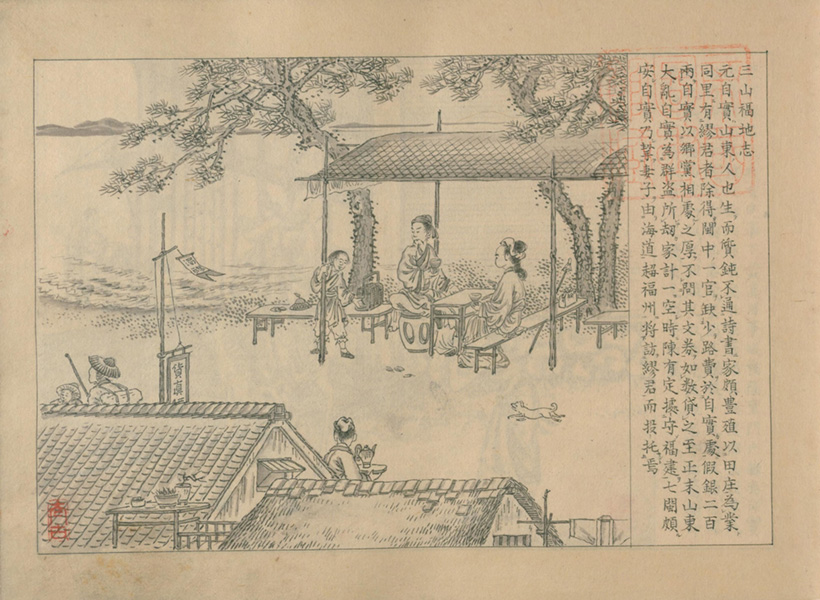從復仇女神到慈善女神
在悲劇作家艾斯其勒斯(Aeschylus)的悲劇三部曲《奧瑞斯提亞》(The Oresteia)尾聲,雅典發生了兩項重大轉變,其中一項對後世來說耳熟能詳,另一項卻常被忽視。
第一個轉變,是女神雅典娜將法律制度引進了城邦,設立法院、以理性論辯與證據程序,藉以取代看似永無止盡的流血報復。她宣布從此之後,殺人罪將由法律解決,不再由復仇女神處理。但後者也並非永遠離開,雅典娜說服她們加入城邦,使她們享有榮譽,肯定她們對法律制度、城邦健全未來的重要性。
後來的人時常將此情節理解為「法律系統必須容納、尊重黑暗的復仇激情」,也就是說,復仇的、應報式的激情依舊存在,只是舊瓶裝新酒,在法律的限制、暗處中蠢蠢欲動。
但這樣的解讀忽視了第二項轉變,也就是復仇女神本性、行為轉變的描寫。在《奧瑞斯提亞》結尾中,復仇女神禁止了所有非必要的殺戮,並宣稱每個人都應關愛彼此,外貌似乎也從原先恐怖噁心(眼睛滴下可怕的汁液、口中吐著嚇人的風),轉變成「挺立前進」的樣貌。從此開始,復仇女神不再是可怖的、野獸般的存在,而成為了所謂的仁慈之人(即慈善女神,Eumenides)。
《憤怒與寬恕》一書的作者瑪莎・納思邦(Martha C. Nussbaum),從這兩項轉變出發,開始了她在這本書的討論。納思邦為芝加哥大學恩斯特・弗洛恩德法律與倫理學傑出貢獻教授,論述橫跨了法律、政治哲學、倫理學領域。其也積極地投入公共議題的討論,如經濟發展問題及性別平等、社會正義與動物保護,皆有所論述。
而本書既可視為納思邦延續其在《善的脆弱性:古希臘悲劇和哲學中的運氣與倫理》的關注,對「情感」價值的進一步探討,也可當作是在《逃避人性︰噁心、羞恥與法律》爬梳人們的噁心、羞恥等情感在法律制度中所扮演的角色、對其造成的影響後,轉向關注「憤怒」、「寬恕」這兩種「情感」的歷史及當代脈絡。
納思邦從艾斯其勒斯的戲劇中得到了靈感:政治正義可以讓個人與公共領域的道德情感持續改變。她也認為,政治正義所關注的不是永遠無法扭轉的過去,而是創造未來的福祉與繁榮。正義體制內的課責(accountability)不應該、也不再是憤怒的、應報的情感,而是為了保護我們對當下、未來生活的評估。
在這個基礎之上,納思邦提出了另一個更深入的主張:「憤怒」在理論層次的討論上是有問題的。(如下文三種道路的討論)她所指的憤怒,在概念上不只包含因為某個人、某事物受到嚴重傷害的情緒,也包含一種想法上的認定──「讓做出不好結果的行為者,承受某些不好的後果」是好的──並將私人領域到公共領域的憤怒,都納入她的分析之中。
除了憤怒之外,納思邦亦討論「寬恕」,因為我們正活在一個「道歉與寬恕的文化」裡,同時,「寬恕」也可能是我們面對壞事、不義之事的態度。在本書中,納思邦檢視當代和歷史上將寬恕視為核心政治價值、個人美德的主張。她問道:如果我們不該憤怒,那我們應該選擇寬恕嗎?《憤怒與寬恕》一書,就是她的回答。
「憤怒」的三種道路
納思邦認為,要「憤怒」通常會走向三條道路:一是地位之道,認為加害者造成的傷害是對被害者、他人的侮辱或貶低,而貶低、羞辱加害者可以回復「地位」;二是償還之道,加害者付出某種代價,使得加害—被害者之間的關係反轉;三是轉化之道,從憤怒過渡到展望未來的福祉。但她說,前兩者是無法自圓其說的。
首先是地位之道,納思邦認為,這並不適合於將互惠、正義視為重要價值的社會。將重點放在「貶低、羞辱加害者」,來改正被害者受創的「地位」,容易讓我們的注意力從被害者所真正受到的痛苦與創傷移開,雖然後者才是真正需要處理的。
至於償還之道,納思邦承認,我們在看到壞人受到懲罰,也就是得到「公道」時的確會有滿足感(她稱為「解脫」),而這種加害者付出代價的心理功能,也可能是基於演化、或者文化建構而來,但她說,「不能因為文化教導能建構情感便輕易擁抱幻象」,因為我們很快就會從生命中醒悟:懲罰並不能讓死者復活、或讓既有的痛苦消失,就像懲罰性的離婚也不能修復死去的愛情。納思邦說,即使報復加害者能夠讓我們感到快樂,但也不應該做為我們立法支持這種殘酷且惡意偏好的理由。
但為什麼純粹的快樂並不能提供立法的理由呢?納思邦回應道,我們可以從許多壞事中得到快樂(種族歧視、家暴、虐童);也可以從許多愚蠢的想法中得到快樂(認為人的魂魄可以附在貓上),但這些快樂不應當作為規範評價時的考量。納思邦應是認為,「快樂」並不能獨立作為理由:就像我們在論證基本權利時,以「多數人」會對此感到快樂,作為剝奪少數異議者保障的理由,這樣的對快樂的考量,似乎是奇怪的。
那該怎麼辦呢?納思邦建議,我們應當將關注焦點擺在創造未來的福祉。她認為,對一個理性的人來說,憤怒後,發現自己正在憤怒,然後一笑置之,怒氣就會消散,接著便會開始展望未來:我們該如何繼續生活在一起?此時便會將憤怒過渡成展望未來的福祉,納思邦稱此為「轉化」。
總而言之,納思邦認為,對一個理智、不會過度焦慮且不只注重地位的人來說,憤怒中的應報或償還的概念只是短暫的夢或浮雲,很快就會被更理智的個人思考與社會福祉給驅散。
寬恕的系譜學
而本書在「寬恕」的部分,納思邦則利用猶太教、基督教的歷史脈絡,理解「寬恕」在其中的道德角色,提出她認為更好的、能夠脫離歷史軌跡的替代方案。
她指出,在聖經裡有著兩種寬恕:交易式的、無條件的寬恕,前者連結到教會懺悔的儀式、人與神之間的關係:認罪、道歉、祈求、懺悔、反省;後者則是無條件的、直接的寬恕,展現在〈馬太福音〉耶穌在臨死前的呼喊:「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
納思邦認為,交易式的寬恕仍然犯了上述憤怒的謬誤:將償還、羞辱認為是平衡、正當的行為,可以補償其所造成的痛苦,儘管這樣的贖罪與規訓可以創造有道德、符合道德的人(如尼采觀察的,一種道德的內化),但仍然與憤怒一樣,存在著謬誤。
那無條件的寬恕呢?納思邦說,它所關注的仍然是過去,而非轉化。它也許可以消除通往未來的障礙,但無法指引未來。它也可能讓人覺得自己道德上勝過他人,並招來同前述的地位、償還的錯誤。例如〈羅馬書〉中,保羅表明:「所以,你的仇敵若餓了,就給他吃,若渴了,就給他喝;因為你這樣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頭上。」儘管是呼籲無條件的寬恕,但保羅其實強調了上帝說的「伸冤在我,我必討回公道。」信徒的寬恕是為了讓路給上帝的怒火。而這種無條件的寬恕,僅管看似抹消當下事件的錯,卻沒有進一步地提及未來該如何。
最後,納思邦觀察到,在經典中存在著一種「無條件的愛」,而這種態度也是她所主張的:例如〈馬太福音〉裡的「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這種愛脫離審判、認罪、懺悔以及放下憤怒,也帶著慷慨,讓我們能夠朝向未來,納思邦說,這種態度並不是問「誰受了最大的痛苦」,而是問「該如何才能得到和解。」
小結
納思邦在本書中旁徵博引,包含古希臘詩歌、神話、宗教經典、乃至音樂文本,當代的小說及詩歌,追及宗教、哲學、倫理或法學等領域,為「憤怒」與「寬恕」的情感價值賦予歷史根源,並將其放置於不同的脈絡中討論,以不同的角度反覆探討同樣的概念,除了核心論述的融貫性之外,識者應能於有興趣的領域各取所需
值得注意的是,納思邦並未告訴我們,該如何棄絕論理上有問題的憤怒、交易式的寬恕,並讓自己轉化與昇華。許多人常這樣說,「當你家人被殺死時,你還能如此冷靜嗎?」如納思邦自己說的,「憤怒」在演化上、在文化上,也可能是帶有意義的,我們究竟該如何抑制心裡原始的、復仇的欲望(像復仇女神蠢蠢欲動),該如何成為她主張的,更好的人?
《憤怒與寬恕》一書,就好像是一本「如何成為更好的人」百科大全,儘管她沒有告訴我們為何人要變得更好,但它仍以理性的、溫和的論述不斷地嘗試說服其對話的對象,告訴我們「這樣的世界難道不會更好嗎」、「你難道不會想變得更好嗎」。
不過,雖然納思邦提出無條件的愛與慷慨的概念,但為何它們很重要、它們如何使人面對過去已經造成傷害的過錯、如何造就未來的福祉,卻沒有太多的論述。也就是說,為何無條件的愛與慷慨,能夠讓我們能更好地生活在一起?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人的條件》一書中,提出了「寬恕」與「承諾」的概念,似乎能提供部分的解釋:
鄂蘭認為,「寬恕」是嘗試做到看似不可能的事情,解除已經造成的結果,並且在似乎不再可能開創新局的地方,成功地打造一個新的開始。其真正的力量體現在「愛」之中:「愛雖然是人類生活裡罕見的事情,卻具有無可比擬的自我開顯的力量,愛是完全無世界性的、不在乎被愛的人是什麼,無關他的特質和缺點,更不用說他的成就、缺陷和過犯。」鄂蘭似乎也認識到「愛」相較於「寬恕」,是更進一步的、能夠讓我們面對過去、試圖「解除已經造成的結果」,這是我們如何面對過去的部分;
另一方面,鄂蘭提到,「承諾」可以消除局部的不可預測性:當人們集結在一起「一致行動」,就會產生力量,而若四分五裂,力量就會消失。而讓人聚集在一起的力量,是相互承諾或契約的力量。承諾可以在「不確定的大海上」打造「可預測性的島嶼」。因為這樣的承諾,我們可以面向未來,擁有共同的生活,這是我們如何面對未來的部分。
在《憤怒與寬恕》一書中,納思邦所提出的「無條件的愛與慷慨」,對鄂蘭來說,也許就是「寬恕」與「承諾」的綜合體,像是羅馬的雙面神傑納斯(Janus),寬恕(或愛?)讓我們安頓過去,承諾則使我們能在繼續生活在一起。也許這樣,便能如納思邦在結尾所說的,讓世界不再被報復宰制,而能夠「給和平一個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