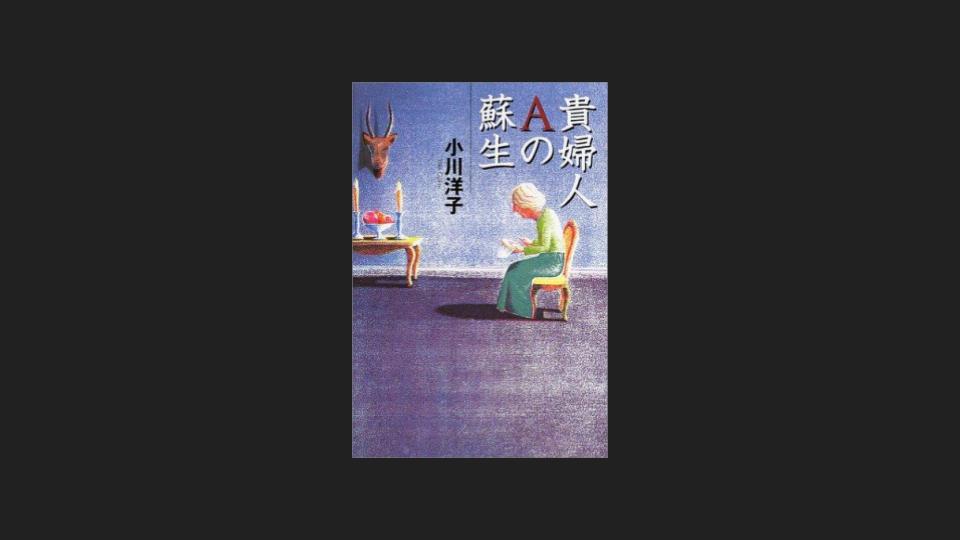那是一種無比純情的叫喊,讓聽到的人心臟彷彿被揪在半空中。那是種走投無路的聲音,讓人五臟六腑凍結到猶如墮入絕望深淵。那發自內心深沈哀怨的聲音,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呼喚我…… 也不知道接下來還要繼續呼喚幾千、幾萬年(略)
「…… 大哥…… 大哥、大哥、大哥。為什麼…… ?為什麼您不回我話呢?是我、是我、是我、是我啊。大哥難道您忘了嗎?是我、是我啊。我是您的未婚妻…… 您忘記了我嗎?…… 我和您互許終身的前一天晚上…… 舉行婚禮前一天的半夜裡,我死在您的手裡。…… 但是,我又活過來了…… 我又從墳墓裡復活,來到這裡。我不是鬼魂啊……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引自《腦髓地獄》
夢野久作《腦髓地獄》
敘事者「我」從睡眠中清醒。
眼望四方是陌生的房間,時間與空間未知,耳裡是陣陣殷切呼喚的陌生女聲。
「我」腦裡一切空白,彷彿意識自虛無中憑空勃發,想不起來自己生命的起點源於哪兒,不知道現在是何時,此處在何方,自己是何許人,而「我」又是什麼?
由此展開的故事,是作品風格人如其名的作家,夢野久作,他十年寫作生涯的心血絕筆,戰後重獲評價的代表「怪」作──《ドグラ.マグラ》(台灣譯作「腦髓地獄」[1])。
《腦髓地獄》裡關於「我」的資訊是一片白紙,讀者不知道,「我」自己也全無記憶,只能仰賴旁人道出的情報拼湊線索。但這些旁人與環境全帶有一絲瘋癲氣息,更遺憾的是除了自己可能精神有異外,「我」眼前的心理醫師,搞不好也沒有多正常。在一切資訊全都不盡然可靠的情況下,「我」讀著心理醫師留下的厚厚一疊手記、遺書與各項匯報(幾佔全書三分之二篇幅)[2],推敲一則詭譎兇殺事件的真相,也試圖推理出自己的身份。
尋找「我」是誰,這個古老的哲學命題事關人類之核心,是自古各種文本創作的重要母題,近年最主流的大眾娛樂品電影之中,也可以頻頻看到這個母題不斷演變、轉化在各種類型片裡的模樣,當代的我們一定不陌生。在這一點上,《腦髓地獄》的氣味或許跟《神鬼認證》、《隔離島》、《記憶拼圖》、描述夢中夢人心深處的《全面啟動》這類諾蘭式的趣味有著幾分相仿,但畢竟沒有好萊塢電影那麼理路明快──或說,夢野久作也並不想給讀者一個理路整然的故事。
但請別誤會,《腦髓地獄》裡雖然層層翻轉反覆,設定卻委實精巧完整,只是讀者很難找到答案罷了。正如夢野久作的自負之語:「這部作品你看五次會得出五種答案。」[3]
雖著書頁往下翻,夢野久作不斷推翻自己前一秒提供給讀者,用以解讀線索、閱讀小說的編碼表。(有點像電影《模仿遊戲》裡,德軍密碼機每天更新一次編碼,每天都需要用不同的翻譯體系,才能解讀加密資訊)前一秒是凶殺,下一秒是夢遊離魂,讀者於是必須不斷置換、更新對整個事發經過的認識,還有對整部小說的預設前提。
敘事不可信,閱讀線索不可信,時間線索也破了又破、再破三破,到最後整部近五百頁的作品,都搞不好只是夢醒時分的短短數秒[4]。
在最淺層的尋找「我」是誰──也就是形而下(或套用作中講不停的「唯物」)的身份背景、偵探事件的推理解謎層面之外──《腦髓地獄》裡的尋找「我」是誰,更隱喻著一絲有些消極、退行又脆弱的,屬於形而上的自我認知與世界建構。
比起推理小說式的解謎找凶,我想《腦髓地獄》更具價值之處或許便在於此,而這一點當然也可以延伸到讀者如何閱讀、進入一本小說的探究上。除此之外,「我」或者美青年「吳一郎」的個人意志受血緣與家族擺弄,勾起書中這一串迷幻顛狂的過程,也讓人遙想起在昭和十年那戰前的空氣底下,家父長式的國族體制中個人仿如水上浮萍,一切飄渺而難倚恃的不安定。
《腦髓地獄》裡所有可信靠之物皆失去了安定。之於小說,那是故事架構與敘事者等,種種攸關閱讀前提的不可信靠;之於人與世界的認知,那是科學理性、醫學人智、物理時間概念等,我們賴以認識世界的尺規的全面崩解。
《腦髓地獄》譯者詹慕如的譯文處理得相當順暢又易讀(可能比原文還好讀)。畢竟這是本饒舌多話的狂人之書,流暢好讀的文字幾乎可說是整本書的命脈。還沒有看過《腦隨地獄》的讀者,如果接下來打算找來閱讀,誠懇建議各位至少要看過一半。若途中覺得哪些理論開始鬼打牆,不妨隨便掃過該段即可,做好不用深究的心理準備,撐過了「瘋人地獄邪道祭文」、撐過了「胎兒之夢」,故事會一下子精彩起來。而待全部閱畢再回頭瞄一眼隨便掃過的部分,也許你會驚覺,自己早已一腳踏入夢野久作迴圈也似的狂言迷宮裡。
關於夢野久作:
出生於明治二十二年(1889),本名杉山直樹。他的第一篇正式出道作始於大正十五年,同年他的私人日記裡也留有關於《腦隨地獄》的創作記述,到了昭和十年《腦隨地獄》發表,翌年夢野久作離世。在日本文學史上留下炫目、異色、耀眼奪目的一抹色彩,正如他意味著癡妄夢話的筆名「夢野久作」。
夢野久作父親杉山茂丸參與許多政治活動,主張大亞洲主義,來自九州的他也與當年台灣治理政策有那麼些因緣。《腦隨地獄》推出於一戰之後,二戰之前,種種隱喻與幽微的言外之意,套用於這部故事舞台局限於醫院這個隔絕空間、充滿奇想的怪異作品上,另有一番耐人尋味的意義。
[1]日文原書名為一奇詭單字,足讓讀者疑惑且印象深刻,中譯本依書中釋義採意譯翻出,帶給讀者的感受可能稍有不同。這問題有點兩難,因為作品裡「我」也會發現一本由狂人寫成的書,同樣叫做《ドグラ.マグラ》,這份書中書的趣味,能替整個殺人事件做出另一種新的解釋。
[2] 書信體是夢野久作極為拿手的模式。好比說他的代表作之一《瓶詰めの地獄》,這部短篇作品以四封信構成,每一封筆法完全不同,參差的陳列順序相當吊人。四封信分別是撿到瓶中信的百姓上呈附書,與三封瓶中信本文,信裡是一對遭逢船難、荒島求生的小兄妹在漫長歲月裡投出的三封求救信。對夢野久作感興趣的人不妨可由此入門。
[3]好比說,筆者當初費盡辛苦讀到了最後一頁,被打著(人類理知的代表)「科學」與(近步與文明的象徵)「醫學」大旗的奇特心理學理論弄得一頭霧水,縱使心上遲疑仍試圖從不斷更新、自我推翻的故事謎底中,理出了一個可能的真相。闔上書本後卻靈光一閃想起:「等等,標題的《ドグラ.マグラ》好像之前在哪兒出現過。」回頭翻找在作品開頭登場幾行後,旋即被棄置不管的那個關鍵字,發現整個故事的解讀又多出了另一種可能。於是五百頁來結腸思索的努力立馬付諸東流。
[4]而且自始至終,以人之瘋狂為題的《腦髓地獄》,都保留了一絲「其實大家都瘋了」的可能性。本文我提起大量電影,除了題材與內容上的考量外,也因為無獨有偶的,這部書裡有一大段是以電影劇本(?)的方式呈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