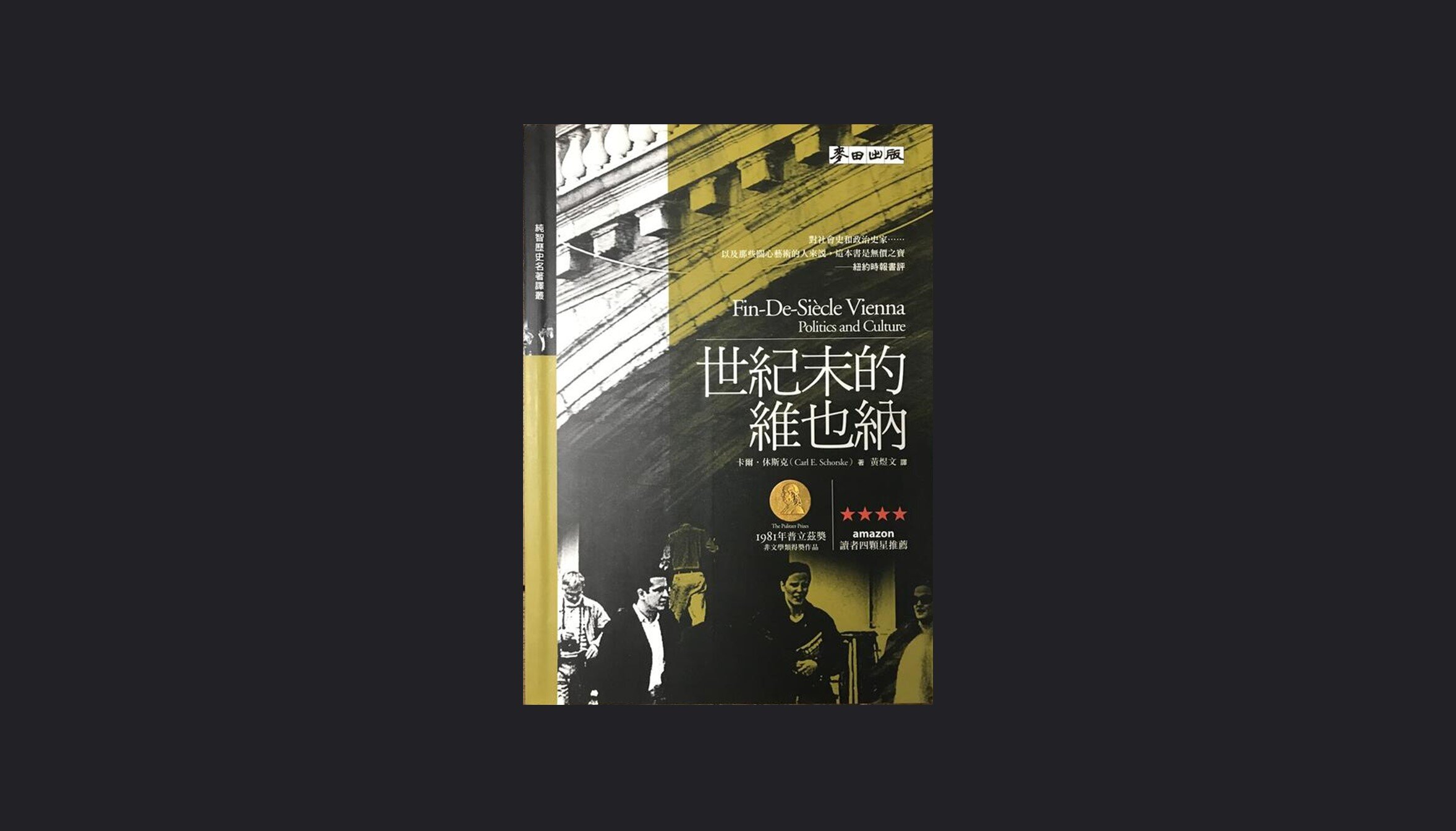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奧匈帝國經歷巨大政治轉型,從王權到憲政,嘗試終結過去的權力結構,另起民主社會。然而,這項轉變隨即導致嚴重政治衝突,乃至國家的崩解。
如何將這段興衰皆驟的過程整理成一個歷史課題?歷史學者卡爾.休斯克(Carl Schorske)於 1980 年出版的《世紀末的維也納》,即使沒有給出確定的答案,也是我們思考這一問題的重要憑藉。
民主變局下的思慮與行動
《世紀末的維也納》以奧匈帝國憲政體制的興衰(1867 - 1918)為時段,以帝都維也納為空間,每章探討不同歷史人物的動態,內容橫跨文學、空間、政治、藝術、學術等領域,呈現個人思想和觀念的變遷軌跡,並映照出「世紀末」(fin-de-siècle)之時,政治與文化的交互關係。
何謂「世紀末」?單就休斯克此書而言,「世紀末的維也納」說的是一個發展不健全的民主社會:以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政治經濟觀為基礎的國家體制,係與舊世界的社會結構(包括貴族階級、手工業經濟體、天主教社群)相抗衡而成立。短暫的和平建基於新舊思維衝突的暗濤之上,萬聲喧嘩的民主社會多少促使對抗關係浮出海平面──當自由主義政治與文化系統開始崩落,成長於如此時代的新生代維也納菁英,因為際遇與環境遭遇不同困難。為了尋求解決之道,他們各自心懷所思,並且各有其政治行動。
以下摘要該書兩章內容,略述休斯克書寫的方法和成果。
第二章論及建築師與都市空間。奧圖.華格納(Otto Wagner)是本章〈環城大道及其批評者〉的主角之一,作為「維也納分離派」(Succession)中堅份子,他認定都市計畫應從「現代」本身的理性秩序尋繹美感,與舊有世界的審美「分離」。華格納的設計不斷嘗試脫離前代遺留的巴洛克語彙,轉而以現代工商業的媒材組構新表達方式,1910 年前後的「新史迪夫特巷四十號公寓」和作為整體維也納都市計畫的〈景觀中心圖〉,可視為此一思想的最具體表現。
大概也在這個時候,步入晚年的華格納,心裡開始浮現了自我懷疑。當時政治情勢逐漸激化,反自由主義和非理性群眾力量進入政治舞台,學院根深蒂固的保守勢力也重新竄升,壓抑了年輕藝術家──包括分離派諸君──的表達空間。
休斯克認為,自由主義衰落導致整體社會經驗轉向,華格納因此於 1913 年設計出當代美術館「MCM-MM」。藍圖中,文藝復興時代的大圓頂(dome)改為鋼條媒材,呈現死氣沉沉的悼念意味,且違背華格納日漸成熟的現代主義建築圖像,設計中已看不見他對理性現代世界的期望,反而是表露對於逝去理性的憑弔。休斯克認為,華格納終於「回歸到歷史當中。……想為『現代』設計的美學模式,也只不過是個歷史博物館罷了。」[1]
政治變遷影響文化思想體系的存滅,但文化語彙也制約著政治行動者想像和實踐的空間。第三章〈政治新曲調〉以三位群眾領袖為探討對象,包括激烈的反猶主義者與提倡猶太復國主義者。休斯克指出,三位領袖皆生於自由主義資產階級,由於體認維也納社會潛藏諸多非主流觀念,經歷思想、認同與進路的抉擇,重新組合各種聲音以換取群眾的支持,從而裂解自由主義統攝的國家政治。
換言之,他們整合不同文化語彙,並賦予個人形塑、表達新政治立場的空間。三位群眾領袖都將他們的意識形態視為信仰,一如急切營造現代建築的華格納。但群眾運動未能迎來想像中的美好社會,僅揭露自由主義民主秩序的脆弱,將維也納帶入更激烈急躁的動盪之中。
「世紀末」是一個不健全的民主社會,也可以說,是一個急遽轉型的民主社會,但轉型的目的地和型態,沒有人說的準;狂放的創造、身不由己的懷疑、迷亂拆毀既有秩序,這些都是休斯克在各個生命故事中引導出的共同經驗,且為本書對「世紀末」的歷史詮釋。
從中休斯克已經超越對於個體生命歷程的回溯,彙整出他對整體社會的觀察:維也納正邁向沒有終點的變遷浪潮。
無歷史的文化:休斯克眼中的「現代」
休斯克在〈導論〉中指出,「現代」(modern)是十八世紀以降西方思想界的重要命題,它相對於「舊社會」或「古代」(ancient)而成立。不過,到了十九世紀末,思想界開始拋棄這種兩種概念互補的關係,而出現一種新意識:要求絕對的、獨立自存的「現代」。
換言之,歷史不再是「現代」之所以存在的憑藉,進步觀念與歷史主義隨而破產,時空的連續性為片段和解構所替代。休斯克稱這樣的轉變為「無歷史文化」的形成。這種對於「現代」的再思考一直延續到今天,也影響人文社會領域對研究傳統的普遍不信任──因為一種思想的歷史脈絡,已失去連結、支撐這種思想內容的正當性。[2]
「無歷史文化」並不是一種史學式的斷言,因為這種對「現代」的新型定義,缺乏明確的時空背景和材料論證。休斯克也無意去組織嚴密的理論來證明該定義之於西方思想史的合用性,他轉而選擇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的維也納作為研究時空,考察人們為何、如何開始拋棄進步,反思「現代」。
在休斯克有意尋索「現代」定義轉型的前提下,前文所述及的各種追尋與失落、批判與懷疑等共同經驗,才被集中在同一本書中。這種後設的研究概念,使人不禁要對休斯克的史學論述是否嚴實合用,存有幾分懷疑;我們可以從什麼角度檢視《世紀末的維也納》所呈現的時空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就應該追問此書的史學方法。
休斯克的局限與遺產
休斯克提出並批評「無歷史文化」,不代表他嘗試復興十八、十九世紀那種「進步的」歷史主義。相反的,他認為面對現代文化,史學家不該再「用一個籠統的定義把多元的事實掩蓋起來」,[3]尤其不能「預先接受一個抽象的範疇來作為分析的工具,如黑格爾(Hegel)的『時代精神』(Zeitgeist)以及彌爾(Mill)的『時代特質』(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age)」。[4]休斯克轉而使用「內在分析」,嘗試為思想的歷史研究另闢途徑。
所謂「內在分析」,即透過文本內容要素的擷取和重組,嘗試理解文化創造者投射在單篇或某組文本中的思想體系、心態狀況等。休斯克進一步將這種文本的內在邏輯當作歷史表徵,與該創造者的人身活動、以及同時代人的思想狀況聯繫起來,組成話語的歷史脈絡,並使思想和心態可與個人實際動態,乃至個人層次以上的社會情境對話、互證。
即使研究取徑新穎,休斯克的諸多書寫環節仍不免遭受質疑。
主題涵蓋過於廣泛,成為《世紀末的維也納》最易受攻擊的軟肋。一方面,各主題之間的關係到底是什麼?休斯克只在〈導論〉中希望「……各個主題能互相印證而構成一個整體」。但如何印證?何謂整體?皆缺乏明確論述。另一方面,前面的例子不難看出,各主題皆與特定個人的生命史緊密相關,特別是從個人的思想歷程、心理狀態、創作表達來與更大的文化史框架相互印證。
但如此一來,難免有「過度詮釋」的問題。舉例而言:第四章探討佛洛伊德的學術生涯如何影響其精神分析理論的建構,休斯克在論證中大量運用精神分析方法,將《夢的解析》中的夢境「重新解釋」,放入個人交遊際遇的脈絡之中。然而,精神分析(姑且不論該分析框架的正當性在今日是否成立)是否能搭配外沿社會因素而與歷史論證磨合?
而休斯克甚至進一步將佛洛伊德的「伊底帕斯情節」作為理解維也納「現代」性質的媒介,其作法不禁令人困惑:這究竟是歷史分析,或文學比喻?這些分析究竟是建築於史料基礎上,或者其實參雜了作者自身的哲學心得與主觀意圖?
若先不論「內在分析」的方法論疑義,休斯克針對「世紀末」維也納短暫的民主社會所作的種種剖析,仍舊開拓了廣大視野。本書同時讓我們得以沉吟自省:臺灣的民主是否也已遭遇某種「急遽的轉型」?書中提及的歷史現象和相關分析、思路,是否也有助於我們理解臺灣今昔的文化、政治和社會?
例如:書中關於建築師華格納的段落,顯示意識形態建構和創作者思維發展間難分難解的關係。如果「環城大道」可視為國家統治語彙的具現,那麼中正紀念堂、國父紀念館、故宮博物院、南海學園……等國民政府遷臺後執行的大型建築計畫,是否也負載了類似的性質?設計者是否也和華格納一樣,對社會與未來懷抱著什麼樣的想像呢?這些想像是否和國家政治有所應合、衝突或協調?後人又如何在既有設計上添加更多的解釋,並與舊有的各種論述相處(或相抗)?
錯綜多元、向度各異的歷史脈絡,為空間賦予深邃探索的可能。「世紀末」已遠,而人們面對社會的歷史,所承接的挑戰卻越來越大。若欲嘗試認識我們這個日趨複雜的民主社會,《世紀末的維也納》確是可以讓我們不斷質疑與參照的經典。
(本文作主為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生)
[1]卡爾・休斯克,〈環城大道及其批評者,以及都市現代主義的誕生〉,《世紀末的維也納》,臺北:麥田,2002,頁 179。
[2]卡爾・休斯克,〈導論〉,《世紀末的維也納》,《世紀末的維也納》,臺北:麥田,2002,頁 31-32。
[3]卡爾・休斯克,〈導論〉,《世紀末的維也納》,《世紀末的維也納》,臺北:麥田,2002,頁 35。
[4]卡爾・休斯克,〈導論〉,《世紀末的維也納》,《世紀末的維也納》,臺北:麥田,2002,頁 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