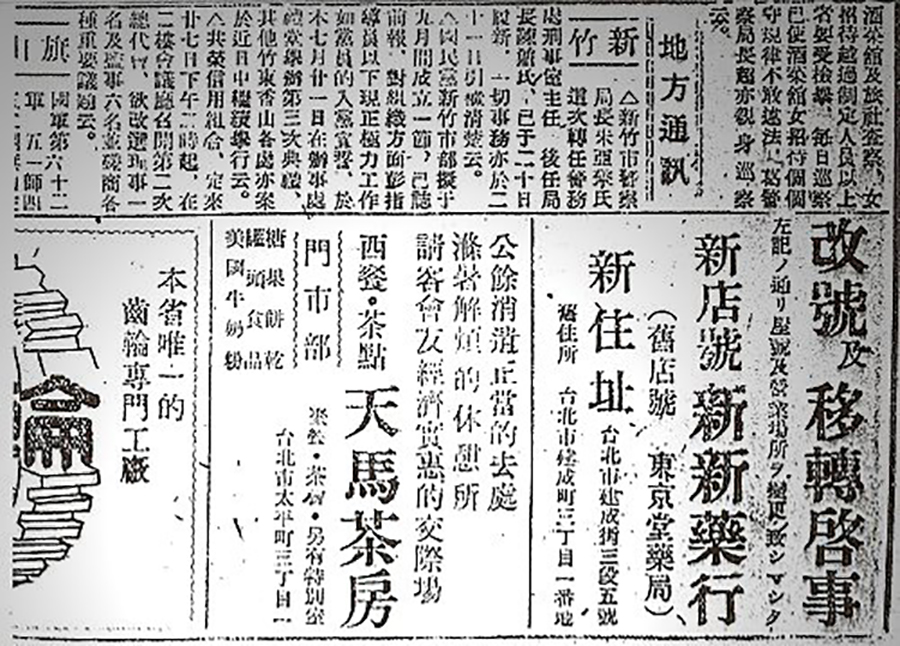編案:「故事」網站「二二八七十周年」的專題,其中一條主軸是「二二八和文學」,三月二日晚上十點公共電視的「紀錄觀點」,即將播出吳米森導演的《再見原鄉:臺裔直木賞作家邱永漢、陳舜臣和王震緒的生命紀錄》,正是「二二八和文學」最佳的影像紀錄。
紀錄片一開頭,日本研究臺灣文學的教授岡崎郁子,憶起 1970 年代至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留學的時候,想要以「臺灣文學」作為研究主題,龍宇純系主任說:「臺灣哪有文學!?」
2015 年東山彰良(本名王震緒)得到日本通俗文學的大獎直木賞,臺灣媒體瞬間陷入一貫的操作手法,給他冠上了「臺灣之光」。
其實不只王震緒,在他之前,也有兩位得過直木賞的臺籍作家,分別是邱永漢和陳舜臣(相關的文章請參見 Emery 的〈被遺忘的初代直木賞臺灣作家:陳舜臣、邱永漢〉)。
由於王震緒的關係,媒體或是大眾開始想起原來我們以往也有「臺灣之光」,但似乎被我們忘記了。為什麼我們會忘記?就是因為「臺灣哪有文學?!」的原因,不是沒有,而是不准有,即使有,也得忘記、也得消去。導演吳米森透過他的視角,讓我們看看這三位作家的臺灣認同,也思考二二八事件、文學和「臺灣之光」的弔詭與矛盾。
「臺灣之光」的故鄉
胡川安:邱永漢、陳舜臣和王震緒這三個作家的故鄉是臺灣嗎?透過這部片,如何思考故鄉在你作品當中的角色?故鄉是一塊土地、一群朋友、一段成長記憶,或只是一種想像、一種虛構的歷史?
吳米森:故鄉的層次相當複雜,在文學家的作品當中也是如此。我們或許可以說故鄉最大的公約數是出身的地方,是童年、記憶、朋友、家族相互交織出來的原鄉。更複雜一點,故鄉也包含想像的因素,不一定是地理上的空間,也不一定是長大的地方,舉個例子來說好了:
我拍《E.T. 月球學園》的時候,講老兵的故事,當時很多人都在講鄉愁,但我其實想要質疑並且解構鄉愁。這些老兵從小長大的故鄉可能只有五年或十年,但在他們流離的過程中,透過彼此的建構,鄉愁成為一個集體虛構的網絡。所以故鄉或是鄉愁比想像的更為複雜,有時是處於心靈層次的,是不存在的,也是浮動的。
從原鄉或是故鄉的概念出發,討論三個臺裔作家的原鄉,與其說我定義什麼是原鄉?不如說我想討論原鄉的複雜性,也藉此解構「臺灣之光」的概念。

文學家的紀錄片
胡川安:文學家的紀錄片,觀眾所預期的可能是作品的介紹、作家的生平,或者拉到作家的故鄉,採訪一些親朋好友,說些他們的豐功偉業、介紹基本內容。但這部片的觀眾如果沒有一些相關的知識背景,看起來會有點吃力。為什麼你會選擇這樣的方式?
吳米森:一般文學家的紀錄片可以稱為「作家身影」式的紀錄片,提供觀眾相當程度的資訊;讓這些人物在歷史的經緯體現清楚的座標,算是功德一件。但我實在不擅長那樣的拍法,加上我最早和影像結緣其實是電視廣告,所以對於「描述美好」一事特別敏感,潛意識裡對其戒備森嚴。
我承認關於影片沒有提供文學/作家的基本的知識背景,恐怕會讓一般觀眾無法消受。但影像存在的目的絕不是取代書本/閱讀;否則對不起文學,也貶低了電影本身。
由於諸多原因無法讓作家本人現身說法,這種情況通常是必須透過學者專家的訪談來背書;但我嘗試著把專家/研究者(岡崎郁子)變成「主角」,唯有如此才能把專家納入如故事的敘事中,他/她對於作家/文學的眼光與記憶才顯得有意義。
岡崎郁子這位日本人,碩士到臺灣大學中文系讀書,在臺灣文學研究還被學界所忽略的年代,她看到臺灣文學的優點與長處,挖掘被人所遺忘的臺灣文學史。透過她自己的人生,觀察邱永漢、陳舜臣和王震緒,岡崎郁子將自己的一生投入邱永漢的研究,透過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生命交流,邱永漢的生命也留在岡崎郁子的身上。
臺灣文學是什麼?
胡川安:從這次拍攝中,你貼身接觸研究臺灣文學的日本人,在日本從南走到北,採訪各式各樣的人,你如何思考「臺灣文學」這件事?而在拍之前,對於「臺灣文學」有什麼看法?
吳米森:臺灣在本土化之後,本土意識抬頭,很多臺灣文學研究都越來越多,也檯面化了。以往臺灣人被國民黨弄到很鄙夷自己的身世,覺得臺灣什麼都不好,沒有文學、沒有文化,好像做為臺灣人就是次等人。我以往對於日本文學很感興趣,覺得臺灣文學很無聊。但當我訪問岡崎郁子時,她反而跟我說臺灣文學相當精彩,而日本文學不怎麼有趣。
我後來仔細想想:難道是因為岡崎郁子是日本人,才覺得臺灣文學有趣嗎?好像也不是。我們被國民黨殘害那麼久,思想上都有點問題,受虐之人的想法怎麼會是對的?
臺灣文學或許就如岡崎郁子所說的,很多的可能性都還沒被開發。我們的文學能量是被低估的,而且我們不是一個國家,確有相關的文學。一個不是國家的地方產生出豐富的文學,其中又與政治高度牽連,這是我在拍攝過程中,覺得相當特別之處。
臺灣之光不想承認臺灣人的身世
胡川安:邱永漢、陳舜臣和王震緒,我們都把他們視為「臺灣之光」,但從這部片來看,為什麼得到直木賞的臺裔作家,都要隱藏自己的身世?說自己是台灣人有那麼難以啟齒嗎?
身分、認同在這些作家身上似乎是種矛盾與情節,但也因為這樣的糾結,才成就了他們的作品。因為你貼近採訪研究者、作家的兒子,或是熟悉作家的朋友,你怎麼看?
吳米森::由於邱永漢和陳舜臣已經過世了,我無法見到,邱永漢我是透過岡崎郁子的研究加以認識的。我有見過王震緒本人,邱永漢和王震緒兩個人對於身分的隱蔽有不同的層次,在他們的作品中,也都用不同的方式呈現。王震緒以往的作品都和臺灣無關,但得到直木賞的這部作品和自己的身世有關,或許是他找到自己的原鄉了吧!
王震緒在臺灣唸過小學,但他的原鄉不一定是個地方,或是臺灣這個地理空間,而有可能是家裡談論的東西,在中國的總總,透過父祖間的建構和回憶,加上臺灣的生長經驗,相互交織。
然而,從個人的身世而言,他不大使用自己的本名,冠上一個像日本人的姓名:東山彰良,他相較於邱永漢是一個很有趣的對照。邱的母親是日本人,但他一直隱藏母親是日本人的身世,反而強調自己「漢」的身分。

從香港、小豆島到中國地方
胡川安:這部紀錄片當中,你走訪很多地方,我們也看得到相當多的地名,包含邱永漢得到直木賞的作品《香港》,岡崎郁子住在日本的岡山,日本人稱此地為「中國地方」。
你也到訪瀨戶內海的小豆島,拍攝很多「瀨戶內藝術季」的藝術品,穿插在影片中,似乎在你的影片中,空間、地方、故鄉、地景相互地交錯,並且貫穿原鄉的主題。
吳米森:我對空間、地景相當地感興趣,我記得三島由紀夫曾經說:「說來慚愧,但身為小說家的我真正感興趣的是『地景』,為了描述這些,我才虛構相關的角色、情節...」這句話我的想法是地理鑲嵌在我們的人生故事中,空間決定了我們的命運與敘事。
在我片中的不同段落:「香港」、「中國地方」其實都是本來這部片的片名,《香港》是邱永漢得到直木賞的小說,「中國地方」是日本岡山、廣島這些地方的地名,但在日本人稱中國地方時,中國還不叫中國,這讓我想問「中國」是什麼?而這些地名也都跟片中不同作者的認同有關。
葉石濤說過:「沒有土地哪有文學?」我很關心土地能長出什麼樣的東西?能滋養出什麼樣的文學?這也牽涉到我去小豆島拍攝「瀨戶內藝術季」的作品,當時我有兩個想法,這塊土地上的藝術形式呈現出什麼樣子?
另外一點就是:拍紀錄片的時候,我不想用很多歷史資料片,大家看這些藝術品時,可以當成廣告來看,雖然有點跳 tone,但至少讓觀眾看到「中國地方」的一些景色,也算是比較有營養的廣告。
從臺灣到魁北克
胡川安:影片的最後,你將場景拉到魁北克,採訪我,當初你是怎麼考慮其中的關聯的?
吳米森:臺灣和魁北克都是追求獨立的國家,其中有很多的相似性,但翻開其中的歷史、文化,我們可以看到不少的差異。
有一個部分我想討論的是語言。我讀了你的《絕對驚豔魁北克:未來台灣的遠方參照》(時報文化,2016),發現一件很有趣的事,在這裡使用法語的魁北克人,並不會覺得它們是法國人。法語是魁北克人認同的一部分,但不等於法國。由此我們可以來思考國家的主體性和臺灣文學的問題。
魁北克詩人感嘆:「我的國家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一場無止盡的冬天。」如果臺灣作家獲日本直木賞一事值得一提的話,絕非肉麻兮兮標榜「臺灣之光」;而是反思我們為何至還今無法辨識自己的身世?在失語的狀態中,連指認加害者都成禁忌。
於是我將鏡頭移向北美唯一法語的「國度」魁北克, 四百年的魁北克經驗可供我們參照借鏡的,不是語言或對法國乳酪的改良,而是不斷追問自己是誰?祖國在哪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