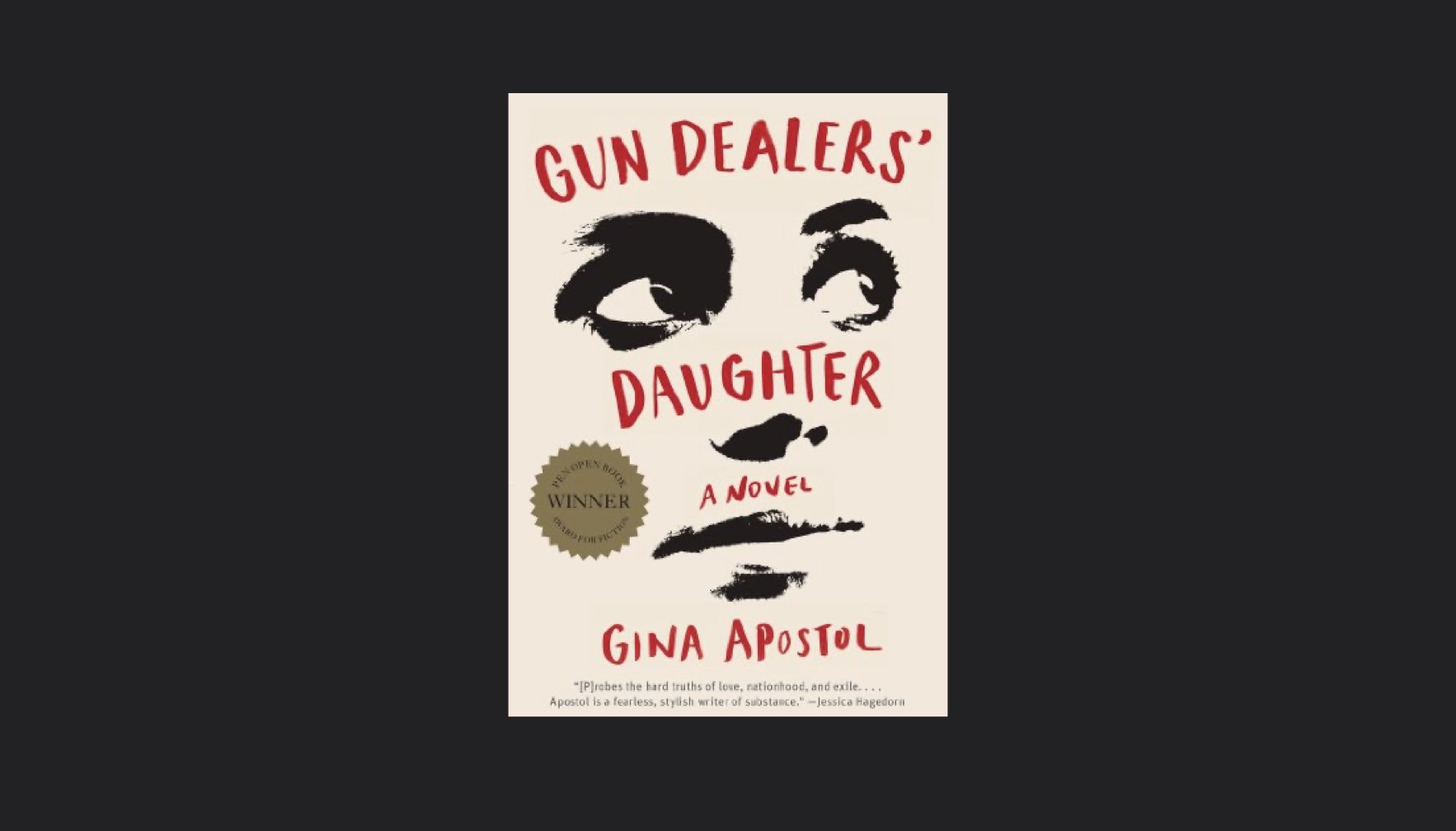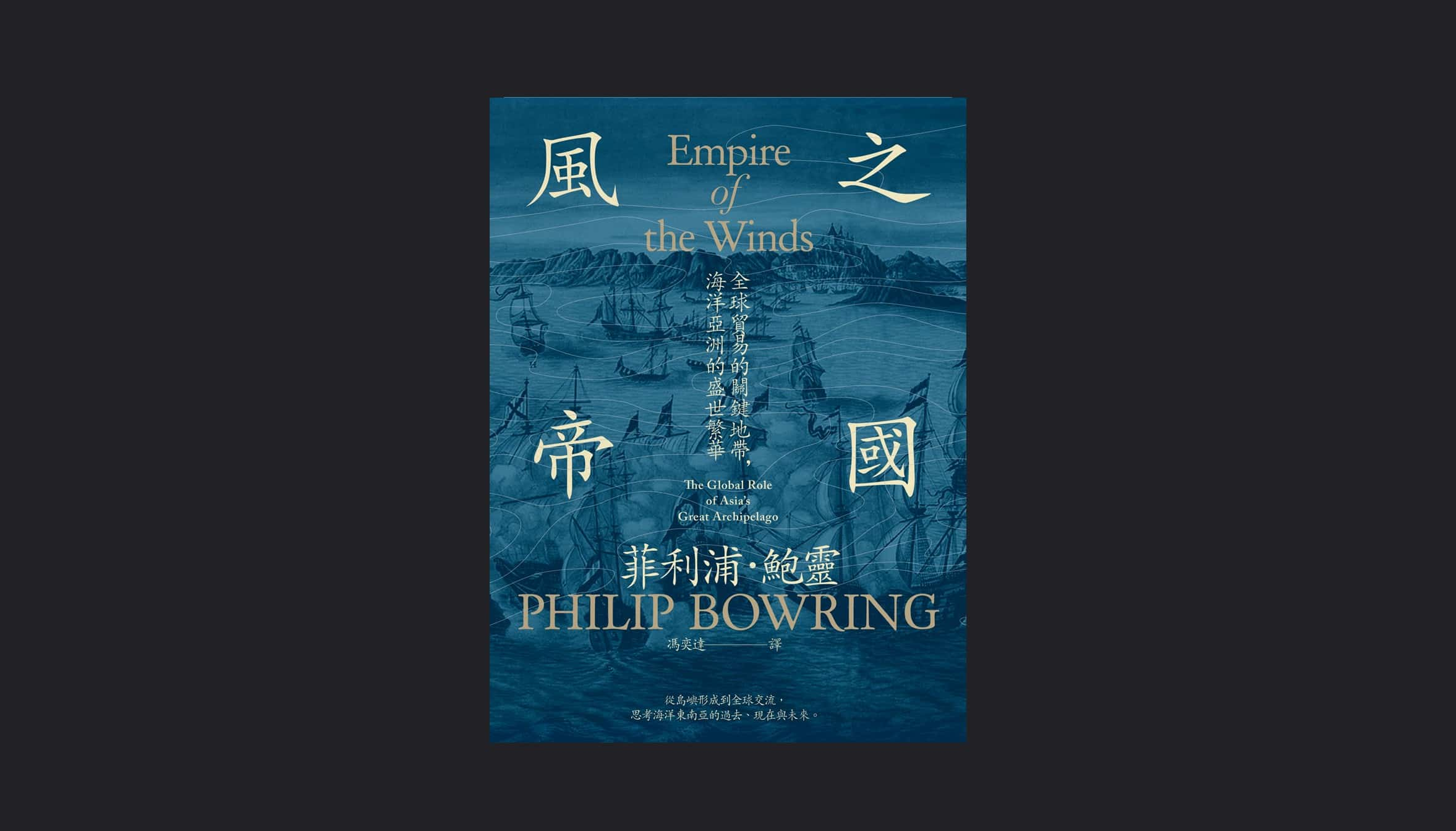菲律賓總統杜特地(Rodrigo Duterte)在 2016 年 7 月正式就任後不久,即開始在首都馬尼拉雷厲風行掃毒,數千人在貧民區陋巷或寮屋簷下不明不白遭殺害,追究無從。這場美名為反毒,實則向弱者抽刃的屠殺,引起舉世震驚,也令世人深思強人政治崛起之危境、人權論述失效的緣由。一種流行的政治詮釋是將之歸結為「威權主義回歸」、「西方民主並不普世適用」,其中隱含文化優越意識,一如殖民者筆下文明深處黑暗蠻荒之域的原型。
如此論調固然不經推敲:菲律賓是一個反殖與革命歷史源遠流長的國家,反抗專權暴政之眾,在史書裡前仆後繼。也正是這段漫長而動盪不已的歷史、對民族身份的探索,有份造就了其多元獨特的革命書寫、異議傳統與當代後殖民文學。其中,菲國當代英語文學書寫既承襲了戰後左翼文學的問題意識,隨後又受益於 1986 年獨裁者馬可斯政權倒台後如雨後春筍的媒體與出版空間,也多少受到同具西班牙殖民背景、宗教文化親緣的拉丁美洲的微妙影響。[1] 同時,其小眾邊緣的書寫特質、當代菲裔知識份子普遍的流徙經驗,令處於夾縫的書寫者對階級與文化表述更形自覺。
這些英語書寫者立足、遊離於所謂「殖民」或「外來」語言的內沿,反而更能體察單一國族論述難以界定安放、所謂「內在」與「固有」文化的異質性,自國族主義載道式的大敘事框架或宿命史觀中跳脫;[2] 透過筆下的敘述者,反身詰問文學書寫的時代意義,省思革命的遺痕與失落、歷史言說之難,刻劃在地聲音的千迴百轉、逆流不逝。
強人政治復歸的緣由,跨代歷史的斷裂,當可從中窺見真相一斑。例如於 2010 年問世的小說 Ilustrado,作者 Miguel Syjuco 以虛實交錯、互為辯證的作家師徒的寫作生命的開展與對接,詰問國族書寫的限制,懷想作家超克生存憂懼(angst)與身份的執迷、面向世界的重要性。本文則希望以引介旅美女作家 Gina Apostol 於 2012 年出版、獲美國 PEN Open Book Award 大獎的小說 Gun Dealers’ Daughter 為例,討論當代菲律賓英語小說如何書寫這種內在的他者,探詢革命的(不)可能。
「失敗之書博大精深」[3]
一如魯迅百年前質問「娜拉走後怎樣」,Gun Dealers’ Daughter 以創傷後失憶的女敘述者 Sol 為中心,描繪 70 年代末馬可斯獨裁治下的社會不義、大學校園裡躍動的左翼抗爭思潮。馬可斯自 1965 年起執政廿年間,曾以剿共平亂為由,在美國的支持下於全國實施戒嚴,血腥鎮壓異議者與平民,又與朋黨掏空國庫、加劇貧富矛盾。這也是直至今天法外處決現象依然肆虐菲國的近因。在這個時代背景下,故事回溯她因愛情與自身階級身份焦慮而投身學生運動,最終卻釀成悲劇、尋死不遂爾後流放歐美的經歷。
情節乍聽看似簡明,然而 Gun Dealers’ Daughter 最令人驚艷著迷之處,在於作者妙用語意的雙關性、意象的對比與聯繫,帶動全書如拼圖般交錯斑駁的敘述形式與層次,令讀者置身 Sol 回憶構築的世界之中時而投入、時而間離,渾然不覺時日之跳接。Sol 在療養院憶述青春的躁動與傾注,文字纖細哀傷而不失冷靜,氣氛令人聯想起美國女作家 Sylvia Plath 的半自傳體小說 The Bell Jar。藉由她刻意雕琢、近乎自虐的喃喃自語,讀者逐少撿拾記憶與殘夢的碎片與懸念,進入她在清醒與瘋癲的臨界無從表述的情感與痛楚,還原悲劇的因與果。
Apostol 利用相似的名字,設計兩組互為鏡像、一體兩面的雙生角色,勾勒命運的錯置與流離。Sol 出身上流社會家庭,父母的媚俗、權貴階級歌舞昇平的畫面卻令她生厭。例如她用了兩節篇幅形容衣香鬢影的總統誕辰音樂會上,管治精英、豪門望族與外交使者們如何各懷秘密,更不忘諷刺總統夫人的壓軸獻唱令人難受得足以鼓動革命(“It was enough to make one turn to revolution”)。
沉迷藝術與歷史的 Sol 尤其痛恨鐵血美軍上校 Grier 對菲律賓獨立戰爭歷史的曲解與屑視,對社會現狀的覺識在校園的左翼氛圍中逐漸甦醒;惟其階級原罪令她置於他者之外,一如她曾經自白,「我在我的國家成為陌生人」(“I had grown up a stranger in my country”)。而那是獨裁者權力高峰之時,也是稍有理想的有志青年都會被異議精神吸引的熱血時代。她在左翼讀書組遇上來自農民家庭的學運女將 Soli,同時愛上 Soli 的男友、同樣有西班牙名門血統的富家子 Jed;她緊隨 Jed 對革命的追尋,輾轉捲入一場改寫眾人命運的政治暗殺行動。
記憶的政治
但這場稚嫩的三角戀也許無關愛情,Sol 嫉羨 Soli 所代表的完美革命樣板、她無可企及的高貴理想與政治正確的身份(Soli 說就連其得名也是源自對菲律賓國父黎剎之作品的敬意),在 Jed 身上則找到一樣的小資叛逆情結,那畢竟只是她自憐自戀的情感投射。Sol 那個對遊行抗爭不以為然的書生男同學 Ed 最為清醒,語帶嘲侃說 ‘Sol for Solipsism’,[4] 拆穿這場自戀的青春祭,背後不過是在集體浪擲自身但求個人救贖的存在危機,何必妄言貧苦大眾命運。
的確,當 Soli 組織貧農抗議遇上軍警鎮壓血腥收場時,Sol 只記得貧民區的酷熱與髒污、令人昏眩欲嘔的死亡。命名的糾結,有如將臨起義的期許,無人知曉業已埋下的命數,盛極韶華,如此陷落。悲劇發生後,Sol 痛切意識到自己始終受著這個她亟欲推翻的不義建制之庇護,付出代價的卻正是身邊那些無權無勢、被棄如敝屣的生命。我不殺伯仁,伯仁卻因我而死,她走向自滅,全因靈魂無法與此和解。Sol 的失憶,因而有著更現實的象徵意義。
而 Sol 錯認了的不只是自己。她以為殖民者是那個父母唯諾奉迎、視菲國為蠻荒異域的 Grier;殊不知暴政機器的運轉,仰賴的並不是暴力本身,而是那些深切懂得暴力底蘊而選擇漠然相視、予取予攜的人。Sol 那個暱稱為「叔叔」的美裔教父 Gianni 是全書始終如謎一樣的人物:他知書識禮、溫文爾雅,對菲國歷史困境處處同情,也比 Sol 的父母更了解她的心思──他甚至會贈以葛蘭西《獄中札記》作聖誕禮物。
殖民者敘述的異質
Gianni 懂得 Sol 的叛逆,更知悉其暗殺計劃,卻選擇旁觀默許、適時利用。Apostol 特意讓他在第二章不無深意地說,菲律賓殖民悲劇本是源於錯認。他借醉向一室的外來者說,航海日誌記載麥哲倫「發現」菲律賓是出於情感的誤認──麥哲倫誤以為自己重返馬來群島一隅,彼時記憶的神往,令他卸下警覺。而史料證明多次大開殺戒的麥哲倫絕非善人君子;為西班牙擴大遠東版圖,也不是他的目的。那為什麼麥哲倫偏偏希望以西班牙國王與天主之名,將菲律賓群島征服收編?Gianni 深信那不是因為戰略計算,而是因為他「動了情」。麥哲倫最終死於菲律賓,算得上是求仁得仁的自我完成,但他的誤認卻成為菲國淪為殖民地的悲慘歷史開端。
但 Gianni 歎道,對被征服的人來說,命運既已寫成,深究當初發現者的目的為何、隱沒於殖民血淚的失落歷史可能,又有何現實意義。一個源於誤認而被征服的域地,一段源於侵略而被書寫的歷史,此成寓言。Gianni 代表的是一種清醒而自覺的犬儒,他既拒絕像那一室的外來者般在殖民主庇護下的安逸裡指點論斷他國,也不問道德,全因體認到他者之域不可言說的絕望。他懺懷自身共業,但他這番話似是故意留給 Sol 和讀者的伏筆:諷刺的是,唯獨這個「外來者」最明白革命的應然與不可得,明白這片土地上的抗命者終必成為悲劇的看客,或不幸陪葬的螻蟻。
麥哲倫之死的寓言,對應的是小說的結局。Apostol 故意在末節隱去 Sol 的敘述位置,容讓在故事前段並不起眼的舊同學、當年另一位讀書組成員 Sally 在多年後與之重逢並書寫落定塵埃,其實旨在保有慈悲──Sol 的雙生兒畢竟並不是 Soli,她也許不再需要背負他人的悲劇了。Sally 代表的卻是 Sol 一切失落的應許,得以在世安身立命有所成就的可能。Sol 成為記憶的囚徒,她的雙生兒卻承擔了記憶逝者的責任、時代變遷之際在場的見證,以最平凡的姿態,走進真正的歷史。箇中諷刺,既淒涼,也有寬慰。
書寫的意義
那 Sol 的悲劇有著甚麼意義?她的築牆自困,並不虛無──她拒絕遺忘,寧可一生被囚於過去、流放自己於歷史以外,那可能是種執迷,可決不是一種懦弱。Apostol 在全書賦予了 Sol 更重要的敘述意義──Sol 對詞藻的迷戀、對蟲蟻與陰翳微物的共感、對尋常細節如栩如生的描繪,都在指向文字的兩面性:書寫可以療傷,同樣可以巧言令色,令書寫者耽溺於創痛而不自覺;可以剖明直面真相的本質,同樣可以掩埋秘密,自我瞞騙而失語成癡。
人世蒼茫莫測,燈明燈滅,擺盪於一念之間,Sol 被自我流放於意識的異境,卻是正言若反,說出了書寫的無用之用,恰好在於其無所應許的脆弱──若生而無限,意志無法對抗無限迴環的虛無,若書寫必然療癒,大悲大苦就失去了洗鍊靈魂而穿越的價值。Sally 在故事末說:「我們中最優秀的都已死去,只有蟑螂如我們僥倖生存」。但即使是蟑螂也有活著、書寫與言說的權利。正如黎剎的文學作品曾經鼓動革命,影響力遠遠超越他被處決的早逝之齡,文學與政治書寫的力量可以無遠弗屆,不就是因為它承載著無數平凡生命不得以成全、世間衝突與遺憾找到和解之道的可能麼?
本文作者為國際新聞記者
[1] 西班牙於16世紀在菲律賓開始了長達三百餘年的殖民統治,「菲律賓」的命名亦源於當時的西班牙王子菲力普。但當時其行政管理並非在西班牙,而是在墨西哥的總督轄地。直至今天,菲國仍是亞洲少有的天主教國家。
[2] 值得注意的是,書寫語言的選擇在菲律賓一直充滿爭議。西班牙在殖民時期並無廣泛推動西班牙語教育與規範,是故西班牙語被視為特權階級精英的語言。以西班牙語寫作的黎剎,作品當時需要依賴翻譯文本接觸國民大眾。後來,美國在菲律賓大力推動英語教學,英語成為主要官方語言,英語寫作的「殖民性」政治爭議不脛而走。但論者指出,在黎剎的時代,菲律賓精英普遍都通曉幾種歐洲語言,今天世人認知的菲律賓當地語言「他加祿語」其時也僅是一種在國內少數人使用的語言。鑑於國內族群與文化的多元,單一而一鎚定音的菲律賓國族語言從不存在。英語寫作從來都是菲律賓國族書寫的一部份。
[3] 編按:借用自北島〈新年〉。
[4] 編按:Solipsism 意指唯我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