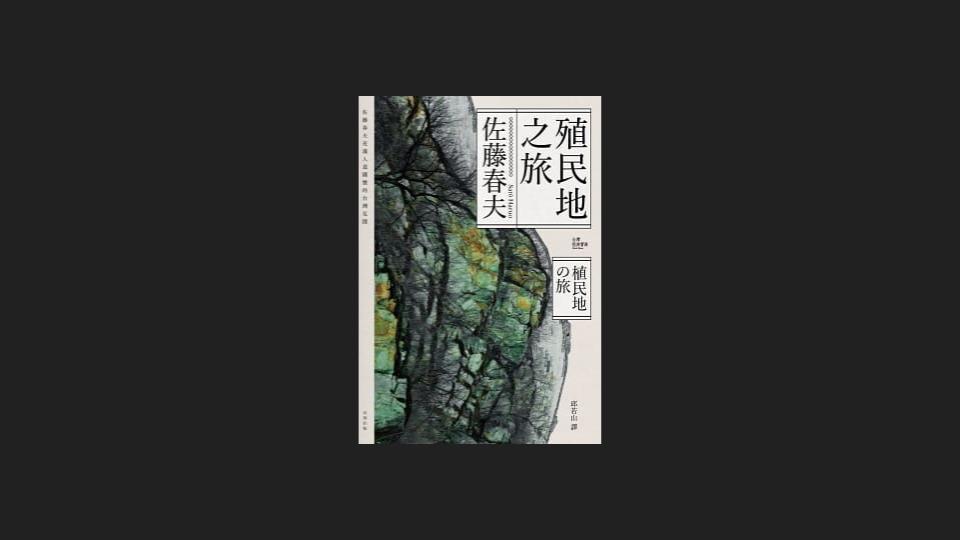臺灣史如何書寫的問題,近幾年已從學術界的私房議題,變成公共領域的熱門話題。在課綱「微調」事件之後,已有越來越多人投入臺灣史的探索與閱讀浪潮。
在這個意義上,日治時期的臺灣研究者伊能嘉矩就是我們的先行者。
伊能嘉矩的《臺灣文化志》與眾多著作、手稿,也成為後來臺灣研究的重要資料。去年(2017 年)是伊能嘉矩的一百五十歲冥誕,今年(2018 年)則是《臺灣文化志》出版的九十周年,值此之際大家出版社重新出版了伊能嘉矩的《臺灣文化志》,並在首場新書講座邀請國史館館長吳密察及新版《臺灣文化志》的審訂者陳偉智,在大稻埕的「臺灣物產」向讀者介紹《臺灣文化志》的誕生與重生。
臺灣的歷史,由誰書寫
吳密察首先說,談到臺灣的歷史,許多人的第一印象即是連雅堂的《臺灣通史》,儘管多數人其實只看過教科書所收錄的〈臺灣通史序〉。
從體例上來看,《臺灣通史》用傳統中國史書的紀傳體撰寫。這種紀傳體體例與現代人較熟悉的紀事本末體的敘事方式不同,因此一般人即使讀了此書也很難對臺灣歷史有一個通盤的理解。更大的問題在於,「《臺灣通史》犯了歷史學最不可犯的大忌。」為了合理化反清復明的論述,書中甚至捏造史料。
吳密察指出,《臺灣通史》以明朝為正統。連雅堂為了合理化這種反清復明論述,用了非常大的篇幅書寫鄭成功在臺的那一年;另外,在朱一貴事件的呈現上,連雅堂甚至自己幫朱一貴寫了一篇反清復明的起義檄文,直接偽造史料。
除了以明朝為正統之外,《臺灣通史》的另一個意識型態問題是「以漢人為中心」。這種以漢人為中心的史觀,讓原住民在臺灣史中的地位完全成為被邊緣化的客體。怪不得有原住民指出:《臺灣通史》強調了漢人移入者「篳路藍縷」,卻沒有看到原住民的「顛沛流離」。這樣的歷史敘述,已經不適合當今強調多元平等的時代潮流。
同時代的另一部臺灣史
吳密察提醒說,有一個與連雅堂同時代的人,也幾乎在同一時期寫出了生涯代表作,那就是伊能嘉矩和他的《臺灣文化志》,「現在應該來看與連雅堂相同時代的另一部臺灣史重要著作」。
「《臺灣文化志》並不是完美無缺的,它也有其時代限制,它仍然免不了十九世紀後半葉至二十世紀前半葉普遍流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以及殖民主義的痕跡。」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它也已經信守現代西方歷史學所強調的史料實證論之基本寫作精神。
現代歷史學講求廣泛地收集運用史料,寫作歷史必須言而有據。在那一個沒有影印機的時代,伊能嘉矩幾乎是「窮盡心力」地抄錄了他所可以碰觸到的史料,即使外文史料也沒有放過。伊能嘉矩不只是個埋首於圖書館、書齋的研究者,他也走入田野在寺廟中抄錄碑碣、採訪耆老,這些資料後來成為了《臺灣文化志》豐富的內容。
被發現的伊能嘉矩
不過,儘管《臺灣文化志》這部先驅性的著作意義深遠,但在一九九〇年代以前卻只有小眾的學術界才瞭解伊能嘉矩的重要性。
伊能嘉矩的名字在一九九〇年代臺灣民主化之後,才開始廣為人知。伊能嘉矩的著作當中,關於平埔族的調查研究,首先被重視。一百多年前伊能嘉矩對於臺灣原住民的先驅性調查研究和分類,成為原住民(包括平埔族)文化復振運動的重要憑藉。
伊能嘉矩不只是一個人類學家,他對臺灣史的影響同樣深遠。陳偉智以伊能嘉矩在一八九九年出版的《世界ニ於ケル臺灣ノ位置》(臺灣在世界中的位置)為例說明,該書總共有十二個小節,編排方式就像當今臺灣史讀物關於一八九五年以前的歷史的大致排序。
後來伊能嘉矩在一九二〇年代參與臺灣總督府的史料編纂委員會,負責了清代臺灣歷史的研究,其研究結果不少後來成為臺灣史的重要論述。
因此,陳偉智指出,伊能嘉矩其實一直以「不具名」的方式與我們同在。如果換個說法,或許也可說,伊能嘉矩從未離開臺灣,他的影響其實一直都在。
值得慶幸的是,伊能嘉矩的整體著作在歷經三十多年的整理之後,已經能夠讓眾多研究者運用。
經典必須一讀再讀
伊能嘉矩是個臺灣迷,他在返回故里後,還在家鄉岩手縣遠野市的自宅設立「臺灣館」,宛如一座臺灣博物館。這批豐富的蒐藏、手稿、圖書,大部分由臺北帝國大學於一九二八年開學前購得,其中的民族學標本目前收藏於臺大人類學博物館,圖書、手稿則典藏於臺大圖書館,另有一部分蒐藏則入藏於遠野市當地的博物館。
吳密察引述日本學者福田德三的說法,將《臺灣文化志》定義為一部關於清代臺灣的文化百科全書、年鑑與檔案資料彙編。
他也指出,「由於《臺灣文化志》具有臺灣文化百科全書、年鑑、檔案彙編的性質,所以當你對清代的臺灣歷史好奇、有所疑問時,可以先從它入手,只要翻閱《臺灣文化志》大概都可以得到答案,而且是相當具有質量高度的答案。」
此次《臺灣文化志》的重新出版,審訂者陳偉智更花了許多心力與時間,校對、補充書中的內容。
他說,「《臺灣文化志》是一部經典作品。經典之所以是經典,因為它可以一讀再讀。」在問世九十年之後重讀這部書,可以重新回顧臺灣歷史論述的履歷,同時,也期待後續的研究者能在伊能嘉矩的基礎上,持續不斷地前進與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