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眾多伊斯蘭議題中,女性議題大概是最紛雜又最引人注目的。從外顯的頭巾、婚姻制度,到女性的社會角色,無一不引發熱議。我們究竟該如何看待穆斯林女性?她們是等待被拯救的弱者,還是獨立自主的個體?穆斯林女性又是如何呈現自己?她們希望自己如何「被看見」?要解答這些問題,或許該從一千四百年前的阿拉伯半島開始談起……
沙漠裡的女權種子
若欲檢視伊斯蘭的性別觀,較恰當的方式應為回歸伊斯蘭的根基──《古蘭經》,以及穆罕默德最初建立伊斯蘭的時空環境──七世紀的阿拉伯半島。眾所皆知,阿拉伯半島是黃沙滾滾的大漠,糧食和資源稀缺。在伊斯蘭教出現以前,阿拉伯人生活在典型的部族社會,部族的生存和榮光高過一切,並且隨時需要戒備外族的侵略。在如此征戰頻仍、環境嚴峻的狀態下,具有生理優勢的男性在部族中的地位高過女性,甚至常有殺害女嬰之事。
西元 610 年開始,先知穆罕默德陸續接收到真主(Allah)的啟示,日後由早期的追隨者協助記錄,集結成《古蘭經》。《古蘭經》中有為數不少針對當時的事件或情勢做出回應的經文,因此我們必須理解這部經典有其脈絡性。去探討這些歷史脈絡,並不是為了證明《古蘭經》只是降下給在沙漠生活的阿拉伯人,對其他地區的人們毫無意義,而是因為瞭解脈絡將能夠幫助我們看見經文字面意義背後提倡的更具普世性的價值。
那麼,回到最初,真主是如何造人的呢?《古蘭經》第 4 章第 1 節提到:「眾人啊!你們當敬畏你們的主,祂從一個人(亞當)創造你們,祂把那個人的配偶造成與其同類的,並且從他們倆創造許多男人和女人。」由此可知,真主為亞當創造的配偶是與其平等的,女人不是由男人的肋骨造出,並不是男性的附屬品。為回應當時的女性處境,《古蘭經》更譴責了當時部族活埋女嬰的習俗,並主張性別與後世的報酬無關,可看出對女性平等地位的強調,因此早期皈依伊斯蘭的穆斯林中有非常高比例的女性。
經常被視為伊斯蘭壓迫女性的「罪魁禍首」大概是一夫四妻制。《古蘭經》寫道一個男人可以娶四名妻子,但前提是必須公平對待每位妻子。有些人認為伊斯蘭允許多妻的原因,是考量當時阿拉伯半島征戰頻繁,經常有男子葬身沙場,喪夫的女性較難受到妥善保護,因此多妻有其必要性。
此外,美國學者哈濟生(Marshall Hodgson)在《伊斯蘭文明》(The Venture of Islam,臺灣商務出版)上卷第二冊第三章中,有一專門的小節討論伊斯蘭的家庭法,其中解釋了為何一夫多妻制可能反而維護了女性權利。在階層明確的社會中,富裕男性通常同時擁有多名女性性伴侶,或是和女奴發生性行為,相較於基督教男性的非婚生子女被貼上「私生子」的汙名標籤,伊斯蘭透過婚姻賦予四位妻子及其子女平等的權利,女奴所生下的子女亦然:「穆斯林的婚姻系統犧牲了主要配偶的婚姻連結,而把所有配偶及其子女間的平等置於首位。」

誰來解經:男性還是女性?
由一夫四妻的例子,我們便能夠明瞭,單就經文字面意義的理解,以及探討歷史脈絡的理解,會導致對《古蘭經》經文兩種全然不同的詮釋。《古蘭經》是以古典優美的阿拉伯文寫成,用字遣詞並不簡單直白,許多語句更隱含深義,若沒有仔細推敲便難以徹底理解,因此,出現了經典的詮釋者──伊斯蘭學者或教長(imam)。這些詮釋者是《古蘭經》與一般穆斯林之間的橋樑,但其各不相同的解經方式也左右了穆斯林對伊斯蘭的理解,逐漸掌握穆斯林社群的話語權。然而,長久以來,在詮釋者之列甚少看見女性的身影。
美國記者鮑爾(Carla Power)著作的《古蘭似海:用生活見證伊斯蘭聖典的真諦》(If the Oceans Were Ink: An Unlikely Friendship and a Journey to the Heart of the Quran,八旗文化出版)一書,記錄了她和印度伊斯蘭學者阿卡蘭(Mohammad Akram Nadwi)一同研讀《古蘭經》的過程。除了描寫兩人針對許多伊斯蘭議題的對話與論辯,作者也相應補充了異於阿卡蘭的各派論點。書中的第二部以「家」為題,探討許多伊斯蘭女性議題,鮑爾引用了一些女性學者對《古蘭經》詮釋的女性觀點,如阿米娜・瓦杜德(Amina Wadud)、蕾拉・艾哈邁德(Leila Ahmed)等人。
在討論童婚的篇章〈「小玫瑰」〉中,提到阿卡蘭因兩位女學生而改變對童婚看法的經過。在穆罕默德的幾位妻子中,對伊斯蘭信仰影響深遠的阿伊夏(Aisha)正是童婚新娘,她在九歲時就和先知完婚。對此,阿卡蘭原先主張,婚姻的正當性並不在於女性的法定婚姻年齡,「合意」才是重點。不過,在他的伊斯蘭法學課堂上,討論到未成年婚姻時,兩位女學生提出抗議。她們在課後花了幾週的時間和老師辯論這個議題,表示在大部分情形下,女童都沒有能力表達其自身意願,以及未成年性交對女性健康的嚴重傷害。於是,阿卡蘭的立場轉變了:
阿卡蘭告訴她們倆,司法正義需要吸收女人的聲音和經驗。穆斯林不該僅從古典文獻認識他們的信仰。今天的學者有必要書寫新的文本,將女人眼中的《古蘭經》與先知傳統之精髓納入考量。「寫本書,」他敦促雅祖,「這些法律觀點被記錄的時候,女性並沒有參與。妳們一定要寫本書。」
穆斯林女性需要的不只是《古蘭經》提倡的平等,更需要在實際的規範律法中被重視、被落實。當女性詮釋出現,才可能對抗扭曲原意的父權主張,女性的主體性也才能夠在辯證之中逐漸萌芽茁壯。
不過,伊斯蘭歷史上,女性是否真的被隔絕在學術之外?事實上,阿卡蘭曾經進行近十年的研究,只為挖掘出伊斯蘭被埋藏的女性學者傳統,原先只計畫寫成一本小冊子,最後寫成四十卷的鉅著──《女聖訓專家:伊斯蘭的女性學者》(al-Muhaddithat: The Women Scholars in Islam)。阿卡蘭從傳記字典、旅遊書和私人信函中,搜尋她們的蹤跡,最後囊括了七至二十世紀的九千名女學者;藉此,阿卡蘭推翻了伊斯蘭知識全是男性研究成果的迷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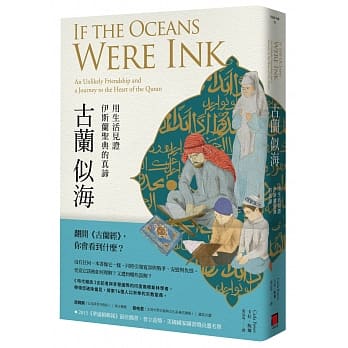
對比於今日女性伊斯蘭學者稀少的光景,過去這些女學者的成就令人驚嘆。中世紀撒馬爾罕的法蒂瑪・撒瑪干迪亞(Fatimah al-Samarqandiyyah)向父親學習聖訓和伊斯蘭法學,成為有資格頒布教令(fatwah)的法官。十三世紀的法學家法蒂瑪・賓特─雅赫亞(Fatima bint Yahya),同為法學家的丈夫會在課堂上講授她的教令,被學生認為是「來自垂簾後的指示」。此外,還有許多女學者因學識豐厚,巡迴中東各地演講。
女性學者被主流歷史忽略的原因相當複雜。其一和「遮蔽」(hijab)的概念有關,伊斯蘭推崇謙遜的美德,而傳統上女性謙恭的表現則是不暴露在公眾目光之下,因此許多女性學者被提及時,經常是以某人的姊妹、妻子和女兒的身分出現。
其二則是因為傳統穆斯林男性的社會角色必須承攬家庭經濟,有時必須將自己的學術研究推薦給掌權者,積極爭取曝光度和政治權力,而十七世紀穆斯林國家受歐洲殖民統治後,更引發男性權威焦慮,女性學者的發展空間遂被壓縮。不過,阿卡蘭也就此論稱,女性的學術研究更為信實,因為「她們不需要編造聖訓,聖訓對她們而言無關收入,而且她們傳授聖訓不是想獲得名氣。她們純粹是為學習而學習。」

選擇如何遮蔽自己的女人
當然,要建構女性的主體性,並非唯有學術研究一途,現今的穆斯林女性已經發展出更多元的實踐方式,頭巾(hijab)是非常好的例子。
穆斯林女性究竟該不該戴頭巾?儘管在穆斯林社群中,姑且不論穿戴何種頭巾、遮蔽程度為何,贊成頭巾者為多數,但事實上,《古蘭經》並未有明確經文指出女性必須遮蓋頭髮和臉部,僅僅提到:
你對有信仰的婦女們說,叫她們降低視線,遮蔽下身,莫露出首飾,除非自然露出的,叫她們用面紗遮住胸膛,莫露出首飾。(24: 31)
先知啊!你應當對你的妻子、你的女兒和信士們的婦女說:她們應當用罩袍(jilbab)蒙著自己的身體。這樣做最容易使人認識她們,而不受侵犯。(33: 59)
首先,對於生活在沙漠環境中的人們而言,以衣物遮蔽身體具有實質的防風沙效用。其次,在七世紀的阿拉伯半島,蓄奴仍相當普遍,女奴往往成為男性發洩性慾的對象,《古蘭經》勸告穆斯林女性穿著遮蔽身體曲線的服飾、不要展露誘惑男性的首飾,是透過區隔自由人的女性及奴隸的穿著打扮,表明穆斯林的身分,進而保護女性安全。
《古蘭經》對女性穿著的勸戒或許僅止於此,然而日後所衍生出的羞體概念界定、女性露出肌膚程度之規範,部分和聖訓傳述有關,其餘則和各地區的政治、社會、文化狀況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穆斯林女性戴不戴頭巾,牽涉到個人的宗教觀和整個社會結構的影響。現任臺灣伊斯蘭研究學會理事長梁紅玉的《蓋頭掀不掀:臺灣穆斯林女子的策略與認同》(女書出版),縝密地爬梳國內外相關文獻分析,勾勒出頭巾概念的演變。此外,她更以臺灣穆斯林女性的身分出發,描寫在臺灣社會脈絡下,穆斯林女性穿著頭巾的感受與身體經驗,提出女性主義的批判觀點,深具啟發性。
作者梁紅玉在書中提到:「伊斯蘭婦女穿戴 hijab[1],皆經歷著某種自我說服與調整過程,其考量因素亦隨個人需求與現實阻力(包括伊斯蘭和非伊斯蘭地區、宗教與世俗認知)有所差別……」在每一層頭巾,或每一綹外露的髮絲背後,都隱藏著穆斯林女性與外界互動所形構的個人生命經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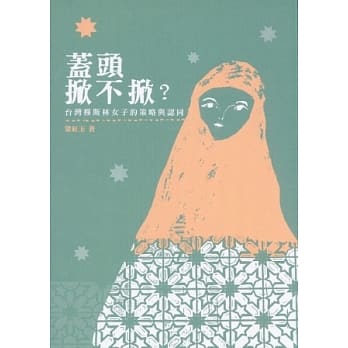
不戴頭巾的穆斯林女性中,有些認為那些《古蘭經》章節的真正意義是穿著符合當地習俗的服飾,而身在穆斯林為少數的地區,她們選擇露出頭髮;有些則認為信仰是她自己和神之間的事,無須透過外顯的衣著來表明自己的信仰。戴頭巾的穆斯林女性中,有些也身在穆斯林為少數的地區,她們為了對抗歧視與誤解,選擇用頭巾展現宗教(政治)認同;有些則是為了仿效聖訓中先知女眷的穿著,或是接受頭巾的服裝形式,認為那能夠展現出穆斯林女性的「端莊」(modesty)。
和露出臉部的頭巾相比,只露出雙眼的面紗(niqab)更具爭議性。在沙烏地阿拉伯或其他較為保守的地區,女性會被強迫戴上面紗,然而穆斯林社群的主流多認為面紗是選擇性的,應由女性自行決定是否穿戴。《古蘭似海》也描述了阿卡蘭如何和女兒蘇麥雅(Sumaiya)溝通穿著的過程。
阿卡蘭深信,女性不應被迫戴頭巾或面紗。「人不因穿著而虔誠」,端莊的打扮一如信仰,應出自內心,否則便失去實質意義。因此他只告訴女兒,他認為寬鬆的衣著是好的,但實際該如何穿,蘇麥雅應該自己決定。有天,蘇麥雅戴上面紗,反而讓阿卡蘭大驚失色,深怕她受到某些強硬派團體控制。
因為父親的態度,蘇麥雅「不是被遮蔽的女人,而是選擇如何遮蔽自己的女人」。她會視身處環境對穆斯林的友善程度,來決定該不該戴面紗,以免引發過度的側目,但她也表示:「比起沒戴它的時候,戴它讓我覺得比較自在。」這種作法也呼應了梁紅玉的論述,穆斯林女性如何蓋頭(或不蓋頭),實是個人需要和環境因素拉扯的結果。

端莊時尚風潮中的伊斯蘭
近年來,穆斯林女性優雅莊重、不展露身體曲線的服裝風格,造成了一股「端莊時尚」(modest fashion)風潮。日本服裝品牌 UNIQLO 和英日混血穆斯林設計師哈娜・塔吉瑪(Hana Tajima)聯名合作,推出穆斯林系列女裝,去年夏天在臺上市。哈娜・塔吉瑪接受訪問時表示:「主流時尚對美的詮釋往往旨在激發情慾。重點不在布料多寡,而在於穆斯林於主流時尚市場擁有選擇的權利及自由。」不過,原先目標客群為穆斯林女性的服飾,其柔美、端莊的風格也開始受到非穆斯林女性的喜愛。UNIQLO 不是唯一推出穆斯林風格服飾的品牌,MANGO、H&M、GAP 等都曾先後推出穆斯林女裝,或聘用穆斯林模特兒。[2]
在「端莊時尚」的潮流下,臉書、Instagram 等各大社群網站出現了一群穆斯林時尚部落客和 Youtuber,擁有成千上萬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粉絲,她們用頭巾和寬鬆服飾打造出繽紛多彩的個人風格。頭巾似乎成為她們展現自信、美麗與個性的載體,破除穆斯林女性樸素、低調、受迫的刻板印象。
不過,對時尚的追求是否沖淡了頭巾的信仰意義?許多部落客在上傳穿搭照、頭巾教學影片之餘,都不忘分享《古蘭經》帶給她們的感動、頭巾的意義,或是自己穿戴頭巾的生活經驗和真實感受。
知名的埃及裔英國部落客迪娜・托奇歐(Dina Tokio),曾在影片中坦承自己其實大多時候並不喜歡戴頭巾,但她絕不會脫下頭巾,因為她從十二歲開始每天都戴著它:「頭巾還牢牢纏在我頭上的唯一理由……是因為我知道這是真主所想要的。」而時尚、設計和創意讓她對頭巾保有新鮮感,讓她可以一直戴著頭巾。不過,她堅決否認自己戴頭巾是為了趕流行:「因為時尚來來去去,但我從不曾時而戴、時而不戴頭巾。」
考量到戴頭巾仍有個人選擇的差異,或許可以把迪娜所認知的「戴頭巾」代換為「女性對伊斯蘭信仰的投入與實踐」。一直以來,穆斯林女性要堅持信仰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必須對抗父權的曲解、社會的眼光和自我信念的動搖。然而,無論是用堅定的論述或是美麗的衣著,每位穆斯林女性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奮戰(jihad)著,努力走在真主指示的道路上。
(本文作者為政大阿拉伯語文學系畢業,「伊斯蘭沒有面紗」臉書粉專負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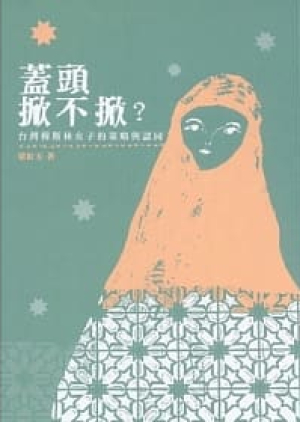
透過訪談與文獻爬梳,
描述台灣脈絡下穆斯林婦女穿著hijab的感受、策略與生活經驗,
另一方面則試圖探詢、統理穆斯林女性對傳統的不同認知,
以及回應hijab的若干非宗教論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