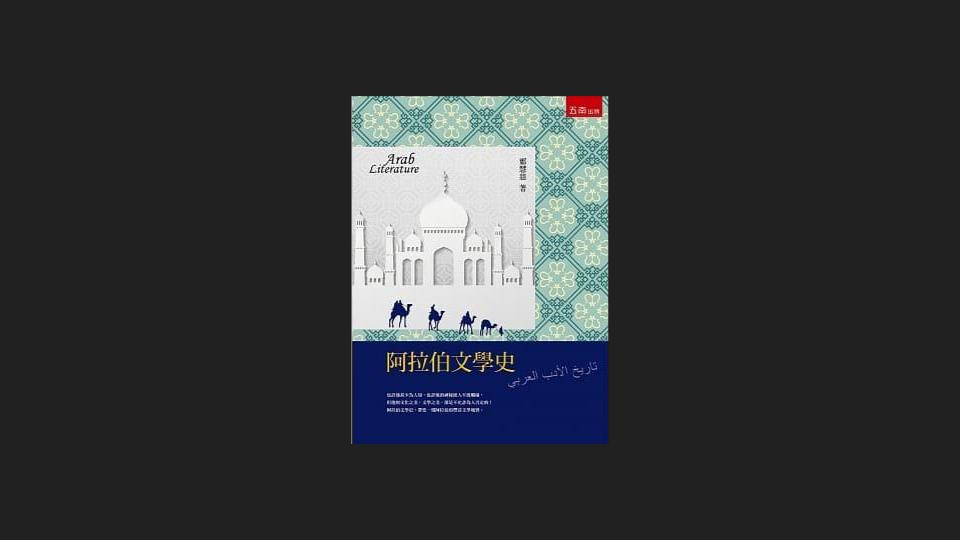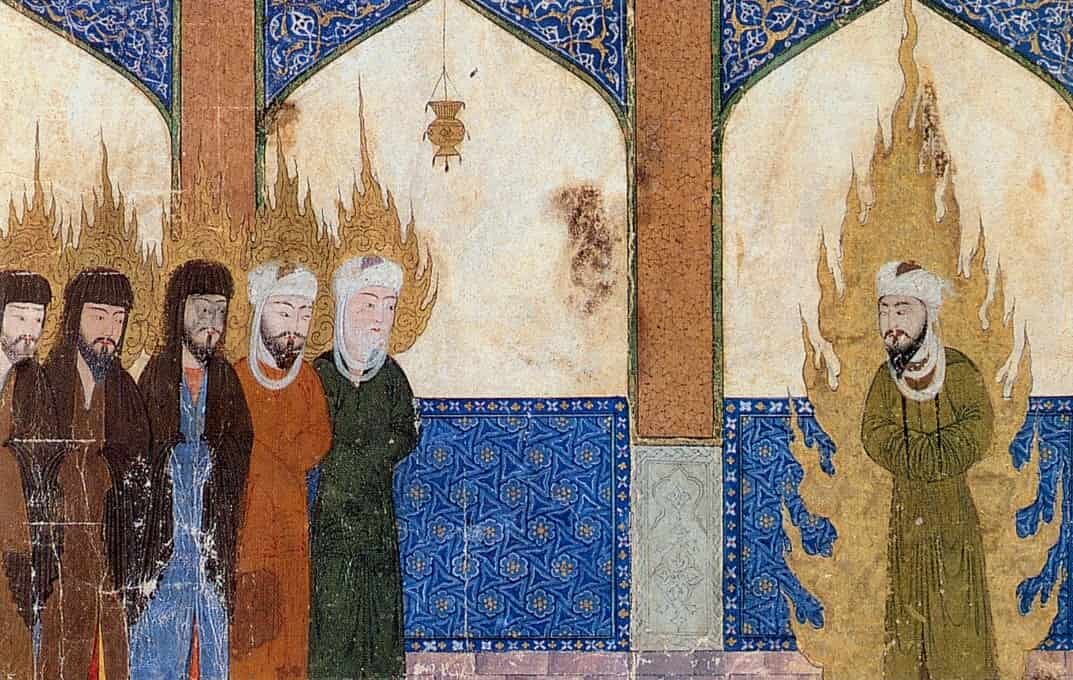阿拉伯文學的長河,時而清澈見底,樸質純淨;時而波濤澎湃,深奧難測。面對波斯、羅馬、閃族等諸多古老文明交匯之地的思想成果,誰能釐清其中每一個元素並堅定的說:這是「阿拉伯的」。沙漠、駱駝、馬……嗎?還是面紗、頭巾和駝轎?顯然這些答案都令人感覺心虛。然而,只要夠謹慎,便可以明確地針對某些元素說:這是「伊斯蘭的」。換言之,阿拉伯文學的獨特性在於伊斯蘭的涓流早已注入文學的長河裡,影像清晰卻與文學難捨難分。
伊斯蘭存在蒙昧時期詩歌裡

詩歌是阿拉伯文學之母,伊斯蘭興起之前的阿拉伯文學絕大多數是透過口耳相傳的詩歌。我在拙著《阿拉伯文學史》裡提到「伊斯蘭」並未在蒙昧時期詩歌裡完全缺席;《古蘭經》稱伊斯蘭以前的一神教徒為「胡納法俄」(al-Ḥunafā),亦即信仰亞伯拉罕所信仰的教義者,這些人在《古蘭經》中被視為穆斯林。因此,蒙昧文學隱約出現伊斯蘭色彩,譬如詩人艾比德(‘Abīd bn al-Abraṣ)對「阿拉」發誓:
我對阿拉發誓,
阿拉對需要者是多恩澤,
至恕,
至寬容的。
又如詩人納比佳(an-Nābighah adh-Dhubyānī)因得罪努厄曼(an-Nu‘mān)國王而吟的致歉詩中,他讚頌此王說:
難道不見,
阿拉賜你經章,
其下諸王忐忑不安。
因你是太陽,
諸王是星辰,
你一旦昇起,
諸星皆黯然。
上述詩中「阿拉」一詞在結構上由限定詞 al- 與名詞「神」(ilāh)組合而成,型態上便隱含「唯一的神」之意。伊斯蘭之前大多數人們是多神教徒,詩節中使用此詞,透露詩人的「伊斯蘭」觀念。
阿拉伯文學語言是古蘭經語
穆斯林無論其母語為何,皆須使用阿拉伯語誦讀《古蘭經》,因為《古蘭經》經文說:「這些是明確的天經經節,我確已降下阿拉伯文的《古蘭經》,希望你們瞭解。」(12:1-2)阿拉伯語的神聖性因此深植在穆斯林的腦海裡。

伊斯蘭不僅統一阿拉伯語言,讓古蘭經語言成為宗教、政治、文學、文化的「正統語言」,許多阿拉伯詞彙也因為時代的巨變而注入伊斯蘭精神,更有一些詞彙因伊斯蘭的興起而產生,隨著伊斯蘭的擴張而被其他民族借用,譬如 al-Islām(伊斯蘭)、adhān(禮拜時的宣禮)、mosque(清真寺)、hajj(朝聖)、zakāh(課捐)、ṣiyām(齋戒)等。阿拉伯人為了研究《古蘭經》,運用宗教學的原理制定阿拉伯語言學,使得阿拉伯語言和宗教緊密結合,歷經十四個世紀未曾改變。阿拉伯文學因此融合沙漠遊牧民族的樸質、豁達、無拘,以及伊斯蘭的理性、務實與謙遜。矛盾的美感增添外族難以捉摸的神秘色彩。
伊斯蘭奠定文學「文以載道」的核心價值
《古蘭經》並非像中世紀許多阿拉伯學者習慣撰寫的巨書,而是人人可以攜帶行走的一本書冊,也是第一本阿拉伯文學作品,採韻文體(saj‘)。阿拉伯人不將《古蘭經》歸類於詩體或散文體,而稱是「奇蹟」。因為其中的蘊含無論在語音、音韻、詞彙、句型結構、語意、修辭、意象、編輯邏輯上,都是橫跨千餘年學者畢生鑽研卻仍無法參透的「奇蹟」。阿拉伯語文的深奧在此經典中得到最好的印證,文學家以此經典作為最高典範。
《阿拉伯文學史》中提及七世紀穆罕默德及正統哈里發時期,無論詩、講詞或訓囑等都充滿宗教色彩,內涵無非在讚頌穆罕默德和正統哈里發、護衛或闡揚伊斯蘭信仰、宣揚統治者在宗教上的正統性。譬如「使者的詩人」哈珊(Ḥassān bn Thābit)在詩中威脅多神教徒,闡揚伊斯蘭的光榮說:
基卜里勒(Jibrīl)天使是阿拉的使者,
他聖潔的靈魂無以倫比。
阿拉說:我派遣了一位僕人,
試煉人們,
宣揚真理。
我信賴他,
你們起來相信他吧!
你們卻說:
我們不起來,
我們不要。
阿拉說:我派遣了軍隊,
他們專門作戰,
是贊助者。
哈珊在哀悼第一任正統哈里發阿布─巴克爾(Abū Bakr)時吟道:
他是第二位德行被讚揚的人,
是第一位信任阿拉使者的男人。
山洞裡兩者之一,
他爬上山時,
敵人環繞著他。
凡阿拉使者之愛,
都知道他無以倫比。
又如阿布─巴克爾就任哈里發之位的講詞:「人們啊!我來領導你們,但我並非你們中最傑出的。倘若你們看到我是對的,就請幫助我。倘若我是錯的,就請糾正我。若我順服阿拉,你們就服從我。若我違背阿拉,就切勿服從我。對我而言,你們之間的強者,是我須賦予他權利的弱者。弱者,是我須剝取他權利的強者。這是我所說的,我求阿拉寬恕我,也寬恕你們。」闡明伊斯蘭的政治觀在順服阿拉並以民為本,成為經典的講詞。
穆罕默德的書信則奠定阿拉伯文書信的格式:「奉大仁大慈主之名:阿拉使者穆罕默德致卡立德・本─瓦立德(Khālid bn al-Walīd)。平安!讚美唯一的真主。你託使者帶來的信,告知哈里史・本─克厄卜(al-Ḥārith bn Ka‘b)族人在開戰之前就信奉了伊斯蘭,回應了你對他們的呼籲,也立下阿拉是唯一真主,穆罕默德是阿拉使者的證詞,阿拉以正道引導他們。你跟他們報福音,警示他們。你請回來,讓他們的代表團也隨你而來。祝你平安,阿拉祝福、憐憫你!」沿襲至今,阿拉伯文書信開頭要寫:「奉大仁大慈主之名」,接著是寄件人及收件人名稱,然後是問候語、讚美真主之詞,再進入信的主題,信完成之後仍需要再寫問候語。
凡此,都顯現伊斯蘭早期的文學在服務宗教,蒙昧時期的情詩、酒詩等主題在此期淪為詩作的點綴,無法登大雅之堂。以伊斯蘭為中心的觀念引領文學,塑造往後阿拉伯文學「文以載道」的核心價值。此後儘管文學逐漸回歸世俗主題,但引用《古蘭經》和聖訓,藉以佐證作者思想的正統性或表達虔誠的信仰,成為詩人與作家的行文方式,《古蘭經》的修辭藝術也成為文人努力達致的目標。
伊斯蘭在文學裡的內化
隨著時代的演變,宗教深入人們的生活中,儘管伊斯蘭思想仍出現在各種文體及各類主題中,卻不再是乏味的教條宣導,而是以較有趣且多元的形式與文學結合。宗教不致成為「愛情」或「酒」的束縛,而是內化的思想與精神,譬如伍麥亞(Ummayyads)時期著名的「烏茲里情詩」(al-Ghazal al-‘Udhrī)便呈現敬畏阿拉的「愛情道德」,且看加米勒(Jamīl)對他的情人布塞納(Buthaynah)吟道:
我對阿拉,
不對人們,
訴說我愛她的苦。
受驚嚇的愛人,
難免牢騷滿腹。
妳難道不畏懼阿拉,
妳殺了順服、謙卑的人。
文人談到「死亡」時也呈現伊斯蘭思想,認為死亡是掌握在阿拉手裡,是從今生到後世的過渡階段,不是結束,每個靈魂在最後審判日都得甦醒,接受審判。加米勒在詩中便說:
願神再賜我一次,
主將知道我多麼的感恩。
倘若她索取我的生命,
我會獻上它、捨棄它,
若這是我能決定的話。
他又說:
主啊!我依賴祢!
布塞納在今世離我如此遙遠,
但可不要在最後審判日啊!
求祢在我死後讓我與她為鄰,
若她與我的墳為鄰,
死亡會多麼美好!
伊斯蘭在文學裡昇華
儘管伊斯蘭早期文學受《古蘭經》影響甚鉅,作品中常呼籲人們莫過度迷戀今生,莫忘死亡和最後審判日,但堪稱伊斯蘭苦行文學者,卻遲至阿巴斯(Abbasid)時期才出現,回應當時社會的奢糜和異端的盛行。
伊斯蘭苦行文學旨在遠離俗世物質的享樂,以求接近阿拉。其中阿布─艾塔希亞(Abū al-‘Atāhiyah)是箇中翹楚。他所有的詩作幾乎都在呼籲人們畏懼阿拉,遠離塵世。他在長達四千節的〈俚語〉(Dhāt al-Amthāl)格言詩中說:
倘若事物不在,
它是多麼的遙遠!
倘若事物存在,
它是多麼的近!
活人靠死人的遺產生存,
房屋靠廢墟而長存。
阿布─艾拉俄・馬艾里(Abū al-‘Alā’ al-Ma‘arrī)表達他的苦行時說:
夏天,
你只需遮羞的衣裳,
入冬,
只需一件粗衣。
我的行程無需錢財,
出外流浪,
身無分文。
不求糧餉,
真主賜我充足食糧。
倘若有人施捨,
我深知那並非我的權利。
阿布─塔馬姆(Abū Tamām)對生活凝視時說:
若真主要闡揚被掩蓋的德行,
就會賜予它忌妒的舌頭。
若非有火的燃燒,
怎知檀木的芳香。
苦行觀念發展至極的蘇非主義(at-taṣawwuf)文學,除了談論苦修、棄絕塵世之外,尚擅長述說神愛,把愛情由物質昇華到精神境界,表達對真主特質的冥想,如阿布─哈珊(Abū al-Ḥasan an-Nūrī)的詩:
多少的悲傷,
苦得令人哽咽,
令此心也傷,
對泣者肅然。
你據理讓我哭泣,
讓我毀滅,
我因你而哭,
或需與你相會。
又如薩門(Samnūn)著名的神愛詩句:
除了你,
我別無所幸,
你意欲為何,
請試煉我。
伊本─艾剌比(Ibn ‘Arabī)的神愛則說:
我主的愛啊!
求你不要拋棄我,
生存如此無趣。
此心所愛無人,
唯願所愛顯現。
伊斯蘭是阿拉伯文學的依歸

綜觀整部阿拉伯文學史,歷代總有一些阿拉伯文人因為作品觸犯宗教禁忌,而遭撻伐或迫害,最顯著的例子便是人類創意的代表作──《一千零一夜》在二十世紀和二十一世紀都曾因語言淫穢、露骨,成為埃及法庭的被告。又如有「女人與愛情的詩人」之稱的現代詩人格巴尼(Nizār Qabbānī)因為詩中充滿挑戰伊斯蘭的言詞而遭撻伐,譬如他呼喚月亮說:「懸掛的大理石主啊!」對女人訴愛時說:
妳對我莫害羞,
這是我的機會,
讓我成為主,
成為使者。
「文以載道」的觀念既是傳統也是永恆的價值,導致「脫序」的文人屢屢遭受惡評與撻伐。回顧《一千零一夜》故事中的善與惡、美與醜、生與死、罪與罰……等都在彰顯伊斯蘭價值,內容甚至提及許多《古蘭經》的故事,譬如所羅門王的精靈:赫魯特(Hārūt)和馬魯特(Mārūt)的法術,[1]伊斯蘭色彩濃厚,但也難逃伊斯蘭道德檢驗,古今皆然。因此,儘管伊斯蘭千餘年來與文學創意相輔相成,是文人腦力激盪的元素、靈感的泉源、思想與感情的依歸,但「伊斯蘭的文學」究竟如何讓文學跳脫傳統的藩籬,讓文學本質毫無牽絆的發揮,著實是當代文學嚴肅的議題。
(本文作者為政治大學外國語文學院院長)
[1] 《古蘭經》中(2:102)他倆是巴比倫兩位天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