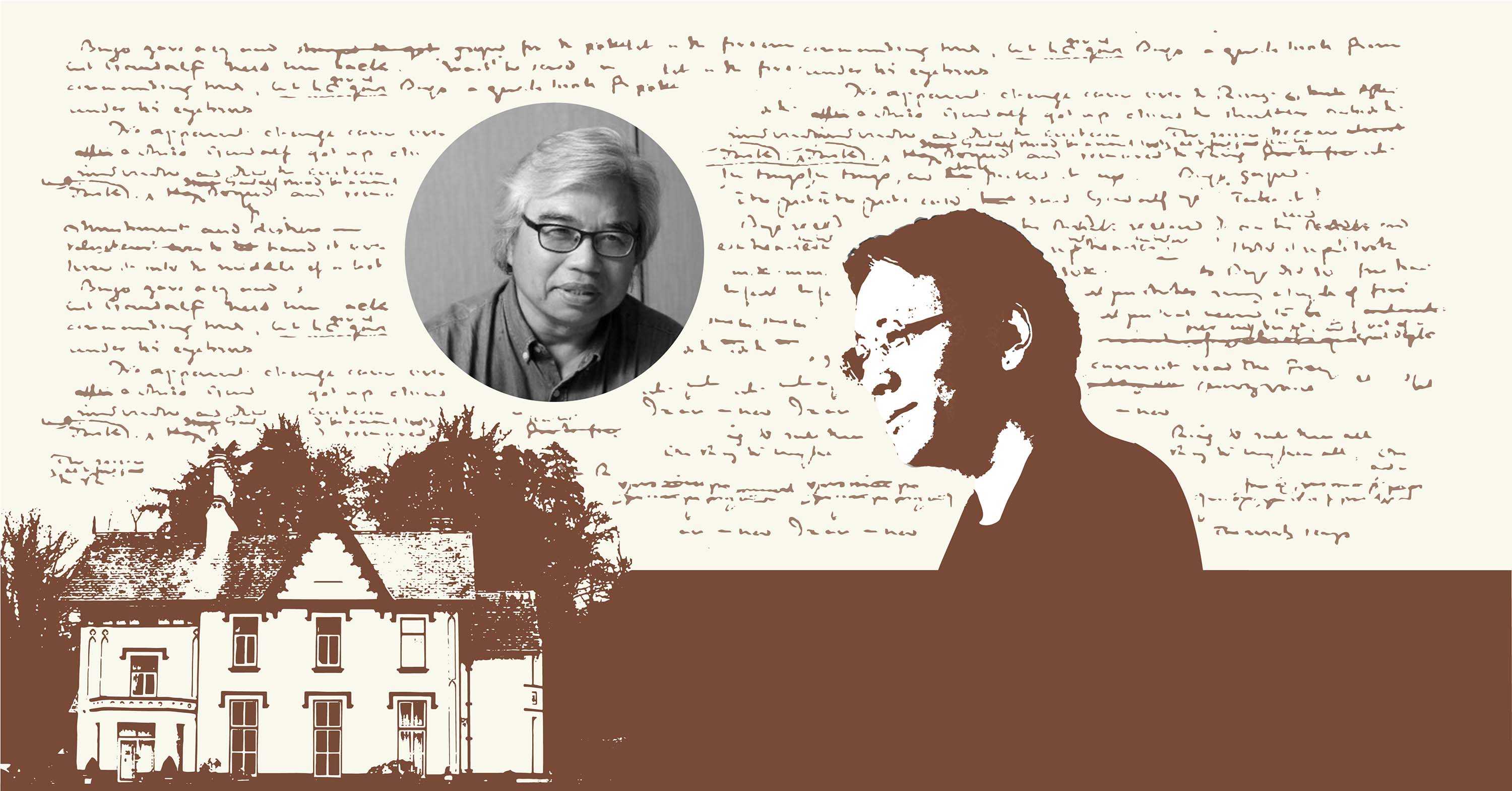三島由紀夫著,唐月梅譯,《金閣寺》,臺北:木馬文化,2018
1950 年 7 月 2 日的凌晨,鹿苑寺舍利殿(金閣寺)被大火吞噬。1956 年,三島由紀夫藉此事件所創作的長篇小說《金閣寺》問世。
這本小說以名為「溝口」的少年角度敘事。有口吃問題的溝口,從小受到父親的影響,一直將「金閣寺」視為世界上最美麗的事物。父親去世之後,溝口被託付給父親的好友,即鹿苑寺住持撫養,溝口在寺居生活中認識了另一名少年鶴川。
沈迷於金閣寺之美的溝口,不斷期望著金閣寺能毀於二戰空襲烈火,卻未能實現。進入大學之後,溝口和同學柏木交好。翹課遊樂、善於調戲女子的柏木為溝口開啟了另一個世界,溝口在柏木的安排下時常有與女子發生關係的機會,但溝口每每在慾望驟起當下浮現金閣寺的身影,終至無法完事。
有一次,溝口撞見住持嫖妓,並藉此捉弄住持,無心於學業的他也逐漸加深了住持對其的厭惡之情。為了擺脫金閣寺之美的束縛,溝口離寺旅行,並立下焚毀金閣寺的目標。回寺後,鶴川自殺的消息震驚了溝口,自己亦因種種脫序行為不再見容於寺中。未能等到住持將自己驅逐,溝口在一個夜晚點燃火苗,燒毀了金閣寺。
三島由紀夫筆下的金閣寺,成為不斷困擾溝口的源頭,這座「美」的化身也成為小說的最大主題。隨著情節推進,金閣寺為何逐漸成為非得親自毀之的目標,其中溝口的思緒變化便值得分析。童年時期的溝口,因為對自己結巴的厭惡,內心幻想自己成為暴君:
我沒有必要用明確而流暢的語言來使我的殘暴正當化。因為只要我寡言就可以使一切殘暴正當化。⋯⋯我還樂於幻想我成為內心世界的國王,成為冷靜觀察的大藝術家。儘管我外表貧弱,精神世界卻比任何人都富有。少年抱有一種難以拂除的自卑感,認為自己是被悄悄挑選出來的,這不也是理所當然的嗎?總覺得世界的某處有我尚未知曉的使命在等待著我。[1]
溝口所想像的暴行,是對美的破壞,他破壞海軍軍校學生的劍鞘,「在美麗的短劍黑劍鞘裡側,深深地劃了兩、三道難看的刀痕⋯⋯」溝口暗戀的村中少女有為子,因為庇護逃兵而死,溝口得不到有為子的美,便詛咒見證自身醜陋恥辱的有為子死去。溝口認為,當世界死滅後,自己才能面向太陽。此時的溝口認為,破壞這些人世間的美麗,才有活下去的可能。
父親死後受到住持照顧的溝口,在戰時不斷期待著金閣寺的毀滅,然而,這時溝口的內心抱持著的是一種「同歸於盡」的陶醉、美妙感受,醜陋的溝口和美麗的金閣寺都能隨空襲的烈焰而消逝。溝口和金閣寺站在同樣脆弱的地位上,因此「這麼一想,我似乎可以把金閣藏在我的肉體裡,藏在我的組織裡,然後潛逃,就像潛逃的盜賊把昂貴的寶石咽下、藏匿起來那樣。」[2]但隨著期待落空,金閣寺不會再受到戰火威脅,便轉而成為一種永恆、不死的美,疏遠了溝口。
戰爭結束後,溝口從鶴川的口中聽聞了對世人惡行的描述,因此思索:
此處所指的惡與黑暗,是相對於美的存在,亦是摧毀美的力量。我們可以推測,溝口對口吃的自卑使他產生了將自己塑造成黑暗的想法,透過成為黑暗、成為邪惡,溝口想像自己具有讓世界死滅的力量,掩飾自己的缺陷。有一次,溝口受到美軍遊客的逼迫,踩了一名妓女的腹部導致其流產,這開啟了溝口行惡、摧毀金閣的念頭。
溝口在大學結識的友人柏木,有著「醜陋的 X 型的腿」,但柏木接受、合理化,甚至利用了自己的殘缺,讓女人憐憫,為其獻身。如果說開朗的鶴川化除了溝口的黑暗,消解了結巴的自卑和缺陷,柏木的存在,則毫不隱諱地強調了殘疾的事實存在。如果說鶴川撫平了溝口自我厭惡的痛苦,那柏木就讓溝口看見、走向自身醜陋的黑暗。
然而,溝口沒有依循兩人的路徑行走,他終其一生是被金閣的美所束縛住的。金閣寺拒絕、疏遠溝口,但永恆的美卻又保護著溝口,阻卻了他體會瞬間的、作為生(命)的美:
金閣寺拋棄了醜陋的溝口,也不允許溝口嘗試生命的滋味。三島由紀夫的筆法毋寧解釋成溝口對「生為一名正常人」身份的拒絕,走向了逃避探索短暫的、生命的美的可能性。
隨著象徵著帶來光明的鶴川死去,溝口喪失了被鶴川肯定「生」的機會,漸次的、模糊的產生了和金閣寺不相容的心態。這個心態是溝口欲強調的自我獨特性和孤獨性,他不要和芸芸眾生同活:
我無意仰仗社會支持我的思想,也無意為了容易被社會理解,而將框框套在自己的思想上。正如我一再說過的那樣,不被人所理解才是我存在的理由。[5
在世間上,除了溝口的特殊性和金閣寺的永恆,餘下的便是作為人而不斷湧將出現的罪惡。在溝口的想法中,殺人是「無濟於事」的,因為人雖然死了,但人類仍將繁衍,將惡傳續下去。相較之下,永恆的金閣寺反而得以一次性的摧毀。這樣的發現,使得溝口感到從無力、束縛的金閣寺中解放出來的可能,將金閣寺燒掉的念頭,便由此確立。
我們可以由此回觀,溝口最初從金閣寺中體現了自我的醜劣,卻無法與其共亡。溝口逐漸區分出金閣寺終究是無法追尋的存在,勒住了他的生活,金閣寺的美讓溝口感到無力,成為了他的怨敵。因此,從燒毀的金閣寺中解放自己的生命便成為必然,「黑暗的力量又立即復甦,把我從那裡帶了出來。我還是一定要把金閣燒掉。另一種我特別製造的、前所未聞的生,將從那時開始。」[6]世界將少了一些美的重量,世界的意義將會改變……。
溝口的金閣寺確實付之一炬了,然而,如此是否就如溝口認為的「我內心世界與外界之間這生了鏽的鎖頭,即將被巧妙地打開」呢?[7]在溝口點燃火苗前,他的內心獨白是「儘管心靈的一部分仍執拗地告訴我,此後我該做的事是徒然,但我的力量變得不懼怕白費了。因為是徒然,才是我應該做的。」[8]溝口認為,唯有行動才能改變世界,但當他「認識」到火燒金閣寺的結果、釐清自己內心的想法之後,是否真正行動與否,反倒失去了意義。
綜觀前文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金閣寺》中溝口自主意識逐漸萌芽的過程。一直以來,溝口不敢和正常人互動,被動的和鶴川交往、被身體缺陷制約,又在「以成為住持為目標」定型的人生中掙扎,但在看似瘋狂的種種對生命意義的摸索:嫖妓、出走、對金閣的破壞中,溝口試圖衝破這些,以金閣為象徵的一切阻礙。最後,溝口決定活下去,不再自我封閉,踏出和社會正常互動的一步,即使這樣的嘗試不一定會被社會所接納。
然而,即使燒毀了金閣寺,但溝口心中時時縈繞盤旋的金閣寺,是否因此隨之散去了呢?我認為,溝口大概仍無法掙脫這座束縛著內心,被視為怨敵的建築吧。溝口斬斷了金閣寺的物像,但內心卻仍然惦記,無法拋卻已深深烙印、糾纏的「美」,自父親介紹金閣寺以來,這個兼有美好、枷鎖、痛苦於一身的物件,已牢牢的和他的生命綁在一塊了。在實際歷史中,金閣寺縱火事件的主嫌林承賢最終在獄中病死, 現實中的金閣寺則在之後更加鮮明、堂皇而傲立不滅。這樣的景象,對如溝口這種試圖打破禁錮的人來說,必定是悲哀的罷?社會所加諸於人的,名為美的牢籠(這個牢籠對於其他人來說,可能是美以外的其他形式),不但不毀,反而又更加堅固,無法逃離了。
(本文作者為臺大歷史系學生)
[1]三島由紀夫著,唐月梅譯,《金閣寺》,臺北:木馬文化,2018,頁 7。
[2]三島由紀夫著,唐月梅譯,《金閣寺》,臺北:木馬文化,2018,頁 52。
[3]三島由紀夫著,唐月梅譯,《金閣寺》,臺北:木馬文化,2018,頁 77-78。
[4]三島由紀夫著,唐月梅譯,《金閣寺》,臺北:木馬文化,2018,頁 136-137。
[5]三島由紀夫著,唐月梅譯,《金閣寺》,臺北:木馬文化,2018,頁 199。
[6]三島由紀夫著,唐月梅譯,《金閣寺》,臺北:木馬文化,2018,頁 212。
[7]三島由紀夫著,唐月梅譯,《金閣寺》,臺北:木馬文化,2018,頁 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