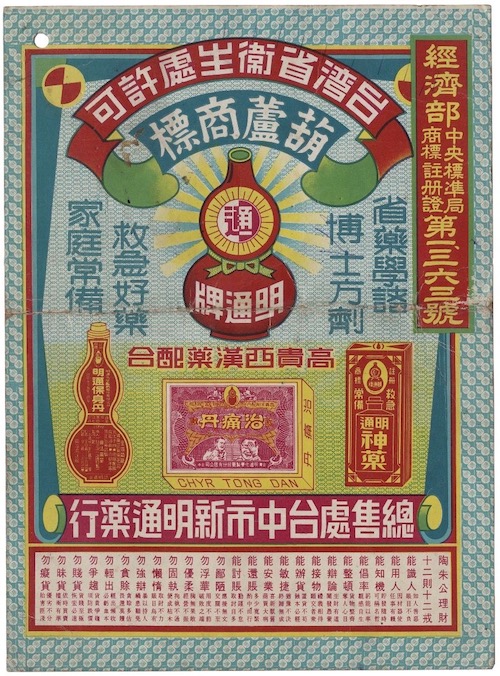自二〇〇四年《瘋狂簡史》中文版出版以來,轉眼已十幾年,事實上這本書已經絕版一段時間了。日前左岸文化編輯孫德齡小姐告知此書將重新出版,並且邀請我寫一篇文章,談談這十幾年來精神醫學與精神醫學史領域的最新進展。
這是個令人振奮的消息。畢竟這本為一般閱讀大眾所寫的瘋狂史,篇幅雖小,其簡明優雅的述說,卻處處展現了羅伊・波特(Roy Porter)這位偉大學者對於瘋狂史的豐富學識與深刻洞見;書中各章主題,也為想要探索瘋狂史的讀者,提供了一個全面的架構。即使年代有些久遠,今日讀來卻仍深具啟發性,也依然能讓人感受歷史思維與歷史書寫的魅力。
只是要我站在巨人肩膀上談這十幾年來精神醫學的發展,卻是個太過艱鉅的責任;又或許在瘋狂這個古老議題的漫長歷史中,這短短十幾年其實微不足道,其進展也並未超出羅伊・波特在本書後幾章中的分析與展望。
事實上,對於此書中文版的再版,除了喜悅之外,我更感興趣的是出版社做此決定的考量。在商言商,這個決定是否意味與十幾年前相比,這本書的利基已經擴大了呢?瘋狂與瘋狂史是否已從一個小眾關心,成為一個更多人感興趣的問題?這些問題關乎這本書再版的銷售前景,而重新出版的決定,可能反映了這十幾年來一些饒富意義的變化。
* * *
記得這本書中文版首次出版時,我剛從一所遺世獨立的療養院,轉至台北市中心一間綜合醫院工作。那時作為一位精神科醫師還經常被周遭親友戲謔:經常與瘋人相處,是否自己也會變得不正常?然而五年不到,在我轉投入醫學史領域之前,由精神科醫師這個工作所觸發的談話,已由嘲謔轉為同理,關心你每天承接那麼多病患的痛苦與壓力,自己究竟如何抒發調適。
不同的對話,反映出一般對於精神疾病與精神科醫師的想像與理解,以及精神醫學與社會的關係,已在短時間內起了很大變化。假如說精神醫學是一門位於邊界且專長治理邊界的科學,今日這個邊界已經由社會邊陲以及個人自身之外,不斷內移而成為難以界定的模糊交境。或是引用羅伊・波特的話,一種以「全人口」為對象的新「社會精神醫學」已經在台灣生根發展,而擁有日益增加的影響力。
想想精神健康議題與廣義的精神醫學,已如何成為我們公共與私人生活的一部分。在社會的層次上,除了傳統醫療領域,藉由精神鑑定、犯罪加害者與受害者評估治療、遊民、藥害、自殺、災難、特教、殘障鑑定與過勞等議題,精神醫學持續地擴大介入司法、治安、教育、社會福利與勞動政策等領域,或至少某種精神科學思維,正讓這些領域的論述與實務發生實質轉變。
在個人層次上,則有憂鬱、焦慮、失眠、成癮、過動、失智、人格違常等層出不窮的診斷,使精神疾病成為一類常態性疾病,而精神健全變為一個必須極度努力才能維持、近乎例外的狀態。不僅如此,在疾病範圍之外,從家庭中的親子、伴侶、手足關係,到學校職場的人際關係,再到個人的自我探索、自我調適與自我成長實現,對於精神衛生專家的指引與介入,也有著更高的需求與接受度。
或許相較於某些西方國家,仍會有人覺得台灣精神醫學的發展不足。但今日台灣社會對於精神疾病與精神醫學的關心,以及對於頂著精神科醫師、心理醫師與各式各樣治療師頭銜的精神健康專家的興趣與熟悉感,已是十幾年前無法想像。求助或被認為需要接受精神醫療的人,也由精神不正常的例外,變為受傷、受苦或承擔壓力的一群。然而世人誰能不苦?對於更多人而言,精神醫學已不是一個關乎他者而是切身的問題。
與此同時,最尖端的精神醫學、心理學、神經科學與生物科學,這十幾年來仍繼續提出各種新發現與新學說,挑戰我們如何了解自己與他人以及我們的生命之道。
一如既往地,這些新概念具有反直覺、反常識的特質,只是更為極端激進,甚至讓人感到荒謬幽默。在前一個世紀,精神分析等新動力精神醫學,曾以其幼兒性欲、童年創傷、多重人格與性學說等理論,在世紀初強烈衝擊當時的社會價值、道德感性以及人們的自我認識與記憶;各種精神治療法特別是精神藥理學的發展,也曾挑起對於壓迫、控制與洗腦的道德疑慮;而憂鬱焦慮等各種輕型精神疾病診斷範圍的擴大,則以疾病與醫療模式,挑戰一般對於不快樂與壓力的認知,而引發了關於醫療化的爭議。
然而到了世紀交替之際,在很大程度上,這些概念已經成為人們自我認識的一部分,不再讓人驚訝或不安,甚至有些陳腐,透過各種實作的擴展,這些抽象概念也已經具體化於日常私人與社會生活之中。只是科學的進展伊於胡底,精神科學還是可以不斷挑戰我們常識與感性的底線。一貫以疾病模式看待異質行為、認知與情緒的精神醫學,繼續提出各種假設性的新疾病概念,或擴大既有概念的涵括範圍,以為更廣泛的醫療介入提供合理性。
於是,在不快樂的成人之後,對於好動不專心的小孩,執拗陰鬱封閉在自己世界的青少年,以及健忘沉浸於過往記憶的老人,我們必須繼續掙扎糾結是否要接受他們罹患精神疾病的解釋,以及是否讓他們接受醫療介入。
秉持依症狀表象界定分類精神疾病的原則,美國精神醫學會《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以「泛」或「光譜」(spectrum)的概念,擴大了某些疾病的涵蓋範圍,甫出版立即引發許多爭議。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一貫對於過度診斷或醫療化的質疑之外,立於發展尖端的生物精神醫學,也從科學角度,對於已通行三、四十年基於症狀診斷分類的原則發出反對聲音。
然而,自視為客觀自然科學的生物精神醫學與神經科學,自新世紀快速發展以來,也未能免於爭議。無論是五顏六色帶有耀眼光芒的神經影像,精細繁複、色彩更為繽紛的基因或神經化學示意圖,或是巨量數字的統計表,以及從其歸納繪成一目暸然的統計圖,一張張散發神祕氣息,甚至比傳統宗教象徵更能震攝人心的視覺圖像,樂觀地暗示科學即將揭露我們正常及病態行為的物質基礎。
但是,當這樣物質化約主義的思維與技術進入社會與個人內在生活中,卻可能帶來許多預期之外的效應。於是,在前一個世紀的精神分析文化與百憂解文化之後,對於正在成形的神經文化與基因文化,也開始出現反思批判的聲音。
至於在實際治療手段方面,至少到目前為止,各種高調的科學發現與理論,並未帶來突破性的進展。但是以一種或許可形容為後現代混搭的風格,精神治療學也持續發展,挑戰我們對於治療的想像與理解。精神科醫師與治療師們從古至今、從西方到東方搜尋各種可用的治療方法,揮灑創意組合搭配出各式處方。
例如,在身體治療上,雖然尚未研發出新的有效化學物質,致力豐富其處方集的精神科醫師,不但將注意力投向他們原本輕視的傳統草藥、方劑與食物領域,也擴展到大麻、安非他命、K 他命等以前因其精神作用與成癮性質而被禁止或管制的所謂「麻藥」或「毒品」。
此外,在前一個世紀引發人道爭議而被認為完全或部分棄用的精神手術及各種休克療法,近年來也被重新審視研究,期待能為停滯的身體治療發展帶來新契機。同樣心胸開放的態度也可見於心理治療領域。事實上,心理治療今日的最新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已與心理學脫鉤,或只有名目的連結。
在個人心理治療上,一方面我們看到電腦化的認知行為心理治療,以人工智慧程式取代真人治療師為個案提供分析與建言,彷彿心理治療是一門客觀醫學,但事實上是出於成本考量;另一方面,則有許多歷史悠久且多源自宗教修行的傳統身心技術,例如呼吸法、內觀冥想、氣功、瑜伽等,被以各種形式及名稱整合進入主流心理治療。至於名目眾多的各種心靈體驗、成長與療癒團體,雖然多半有其自稱的心理學根據或獨創心理理論,但在形式上與內容上,卻往往與傳統宗教或社會儀式難以區分,而可以看出其靈感來源。
如此混搭風的治療學,模糊了治療的定義,讓我們必須重新建立對於治療的理解與想像。它為治療師提供了豐富多元的治療手段,讓他們可以因應為各式各樣精神痛苦前來求助的個案,事實上,求助者也從此開放的治療策略中受惠。然而,折衷主義治療策略終究只是缺少神奇子彈的權宜,它凸顯了精神治療學缺乏突破性進展的窘境,也讓想在實證基礎上運用神祕體驗的精神醫學,在某些方面看來與有復興跡象的神祕主義與超驗玄學難以區分。
* * *
儘管如此,精神醫學的影響力還是持續擴張,而在我們生活中扮演更多的角色。無論在台灣或是其他國家,這都引發了不少的質疑與批判,而且常是出於切身痛苦的抗議。更多人想從醫學與心理學之外的其他觀點,特別是社會學、人類學、哲學及歷史學等人文學觀點,理解精神疾病與精神醫學。近年來,台灣見到不少相關書籍的翻譯出版,這應該也是出版社在十幾年後再版《瘋狂簡史》的背景。
事實上,要批判精神醫學或精神科學並不困難,其對於疾病模式與物質化約主義的偏執、對於主觀經驗與環境因素的輕忽、將假設視為現實的魯莽、強制手段對於人權的侵害、不自知的控制規範心態、對於精神藥物的依賴與輕率使用、以及知識基礎與實作的巨大落差等,無一不是可以輕易攻擊的標的。
作為批判的對象,精神醫學甚至有些過於便利廉價,而使批判失去深度與力道。問題是,何以進展明明極為有限的精神醫學,可以高唱凱歌,一路挺進?顯然地,這與精神醫學專業追求提昇地位及影響力有關。
自十九世紀末以來,精神醫學一方面以其他專科為標竿,致力依據醫學模式特別是生物醫學模式將自己發展為一門真正的科學醫學專科,另一方面則跨越療養院高牆,多層次地介入社會與私人生活。無論出發點是專業、經濟利益或公義,精神醫學的自我期許與野心,推動著精神醫學的擴展。而以跨國藥廠為首,各方藉由精神醫學擴張謀利的團體,也是顯而易見的可能黑手。
此外,在處理問題分子、維持社會安全、解決人民不滿痛苦以及提高人民幸福感受上,現代國家治理也在更多方面對於精神醫學有更深的倚賴,而以公權力及公共資源支持精神醫學的發展,並賦予精神醫學更多角色與更高的權威。因此,台灣精神醫學的擴展與民主化在時間上的重疊,也許並不只是一個巧合。現代政治體制中,國家權力的合法性許多來自科學治理與對國人福祉的照顧,這使其與聲稱照護心靈的精神醫學一拍即合。
然而,除了這些似乎懷有陰謀的特定力量,我們也不能忽視個人與社會對於精神醫學的需求。雖然有其局限性,精神醫學確實為某些造成困擾的疾病或現象提供解釋,也的確提出一些有效率且部分有效(雖然可能有副作用)的解決方法,改善了許多病患的精神痛苦。若不具有一定的有效性與使用者滿意度,精神醫學也不可能持續擴張。
更重要的是,精神醫學的發展,並不是完全來自外部力量的蠱惑或強制,而是在社會文化內孕育形塑。
對於精神醫學思維與精神醫療的接受與需求,有時只是不得已的選擇。在其他資源已經瓦解或尚不存在的情況下,精神醫學可能是唯一尚可接受的解決方案。但是更多時候,精神醫學與社會主流文化有著高度親近性,彼此提供養分相互纏繞蔓延,使精神醫學成為當代文化的一個重要縮影與表徵。無論是十九世紀末的中產階級文化,或是二十世紀下半葉的受害者文化、自戀文化與治療文化,都為精神醫學的擴展提供了適合環境,也讓精神醫學專業可以振振有詞地辯護他們是在解決既有問題,而非創造問題或需求。
同樣地,台灣近十幾年來精神醫學的快速普及,與其說是精神醫學專業及國家權力以強制或誘騙手段所進行的介入,還不如說精神醫學在當代社會文化中同時發現了多處適合其發展壯大的利基。面對尖銳的批判,精神醫學其實無所畏懼也自覺問心無愧:在現實環境中,對於現代人的憂鬱、焦慮及不滿,或是對於過動不專心的問題小孩以及衰退需人照護的長者,還有人能提出符合主流認知架構與價值,而又有效且具可行性的解決方案嗎?雖然這樣的自負之所以能夠維持,環境因素其實與精神醫學自身的努力同樣重要。
無論如何,對於越來越多人而言,精神醫學已不再是一門只關涉他者的科學或醫學,而是更切身、更迫切要求理解與採取立場的問題。即使不想捲入精神疾病是否真實存在或只是人為建構這樣無窮的玄學爭論,一些較細節、較實務性的問題,例如現行診斷標準與診斷方式是否過於武斷草率,藥物或五花八門的各種心理治療是否適當、有效及安全,照護精神病患的資源是否不足又應如何分配,以及精神醫學醫療模式與教育、司法及社福等傳統領域如何接軌等,已成為許多人每日生活中真實面對且必須作出決斷的疑問。
以其獨特的自我觀點與自我技術,精神醫學原本就相當引人關注,只是現在更多人關心精神醫學,並非出於好奇或追求思辨樂趣與道德優越感,而是源於痛苦、徬徨、尋求拯救或是憤怒。批判或否定精神醫學並不困難,拒絕精神醫學卻是另一回事,其所引發的複雜心理與實際效應,若非擁有異常豐富的資源或是偏執者,並不容易承擔。
面對這樣必須採取立場的迫切性與兩難,了解瘋狂及精神醫學的歷史或許會有一些幫忙,雖然它所提供的協助,並不在於讓我們了解瘋狂的真相──事實上可能也不存在所謂的真相,也不在於揭開精神醫學的暗黑內幕或讓我們做出「正確」判斷。
歷史可以給予我們的啟發,只是讓我們了解瘋狂問題的久遠與複雜性,以及現下處境的時代性。即使只看羅伊・波特這本小書的各章主題,從超自然到自然,從歌頌到貶抑,從監禁到解放,從心靈到身體,從主觀到客觀,一方面精神醫學有其一貫的堅持與盲點,另一方面我們不仍還是在同樣框架裡理解瘋狂這個古老問題與爭議嗎?這樣的領悟是否能夠讓我們暫時跳脫當下,在歷史中找到一個可以稍事喘息的立足之地,撫慰我們的焦慮?
(本文作者為中研院史語所助研究員)

在當時的認知中,他們瘋狂的起因為何?
社會又是如何處置這些瘋狂的人?
本書爬梳了從以神魔力量解釋瘋狂的起源開始,
古希臘羅馬時期的理性化醫學理論,
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傳統對於瘋狂的禮讚,
十七、十八世紀對於瘋人的監禁,精神醫學的興起,
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有關瘋狂的理論,
二十世紀的精神分析,一直到現代精神醫學治療模式的這段瘋狂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