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碎的桌邊小說
熟知村上春樹創作歷程的書迷都知道,他是在棒球場上突然有了寫小說的念頭[1],但從「覺得自己可以寫小說」到真正寫完《聽風的歌》並投稿,他其實為了尋找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語言」,苦惱了很久,最後決定先用英文寫初稿,再以日文重新將文字轉譯,才順利完成了這第一部小說。
當時的村上,還是爵士餐廳的老闆,只能在每天關店後就著餐桌利用零碎的時間進行寫作,因此他稱自己的頭兩部小說為「Kitchen Table Novels」,而或許也是因為沒有時間組織更完整的架構,《聽風的歌》與《1973 年的彈珠玩具》在劇情上都不免有些破碎。然而,在這樣零碎到不成「精彩故事」的文章,卻自成一個迷人的宇宙,那些模糊的情感、浮動的關係、無法說出意義的行動,觸動了同樣陷在這種迷惘情緒的少年少女們。也因此,對於有些村上迷如我,這本小說就彷彿私房清單一樣,沒有這麼符合大眾口味到能推薦給其他人,但卻是同好之間能相互辨認的信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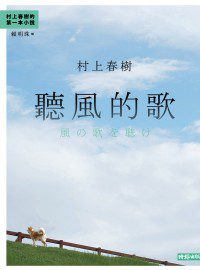
《聽風的歌》中沒有明確的劇情主線,一切都圍繞著主角「我」在 20 歲時所遇見的人與發生的事情展開。主角與朋友「老鼠」成天混在「傑氏酒吧」中,喝著驚人數量的啤酒,一邊聊著不著邊際的事,一邊醞釀著想寫的小說。
即使文體是如此「輕描淡寫」,但提及的故事卻有著沈甸甸的重量,「我」的前任女友在樹林裡上吊自殺(《挪威的森林》的女主角之一直子也是這樣離開人世),在酒吧偶遇的女人則剛拿了一個小孩(《國境之南、太陽之西》裡的島本也在河邊埋葬了自己夭折的孩子),「我」所崇拜的虛構小說家哈德費爾則懷抱著未竟之志墜樓而死。
就像村上春樹日後的許多小說一樣,這本書裡瀰漫著死亡的氣息,這或許與他身為學運世代的經歷有關,如同活過同時代的日本作家川本三郎在《我愛過的那個時代》中寫到:「日常生活中到處都有人死掉,生的中心就有死,而且「我們」並不避開那死,反而想去親近。」生與死之間界線的模糊,也就此成為村上春樹小說中的基調。
平易近人的「僕」
以第一人稱寫作的日本小說不少,然而與傳統日本「私小說」中以大量暴露自我的告解/白風格不同,村上春樹筆下的那個「我」(日文原文為「僕」)對於自己的人生時而顯得漠不關心,乍看甚至是性格淡薄到沒有存在感可言,與其說他們是書中的主角,不如說他們其實是個觀察者,映照出身邊其他生活曲折的人物有多麼獨特。
在處女作《聽風的歌》中也是如此,主角偶然在酒吧遇見、只有九個手指頭的神祕女性,身為有錢人卻在初登場就大喊「有錢人,全部都是狗屎!」的老鼠,甚至連主角的前女友都有著戲劇性的經歷(在森林裡上吊自殺、遺體在森林中吊掛了兩個禮拜才被發現)。
也因為這些主要敘述者是如此平易近人,讓讀者就像聽朋友聊天一般,輕鬆的走進了小說中的故事裡。這不禁令人聯想到村上春樹在成為小說家之前的工作,作為酒吧老闆,他必須一反原先內向安靜的性格,去聆聽手下店員以及顧客的心聲與意見,在這裡他遇見了形形色色的人,自然也聽見了各式各樣的故事,這段時光的累積,或許也成為了他初期寫作的養分。
這樣以平易近人的「僕」作為主要敘述者的寫作模式,直到《海邊的卡夫卡》開始才有了改變,此後的幾本長篇小說,因為格局越拉越大的緣故,他也不得不以第三人稱視角來描述腳色的故事,尤其在人物繁雜並且多線進展的《1Q84》裡,全知視角的寫法也只能說是不得不為的做法。儘管如此,在新作《騎士団長殺し》(暫譯:騎士團長殺人事件)中,他又重新拾回孰悉的第一人稱,對於習慣這種距離的讀者來說,也算是個好消息吧。

模仿不來的「春樹體」
雖然村上春樹初試啼聲之作就獲得了「群像文學雜誌」的新人獎,但他獨特的文字卻也在日本文壇掀起了不少批評聲浪,有些評論者甚至指責他「使日文崩壞」。對於透過賴明珠小姐的翻譯走進村上世界的台灣讀者來說,比起其他譯本的讀者來說,或許更能深刻感受到村上文字的特殊性,認為自己是忠於原作文字的賴式翻譯,同樣也使得台灣對於村上春樹的小說形成了兩極化的平價。喜歡的書迷認為這是作家獨有、想模仿也只會顯得東施效顰的「春樹體」,討厭的則覺得這是刻意賣弄讓人難以讀懂的文青作風。
即使褒貶不一,但村上春樹確實在處女作就找到了屬於他自己的聲音,這對於新人作家來說是再重要不過的一件事,讓你的作品在茫茫書海中展現辨識度,讓人一翻開書就知道這是出自你筆下的作品。他擅長用充滿想像力的比喻,讓抽象的情感一下子具象化起來,比方說寫無法重回的青春時光,他這樣寫:「海潮的香、遠處的汽笛、女孩子肌膚的觸覺、潤絲精的檸檬香、黃昏的風、淡淡的希望、還有夏天的夢⋯⋯。但是這些簡直就像沒對準的描圖紙一樣,一切的一切都跟回不來的過去,一點一點地錯開了。」除此之外,愛用數字、喜歡用綽號而非名字稱呼角色、喜歡在對話中提及關於動物的冷知識等等特點,都在第一本小說就令人印象深刻。
所謂完美的文章並不存在,就像完美的絕望不存在一樣。
這不是一本完美的小說,但它恰到好處的留白,讓讀者得以用自己的經驗填空進去,我們都活過那段懵懵懂懂的青春時光,也曾經不可避免地失去重要的人或事,被殘酷的世界傷害,也因為一己的自私而傷害了別人,這樣的基調成為村上春樹日後小說中的主旋律。在混亂的社會中,也許我們都需要靜下心來,側耳傾聽風的聲音,即使此時此刻在你頭頂上吹著的是惡風,彷彿不管做什麼都無法順利,但是只要等待風的轉向,我們就能重新找回生活的力量。《聽風的歌》寫的就是這樣的一個故事。
[1] 根據村上春樹自述:「1978 年 4 月,有一天我突然想寫小說。那天的事我還印象深刻,當天下午我正在看棒球,坐在外野區,一邊喝著啤酒。我最喜歡的球隊是養樂多隊,當天是和廣島隊比賽。養樂多隊在一局下上場的第一棒是個美國人,大衛‧希爾頓。我記得很清楚他是當年的打擊王,總之,投出的第一球就被他打到左外野,二壘安打。就是那時我起了這個念頭:我可以寫一本小說。這個念頭就像突然從天而降的啟示,沒有理由、無從解釋。那只是突然湧現的一個念頭,一種想法。我可以啊,時機已經成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