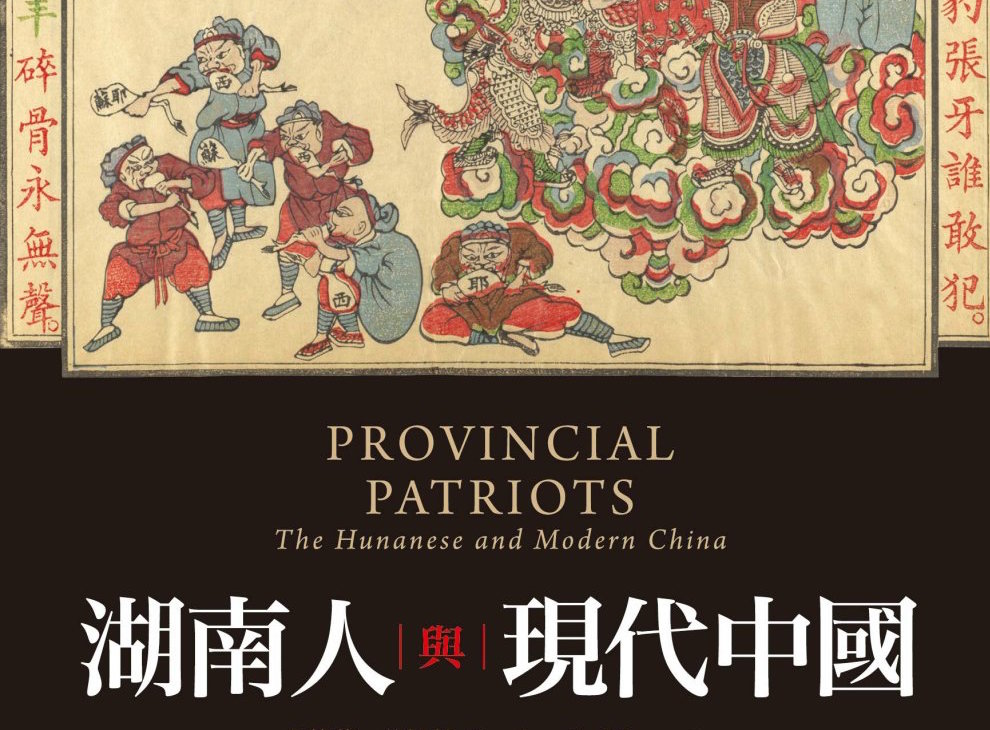咖啡、母乳、百貨公司、跑馬跑狗和回力球賽,從不同的具體物象切入討論現代中國的形成,此種「異國事物轉譯」的研究近年來頗有蓬勃發展的趨勢。相比起這些別出心裁的視點,《鐵路現代性:晚清至民國的時空體驗與文化想像》挑選我們當下接觸頻率極高的鐵路作為主題,興許還不夠有吸引力,不過本書於問題意識上與眾不同的關懷,便足以勾起讀者的好奇心。
作者長年浸淫文化研究,一開始便靈巧地反省鐵路研究可能存在的各種敘述套路,整理出「現代性神話」和「技術神話」兩類八股。前者把鐵路當作現代性的象徵,實質卻使之淪為空洞的能指,「鐵路」可以被置換成輪船、飛機、電報等(乃至前文提到的那些事物),最終無非又在書寫一套大同小異的現代性神話;後者則過於突出「物革命」的重要性,沒有覺察到巨變的背後是舊經驗和新現實一系列的殘酷角力。比較之下不難發現,屬於「物」的歷史被無情剝奪了。
因此作者從現象學的角度,提出一種以物為主體的理論。理論化「鐵路」這個物象本身,從語言學的角度可以這麼理解:所謂「鐵路現代性」貌似「現代性」的氣勢更大,可將「鐵路」死死壓住,但作者卻認為,「現代性」未免有裝腔作勢之嫌,這個概念也從來不是「鐵路+現代性」的偏正結構,中心語其實落在「鐵路」身上,鐵路之所以為鐵路,是因為它以自己的方式聚集起現代性的世界。因此更值得問的問題應該是──鐵路如何開啟現代中國?
正因現代人無時無刻不進行的通勤和旅行,我們對鐵路再熟悉不過。如何回到經驗徹底自然化之前,客觀還原鐵路這種異國事物進入、衝擊和引領中國的全過程,須用不同於以往的論證策略重新蒐集、闡釋過去被拒絕的文本。在傳統的框架中,器物的引進一直被視為失敗的嘗試,更不用說接下來的比附性、想像性的科學認知(例如康有為對聲光電化的認識)。對於這些一度被判定為不夠「現代」的經驗,作者並不貶低,反而予以了前所未有的重視。
本書圍繞語言、視覺、事件、國家、運動和他者設計了六個章節,涵蓋「鐵路」作為全新事物進入中國人視野所必經的全部階段。總而言之,我認為有三大特色值得關注:(1)日常鐵路概念的問題化(第一章);(2)直觀鐵路經驗的還原(第二、五、六章);(3)民族-國家意識形態的「鐵路」脈絡化(第三、四章)。這些特色相互支援,相輔相成,共同構築了一幅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鐵路中國」的多彩圖景。
作者首先將有關鐵路的日常概念問題化、歷史化。如「鐵路」、「火車」和「時間」,指出事物命名的背後靶向完全不同質地的感覺結構,即必須承認:被鐵路打開國門的晚清中國人、命名鐵路的普魯士人以及整天活在鐵路周遭的我們三者,都在以各自的方式表達與鐵路有關的經驗。
通過檢視晚清從「轣轆路」到「鐵路」的命名演化,作者發現,最終引起改變的,既不是認識論水準也不是語言學規範,所謂的科學未必按現代性的時刻表如約而至,畢竟鐵路從來就不是字面意義上的「以鐵鋪就的路」,相關詞語也不見得說明人們對鐵路的認識日趨理性。真正引起變化的,毋寧說是愈發豐富的新經驗對舊經驗的覆蓋和改寫,從而開拓了一個供「傳統」與「現代」相互創造的界面。
還原清末民初中國人的鐵路經驗,堪稱本書最有趣的部分。我們此前無感,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現代性的日常化已讓我們難以有動力去參透經驗背後的深刻意義。
除此之外,鐵路遊記中的風景書寫長期以來被忽視。通過細緻地文本鈎沈,作者發現了在鐵路旅行中,瞿秋白曾情不自禁地將他所看到的西伯利亞雪景和中國的傳統山水畫聯繫起來,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黎庶昌、薛福成和朱自清等人的身上,說明觀看異邦風景時回歸傳統美學參照系的現象,具備一定的普遍性。
關於《點石齋畫報》的觀察更為精采。書中提到,中國第一條自行修建運營的唐胥鐵路,曾出現過的「馬拉火車」一向被視為落後的象徵。作者首先將「馬拉火車」這一飽受批評的視覺符號與「傳統愚昧」的意識形態偏見脫鉤,並舉出多項例證,表示在同時代的歐美也有「馬拉火車」的存在:例如多倫多老北站的騾馬街車(1889)和倫敦的馬拉有軌街車(1890)。如此一來,原先被簡單化的二元對立便十分可笑了。

受這種演示的啟發,作者重新分析了《點石齋畫報》中各種千奇百怪的火車意象。如〈水底行車〉和〈海外奇談〉,表面上好像是為了報導西方時事,傳播隧道的技術和知識,然而報道同樣內容的《倫敦新聞畫報》(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注重客觀還原,如實報導,這兩幅畫卻充滿奇想,更強調水底行車、火車入海的夢幻體驗,說明看似科學、客觀的報導,實際上卻為荒誕的想像、非理性的故事創造了條件。
正如《點石齋畫報》中的火車並不必然、直接地與現代性、科學技術綁定在一起,作者話鋒一轉,指出有關巨龍──這一傳統中國的經典意象的視覺再現,也非總是承載著迷信與傳統。
更為荒誕的〈西人見龍〉仍然聲稱是源自西報消息,講述的是一艘外國輪船在非洲南端目擊到海中的巨獸,而畫報斷定這頭巨獸毫無疑問就是龍。通過和傳統中國繪畫中的龍比較,作者發現這幅畫的畫師吳友如運用西洋畫法,將龍在繪畫中的地位,從一種神通廣大的神物降格為現代生物學意義上可被見證的巨獸,以視覺的方法,即西方寫實而非傳統中國的寫意向世人宣告它的存在,說明畫師對龍的理解其實早已逸出傳統框架。
此舉固然是一種維持傳統優越感的「西學中源」心理,無甚稀奇。但無論如何,意欲強調中國人早已懂得龍的存在,遠高明於西人的優越心態,晚清中國人到頭來卻只能借助源自西方的寫實認知模式來說明。
火車和龍的故事,暗合張寧博士在《異國事物的轉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9 年)中得出的結論,可見鐵路現代性也溝通了其他異國事物的經驗:
異國事物很可能在傳入時便屬於變動不居的狀態,傳入後更因環境的關係而不斷微調,其受眾乃基於本身的需求與文化傳統,對所看到、聽到、感受到的外來事物重新加以定義和演繹。
本書的經驗寫作很容易令人想起傅柯關於監獄、瘋癲和性的研究。不過後者旨在本質性地拷問當時的歐洲社會秩序,對人性做最前沿的探討。本書則有意探詢鐵路在現代中國的意義,如果說前面只是體現文化研究的趣味性,〈回顧物的歷史:從吳淞鐵路到洋務運動〉和〈民族國家的想像與測繪:孫中山的「鐵路夢」〉兩章則說明,作者對鐵路文化的思考已經深入到歷史內部。
作為現代中國最重要的任務,從「天下」到「國家」的轉型很大程度上靠具體對鐵路的認識、想像和實踐才能落實,表明鐵路在現代中國政治中的位置超過了一般的「異國事物」──孫中山的鐵路夢早知是不切實際,卻無法不夢,必須要夢,且無法離開「鐵路」這個中心,即為明證。
然而民族-國家的構建是一個長時段,且十分繁複、曲折的過程。若用鐵路現代性來回應這麼宏大的問題,單靠這兩章的爆發遠遠不夠,書中未提的北伐、抗戰時期的鐵路現代性也是頗值得深入的議題;同時這本書也讓我想起《大日本帝國時期的海外鐵道》(台灣商務印書館,2020 年)──鐵路在日本起步很早(1872),由此衍生出來的鐵道文化至今仍是一絕,它對現代中國有什麼影響,能否從鐵路現代性的角度重思近現代中日關係史,不禁令人遐想。
最後,若要說本書整體給人最突出的一個印象,我覺得是「深入淺出」──一般說來,文化研究好整高頭講章,同本書這種學問和文筆皆屬上乘的佳作殊不易得,遑論它還只是博士論文。在導論部分,作者梳理了迄今為止中西方近二十家現代性學說,提出「鐵路現代性」的範式,立意擺得很高;但作者也沒有放過任何一個琢磨如何平衡理論和經驗的機會,用講故事的方式來展開章節內容,而且還能敘述得妙趣橫生,理論從甘蔗桿化成了甘蔗汁,令人回味無窮。
(本文作者為第46屆青年文學獎文評組亞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