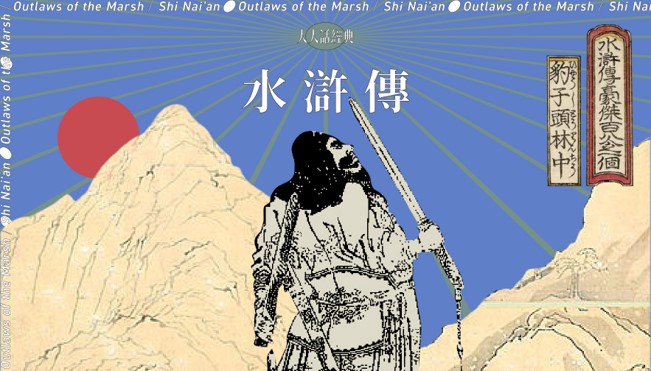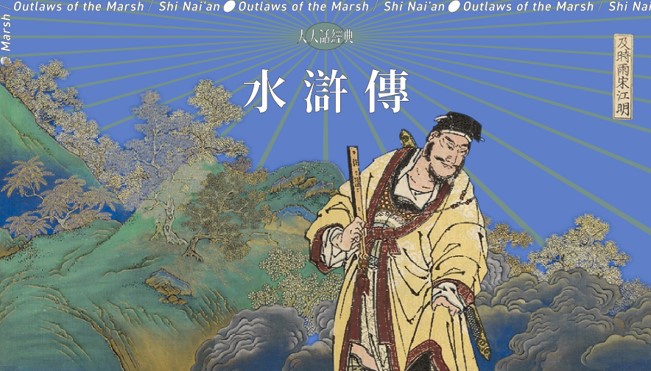孫二娘綽號母夜叉,是《水滸傳》一百單八將中僅有的三位女性角色之一,原先與丈夫菜園子張青在孟州十字坡經營酒店。夜叉是印度傳說中的神祇,原指「以鬼為食之神」,足見其兇惡。女性夜叉亦出自印度傳說,後被佛教吸收,在佛經中往往以美豔之形象出現,有時扮演考驗修道者的角色。
因著這些屬性,「夜叉」一詞在使用上如涉及女性角色,便產生了形象上的分歧。「母夜叉」作為一個綽號,可以指其形象美貌,也可以指手段兇殘,抑或二者兼具。
不過,小說中並沒有對孫二娘容貌是否美豔做直接的描寫,又或者說,對比於其他在容貌上著名的女性(如潘金蓮、閻婆媳、李師師、一丈青等等),孫二娘在角色的外型上,有著截然不同的設定。這與孫二娘獨特的身世有關:
初登場時,孫二娘與丈夫二人專在酒裡下蒙汗藥,迷倒旅人,奪其財物,再將其殺害,做成人肉包子販賣。當然,十字坡酒店戲裡戲外都惡名昭彰,許多人直接以之為黑店代稱,上門之客基本上有去無回。(至於為何這麼有名的店,還有那麼多人會著了他們的道,這又是另一個奇處了。)
孫二娘的父親是出了名的綠林大盜,其心狠手辣的性格,倒也算是家學淵源。這賣人肉的黑店,也就算是孫二娘所繼承的家業了(據小說情節看,這門生意在孫二娘夫妻手上似乎還頗有發展,甚至開了分店)。
她的丈夫菜園子張青,是她的父親選中的女婿,性格較為仁厚,與孫二娘形成鮮明對比。《水滸傳》凸顯現實荒謬之處在這裡明顯可見,即便是溫柔敦厚的張青,依舊跟著妻子在賣人肉、開黑店,顯然溫厚的性格與行為的良善未必相關。
更進一步說,《水滸傳》從來不是一部標舉善良風俗的小說,更不用談有什麼教化功能。孫二娘與丈夫的性格差異,並沒有終結十字坡酒店的邪惡生意,但張青加入這「家族企業」之後,也確實帶了一些改變。
張青曾與孫二娘約定出一些原則,有三等人不可下手:第一是雲遊僧道,當初花和尚魯智深到酒店裡喝酒,被麻倒之後便是靠著這條規矩才保住性命;第二是風塵妓女,這些人用身體賺的辛苦錢,謀不得;第三是流放的囚犯,因這些人裡面有許多「好漢」,不可錯殺了。
而這三條規矩,正暗暗勾勒《水滸傳》建構的價值輪廓。在這草莽故事中,傳統的仁義道德並不俱有主導地位,象徵正義與秩序的官府,是個腐敗的萬惡淵藪,故事中充滿著來自結構的暴力與惡意。
很多人從這個角度來看《水滸傳》,便認為梁山好漢們正在對抗著這吃人的體制,遂將之與當代公民運動等作連結。山寨口那面寫有「替天行道」的大旗,人們口裡吶喊著的「官逼民反」口號,似乎都為嘯聚山林的「好漢」們染上幾許浪漫色彩。
然而,《水滸傳》從來都不是一部偉大的英雄史詩,在濃濃的悲劇氣息中,往往更透露出荒謬的色彩。或者,悲劇與鬧劇有時驚人的相似,甚至存在著相同的本質。
水滸世界有自己的規矩,這是私家的正義。梁山泊是私家正義的集合體,每個來到梁山的好漢,來自社會不同階層,都帶著各自的價值觀。但來到這山上之後,脫落了人間的束縛如林沖、呼延灼等,便也能接號令、打城池;若是本來就殺人放火如李逵、魯智深等,便是得其所哉,是梁山第一等快活人。這些人在山上形成了一個不成文的共識──有原則沒細則,只有一句模糊的替天行道,這「道」的模樣是什麼,卻是宋江說了算、大哥說了算。
嚴格來說,《水滸傳》中的「道」缺乏了論述基礎,人們很難具體說明這個「道」的價值根源為何。大抵來說,便是見那人間有什麼不合理的、不公不義的,看了心裡不舒服,就靠暴力來扭轉。
是以,這自始至終是私家的正義,沒有點拳頭和本事,便無法維繫。
回到孟州十字坡酒店,孫二娘跟著大盜父親學得了一身本事,性格上當然也就是個殺人不眨厭的女魔頭。但自從張青加入之後,這人肉包子店也開始鋪展自己的價值觀,行起自己的「道」了。
我特別想點出的是上面殺不得的三等人,其中第二等「妓女」等風塵女子,這一條特別有意思。
從各個角度來說,《水滸傳》都是一部極為陽剛、父權的小說,書中對女性的醜化、貶抑、輕賤所在多有。如果是正面形象的角色,基本上都帶著男性視角的期待,如女將扈三娘,是個貌美如花的女中豪傑,偏偏整部《水滸傳》幾乎只提到她的長相而未給予任何台詞,形同噤聲。扈三娘後來嫁了矮腳虎王英,自然也不是出於本願,但嫁人之後又死心踏地跟著夫婿,成了模範妻子,這一切描述全然符合父權期待。所以,如果要在性別意識上給《水滸傳》打點分數,大概是死當再死當了。
不過,正是在這性別意識特別薄弱的小說中,張青等人對於風塵女子的同情,倒成了特別有意思的觀察重點。小說原文說道:「第二是江湖上行院妓女之人,他們是沖州撞府,逢場作戲,陪了多少小心得來的錢物。」
十字坡酒店對妓女的同情,並不基於任何性別、人權或女權之立場,純粹是一種素樸的、有著明確因果關係的正義感。因為這群人符合了某些條件,是顯而易見的「弱勢者」,身上帶的都是辛苦錢,是以不得殺。至於更為底層的窮苦人口,則連上酒店的可能都沒有,就不在此列了。
對於妓女與罪犯的不殺條款,恰恰展現了水滸價值中的兩個層面。其一是對於弱者的同情,且弱者的認定是主觀的,並沒有從從結構上徹底反省產生的論述作為基礎;其二是對於好漢(某種程度上,可以是相對於弱者的強者)的人格審美,這是一份浪漫的英雄惜英雄之情,因著對方是條重情重義、有血有淚的漢子,是以打從心裡認可。只要得到「好漢許可」的人,無論是身懷絕技,抑或重情仗義,都夠資格上山結拜,坐一頭領席位。
而此處所說的,對於弱者主觀的認定,正顯示出水滸世界裡「正義」面對結構問題時的簡陋與無力。就女性角色而言,《水滸傳》對於妓女這一類風塵女子採取的,基本上都是一種同情乃至肯定的態度。除了十字坡酒店的店規,書中後半部串起宋江與皇帝「趙官家」的重要人物,汴京名妓李師師,更是此一人物之典型。
無論是賣藝的藝妓,抑或賣身的色妓,在《水滸傳》中的地位,也反襯出另一類女性角色的醜化與貶抑。
這類女性角色在書中被描寫為「淫婦」、「蕩婦」,下場都是被梁山好漢「大快人心」的殺害,諸如著名的潘金蓮,以及宋江所殺的閻婆媳,都是這類人物的典型代表。然而,在水滸世界提供的視角裡,我們很難感受到這些女性實際上一直活在結構的縫隙中,苦苦掙扎著。
於是,在《水滸傳》的價值體系中,孫二娘可說是一等一的女性角色了。她不是嬌弱柔媚的女人,自然不會是敗壞倫理道德的淫婦,但她亦不能是知書達禮的良家婦女,否則上不了梁山。是以,孫二娘以近乎風塵女子的型態登場(《水滸》原文寫孫二娘出場:「下面繫一條鮮紅生絹裙,搽一臉胭脂鉛粉,敞開胸脯,露出桃紅紗主腰,上面一色金紐。),幹的是殺人劫財的勾檔,但又同時在丈夫面前扮演一個順從的角色,即便家業繼承自父親,最後仍依了張青所要求的新規矩。
而除了故事前期與武松有過幾番談話,孫二娘同大部分角色一般,在小說後半部幾乎是噤聲的。當然,這也顯示出孫二娘與丈夫張青,充其量只是一個功能性的角色,在後期的劇情發展中可有可無。(張青後來折在亂軍之中,草草一筆帶過。孫二娘痛哭一場後,不久後也被飛刀殺死)孫二娘真正的表現,大抵在夫妻二人與武松的一段緣份後就結束了。
不過,某種程度上來說,孫二娘與武松之間的情誼,依然是依附在張青與武松的兄弟情之下。與武松談輩分、論交情,稱兄道弟的是菜園子張青,而不是母夜叉孫二娘;說話的是丈夫,妻子只是理所當然的被算在這份交情之內。
孫二娘真正的性格,僅凸顯於她與丈夫間的對話中。她可以笑罵張青的老實,可以為武松作未來打算。她重情重義,只可惜在《水滸傳》的格局中沒辦法有太突出的表現。更重要的,孫二娘在水滸中的正面形象,仍舊不脫父權價值框架的審視,即便再精明幹練,依舊走不出這層限制。但也許也正是因為這樣一位特殊的角色,方能讓我們找到一個特別有意思的切入點,看見細節處透露的結構問題。
《水滸傳》不完美、亦不進步,他透顯的是舊社會裡的諸多框架與束縛,有顯有隱,顯者如官逼民反、英雄末路,這是作者有意的經營;隱者則如女性的噤聲、道德的束縛,這則可能是連作者都未曾跨越的限制。我無意藉由任何進步價值,審視舊時代之經典,甚至以之判定其文學成就。但身在新時代的我們,總必須透過一個又一個更新的視野,去檢視舊時代的的傷口,以思去路。
同場加映:學霸陪你讀《水滸傳》
北宋末年,民亂四起,官場的腐敗導致了社會動盪,恐懼、不甘、憤懣烙印在每個人的瞳孔中,這個無序的世界,只能靠自己拯救。
本月「人人話經典」的專文,將帶著大家進到《水滸傳》的世界,感受林沖退無可退、逼上梁山的心路歷程、體會宋江在亂世中用控制人心的權謀之術、品嘗孫二娘賣人肉包子背後反映的女性哀愁。
施耐庵寫下《水滸傳》,眾生百態栩栩呈現,每個人的故事各有能細細品味之處,不同的角色際遇,也鏡射出不同的觀點,水滸一百零八條好漢,你又最想讀誰的故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