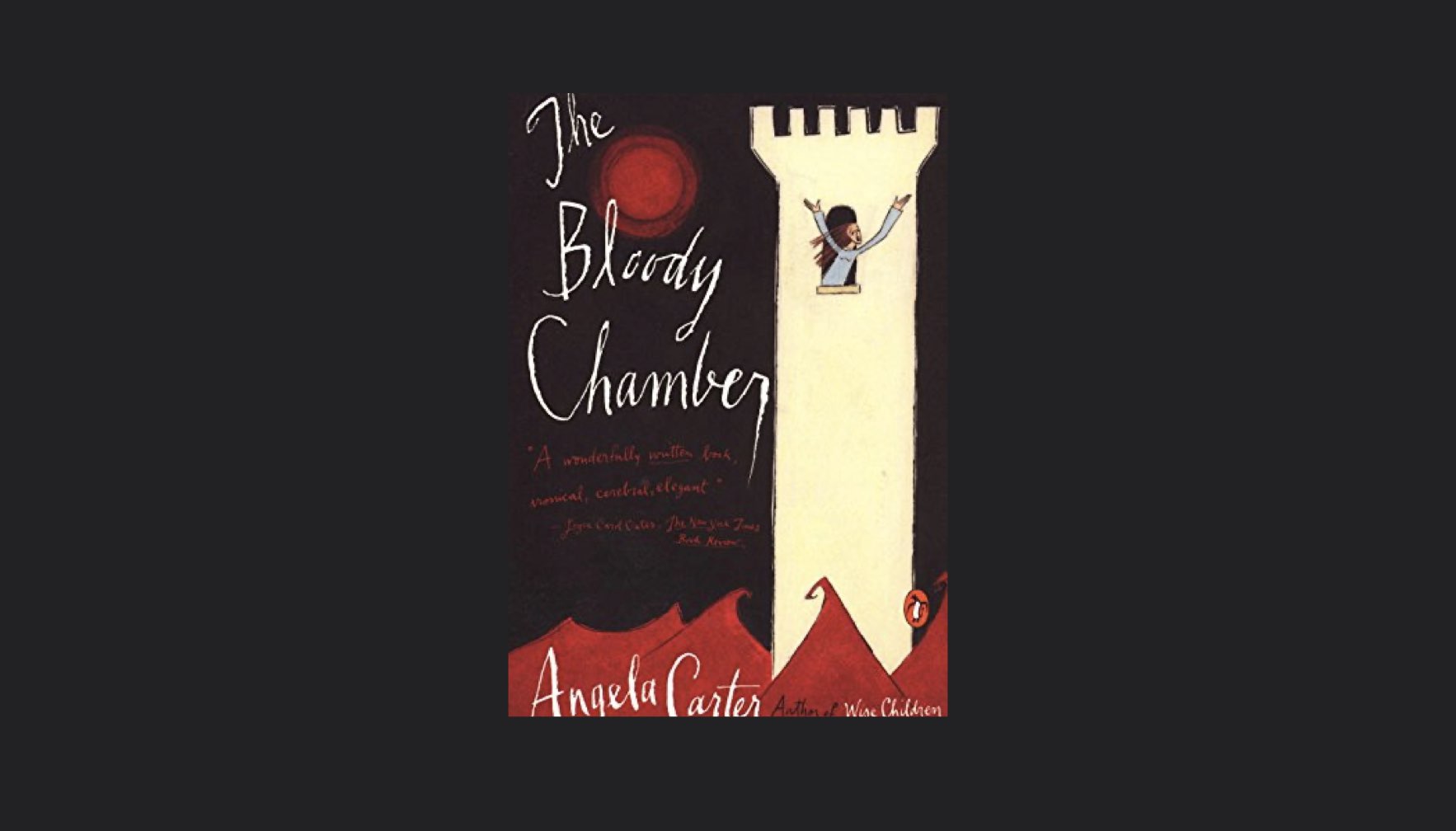安潔拉・卡特(Angela Carter)1979 年的短篇小說集《染血之室》(The Bloody Chamber)無疑是眾多改編童話[1]中的首開先河者:從〈小紅帽〉、〈美女與野獸〉到〈穿長靴的貓〉和〈白雪公主〉,卡特刻意凸顯童話中潛藏的性別政治,對經典童話的重詮引起不少論辯。
「戀愛與酷刑驚人地相似──這是我在自己婚床上學到的啟示。」(頁 28)〈染血之室〉的敘事者引用詩人波特萊爾如此道出婚姻的真諦,這篇作品改寫自佩羅(Charles Perrault)1697 年的知名童話故事〈藍鬍子〉[2]。〈染血之室〉收錄於同名故事集,是一則非典型哥德羅曼史(gothic romance)[3]:女主角嫁給遙遠古堡中的男侯爵,卻在好奇心驅使下拿著侯爵交付的鑰匙,偷偷開啟了通往禁忌之室的大門,最終發現宛如預示自己噩運般的駭人秘密。
在女主角出現前,故事中出現的每場婚姻關係都以妻子之死作結。耐人尋味的是,卡特重述版本裡的夫妻關係卻添加了毫不遮掩的露骨情色場景、以及童話故事中少見女主角探索情慾的心理轉折,最終拯救女主角的不是兄弟也並非情人,而是女主角的母親。如果佩羅的原著是一則告誡女人不該好奇心過盛、揭露丈夫秘密的警世寓言,卡特的改編就是滿載情慾張力、從女性角度口述的黑色成人童話。

童話與色情:想像一種道德的書寫位置
童話與色情乍看之下互不相容,事實上卻是從 1970 年代就引起不同女性主義流派激辯的主題,〈染血之室〉便是在第二波女性主義反色情[4]聲浪高漲的氛圍下完成的作品。
基進女性主義代表德沃金(Andrea Dworkin)在其著作《厭女》(Woman Hating)中批判童話故事中兩性權力關係傾斜的問題,並指出色情在傳統童話故事裡時常成為服務父權體制、鞏固性暴力的要素。這個觀點在《色情》(Pornography)中開展出新的論題:即施受虐(sadomasochism)的浪漫化延續了父權結構中男性對女性的主宰和掌控,並點名薩德侯爵(Marquis de Sade)為提倡此種關係的開山鼻祖。
色情對女人而言是否業已(always already)被掏空了所有正面積極的意義?卡特在 1978 年的論著《薩德式女人》(The Sadeian Woman)中對薩德侯爵兩部作品《茱絲汀》(Justine)與《茱麗葉》(Juliette)的評析便可視為對這個問題的回應與省思。
薩德筆下的茱絲汀篤信美德與貞潔能替她換取父權社會的尊重,而她的純真也為她帶來優越感。但茱絲汀的優越奠基於由裡到外的壓抑:壓抑情慾、憤怒、與慾望內在固有之暴力。對卡特而言,茱絲汀體現了一種「只關乎自身的女性受虐(self-regarding female masochism),這樣的女人在世上沒有立足之地亦無權勢,她的抵抗行動早已被自我憐憫腐蝕殆盡」[5]。
更有甚者,她的美德建立在順服與屈從上、否定了女性侵略的潛力與所有自身慾望可能導致的暴力,她的貞潔源於對性愉悅的拒斥,而這種被動位置導致任何形式的性行為都構成一種無力抵抗的暴行[6]。茱絲汀的貞潔遂可理解成一種被虐狂式、悲劇性的最後掌控。但對美德與守貞的掌控非但沒替她帶來幸福,卻恰恰成為悲慘厄運的原因── 茱絲汀的美德讓她享受神格化的瞬間,但正是基於這種神聖,才構成了被褻瀆的前提。
對卡特而言,薩德筆下女性缺乏一席之地的形象本身就是一種必須被破除的神話。這種神話又時常糅合母職的神聖化、試圖將女人抽離世俗生活與物質基礎[7]。與茱絲汀帶有殉道色彩的苦難形成對比的是放浪形骸的茱麗葉:茱麗葉極盡所能地掠奪侵占他物,且一手策畫眾多淫靡悖德的謀害,除了運用理性和美貌帶來的權力獲取財富外,她更熱衷毫無目的性或意義的性愛。茱麗葉象徵毀滅性的女性憤怒與情慾,而這樣的毀滅性具有拆解父權秩序的潛力。
薩德極可能不自詡為女人的盟友,但其書寫中對中產階級意識的抵抗──反對浪漫愛、毀棄婚內單偶制度、擁抱非生殖性行為的位置──卻使他意外地開啟更多關於性別與女人的想像。就此層面而言,薩德的創作提供了女性一個超越婚家與母職的叛逃路徑。
藉由重新閱讀薩德,卡特幾近挑釁地將道德與色情並置,試圖在兩者的對立之間尋找一種「道德色情」(moral pornography),亦即服務女性的色情。這種解讀當然讓卡特招致不少非議,其中又以指稱其再製女性受虐情結的壞信念(bad faith)為首、大力抨擊其中可能將針對女性的暴力浪漫化的意涵。但卡特深知色情潛藏的陷阱、亦承認薩德作品中厭女的角色呈現,只是她更強調破除「神話式的抽象描繪(mythic abstractions)」[8]:色情並非構築於真空,任何道德的色情作品都應具體描繪真實世界裡各種性別個體間的互動關係,而非建立一個抽離現實的幻想空間。
易言之,一名道德的色情創作者應利用色情素材來批判現實生活裡的性別窠臼;創作者的使命是肉體的去神秘化(demystification)。據此,卡特對於色情的基本立場既非閃躲亦不認為色情應被控管禁絕,而是主張女人應積極介入色情的生產、策略性運用色情奪回自身的話語權,建立為女人存在的色情傳統。
童話傳統中無論性愛場景的描繪或女性情慾都時常被抽象化或隱晦呈現,卡特的改編故事則刻意凸顯了社會現實的物質層面與女性身體,試圖還給歷史上面貌模糊的女人一個具象化的肉身。從這角度來看,〈染血之室〉毋寧是卡特作為一名「道德色情創作者」的政治實踐。
重探〈藍鬍子〉:染血鑰匙開啟的情慾政治
乍看之下,卡特解放式的訴求似乎輕易就能歸類到 1980 年代女性主義流派中強調反叛的性積極(sex-positive,或稱擁性/性激進)「惡女」陣營,但細究其童話會發現不少抗拒二元化標籤的曖昧空間。事實上,部分論者[9]甚至認為〈染血之室〉是整本故事集中最保守的一則寓言。在這個故事中,男性情慾固然是死亡導向的,無論侯爵的凝視、陽具或匕首都與針對女性的侵略和暴力直接連結,而這樣的暴力最終也並未替女主角開啟一條逃逸路線,潘朵拉仍然因為自己的求知欲被懲罰了[10]。這種詮釋下,陽性權力的彰顯和暴力的情欲化(the eroticization of violence)都和德沃金定義的色情本質相去不遠。
但〈藍鬍子〉真的只能從女性屈從和性別暴力的角度詮釋嗎?許多民俗學學者回溯童話故事的詮釋傳統,發現〈藍鬍子〉的口述版本在佩羅的創作問世前已存在許久。其中一個版本提到年輕慧黠的女主角成功瞞騙其丈夫安全逃脫、並將其受害的姊妹們一併救出侯爵的魔掌;其餘版本也不乏女性勝利的結局[11]。直到 1976 年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學派與兒童心理學家貝特罕(Bruno Bettelheim)在其著作《童話的魅力》(The Uses of Enchantment)中首度將佩羅版本的〈藍鬍子〉詮釋成道德寓言時,這些原先不帶訓誡意味的故事突然被賦予了至今為止仍屹立不搖的啟示:即女性求知慾的潛在危險。
對貝特罕而言,侯爵的鑰匙是對女性是否值得信賴的試驗,故事中的女主角因撒謊而陷入危險,倘若她肯認並懺悔自身的過錯,最終將可獲得救贖。然而〈藍鬍子〉裡的求知不僅與女性對真相的探尋/知識相連,女主角的踰越之舉也象徵了女性在情慾方面的好奇心。原著中藍鬍子為了測試妻子留下一串鑰匙,並明確叮囑女主角整個城堡裡唯有一間房間不可開啟。在侯爵離開、女主角開啟禁忌之門後,手上的鑰匙便沾染上無法抹滅的鮮紅血跡。倘若讀者將開啟禁忌之門理解為男性性器的侵入、而初次性交後女方處女膜破裂被鮮血染紅的隱喻,鑰匙上無法拭除的血漬便不難理解了── 畢竟喪失處女之身是不可逆的結果。
〈染血之室〉刻意突顯了這個橋段與女性情慾的連結:藍鬍子抵達宅邸後便質問妻子是否違背叮囑打開了秘密的房間,侯爵命令妻子跪下,並以染血的鑰匙在其額頭上烙印「心型血漬」(頁 38)。這裡的紅色印記讓人聯想到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著名作品《紅字》(The Scarlett Letter)因通姦罪而在胸前被烙上紅字的女主角海斯特(Hester Prynne),而腥紅色自此也成為姦淫與不忠貞的代名詞。不過正如後續各種翻案改編為紅字帶來的嶄新意義,讀者亦無法素樸地將〈染血之室〉裡的女主角視為被動承載父權意志的受害者。
獻給妳的童話:自戀凝視與母女情誼
〈染血之室〉與原版最顯著的差異便在敘事觀點從第三人稱視角轉為由第一人稱女性角色敘事。不過女性敘事者並不必然構成文本挑戰色情傳統的前提,正如卡特對茱麗葉的評語,〈染血之室〉的女主角極有可能只是「說書的婊子」(the whore as story-teller),仰仗天花亂墜的故事來娛樂她的囚禁者,才能逃過死劫[12]。然而從敘事方式來看,〈染血之室〉顯然不是為了取悅男人而存在的故事。

事實上,〈染血之室〉多處對原著的解構皆可看出對女性主體性的積極肯認。首先,佩羅原著中只提到丈夫面貌奇醜並坐擁財富,但卡特的版本中丈夫多了「侯爵」(Marquis)的頭銜,深諳藝術鑑賞並熱愛蒐集色情刊物。這裡的侯爵略帶戲謔地指涉薩德侯爵,另一方面又暗喻藝術與色情間模糊的分界。藍鬍子的貴族身份與年長男性所具備的經驗建構了他的權力來源,而這點也從女主角的年幼純真襯托出來(哥德羅曼史小說中常見的設定便是男女雙方顯著的年齡與經濟地位差距)。侯爵對女主角的窺淫式凝視[13](voyeuristic gaze)固然可視為一種男人對女人的暴力穿刺,但女主角半抗拒半好奇的的心理狀態與情慾探索的過程卻也點破了這種凝視的雙向性。
最具代表性的便為故事中女主角在侯爵特意準備的鏡面房看見鏡中自己充滿慾望的形象:「看見他用充滿色慾的眼神望著我時,我低垂雙眼,卻在轉移視線至遠方的同時無意間瞥見了鏡中的自己。霎那間我突然透過他的視角看見我蒼白的臉龐.......在我無知侷限的人生裡,第一次感到自己有墮落淫靡的潛能。(頁 6)」
有別於原著中第三人稱觀點的敘事方式,這個版本中的敘事主體是女主角,讀者也十分罕見地看到女主角對自身慾望的表述:「他身穿倫敦訂製的西服;她則如羔羊般赤裸──這是所有遭逢中最色情的一種。在歌劇院乍見我映於他眼簾的肉體時,體內的情慾騷動讓我驚駭無比。......我顫動著,像比賽在即的賽馬、卻揉雜了恐懼,因為做愛這念頭帶給我一種奇異又事不關己的亢奮(impersonal arousal),同時他雪白沉重的身軀卻讓我無法抑止地嫌惡。(頁 12)」這個場景提醒讀者女性身體往往被描繪成一種展示性奇觀(exhibitionist spectacle):男人注視女人,女人則注視著被注視的自己,而女人也因意識到自己成為造就這個奇觀的共犯而無時無刻感到罪咎。但這樣的自戀凝視真的只有「父權共謀」的意義嗎?
若將鏡面房的場景跟《薩德式女人》並置閱讀,則不難看出女主角和茱絲汀的相異之處:茱斯汀未曾把美貌視為自己內在固有的優勢,而是外於自身的特質。而茱絲汀對陰性特質的拒斥也使她的純真無知有了正當性。(頁 41)
然而,〈染血之室〉女主角並不是茱絲汀。她體內的騷動混合了期待與自我意識,對自己身體的自戀凝視也讓她主動參與了侯爵的遊戲,更有甚者還扭轉了遊戲規則:陰性特質自此不再等同被動/被宰制,遊戲的意義亦不在於迎合或抵抗男性凝視,而是自我觀看。藉由自戀凝視,女主角意識到女性身份陰柔與被動特質對男性的誘惑與魅力,而正是這層直面黑暗後象徵「性覺醒」的自我意識,將卡特筆下的女主角與原著中妻子或茱絲汀蒙昧無知的心理狀態區隔,開啟女性身為情慾主體的可能。
女主角的恐懼和厭惡則暗示兩相悖反的事物有其建構性與互相依存的本質,或許卡特的童話從來就沒打算消解父權體制與女人主體性之間的矛盾,而是看見矛盾的縫隙與其間流瀉的光影。因此,〈染血之室〉的妻子不是茱絲汀、也並非茱麗葉;她的曖昧位置勾勒出貞女與浪女、受害者與共犯、「家中天使」與「閣樓上的瘋女」兩造外無法窮盡的可能。

除了敘事觀點轉移外,卡特的版本更試圖挑戰男性佔據主動侵略者位置的傳統,以女性對男性身體的「回望」(return of the gaze)再度鬆動童話故事的敘事結構。這點可從鋼琴調音師尚伊夫(Jean-Yves)說起:對應到傳統童話的配置,此角既是從暴虐丈夫手中英雄救美的「王子」,也是女主角在苦悶婚姻外需索浪漫的「情人」。然而尚伊夫的失明一方面暗示他被剝奪了像侯爵那樣凝視女體並享受其視覺快感的權力,另一方面也象徵了被閹割的殘缺男性身分。兩者皆標示了慾望的缺席。
因為失明,尚伊夫沒有機會窺視侯爵圖書館裡禁忌的蒐藏、也不會看見女主角額頭上恥辱的印記。基於同樣的理由,讀者對尚伊夫的第一印象不是帶來激情火花的第三者、不是奮勇救美的王子,更不會是對女人的威脅。那無法施展男性凝視的尚伊夫究竟在故事中佔據什麼樣的位置呢?
這個問題的答案或可從他與藍鬍子角色上的對照談起。女主角初遇尚伊夫時,對方羞怯地表示對女主角琴藝的仰慕,並詢問是否能允許他偶爾在一旁聆聽女主角練習時優美的樂聲。在這個場景中,女性顯然主導了互動的掌控權,而尚伊夫在故事中一再被強調的敏銳聽覺也與侯爵的視覺構成鮮明的對比。侯爵離開後,女主角一度感到難耐的衝動,希望能有機會私下跟調音師聊天,可見對於女主角而言,尚伊夫是整個城堡中唯一值得信賴的傾訴對象(listener)。
如果侯爵的視覺侵略代表感官享樂,尚伊夫的傾聽則凸顯了某種幾近柏拉圖、對精神交流的渴求。然而,若據此將故事本身解釋成褒陽貶陰的心物二元論,或有過度簡化之嫌。即便扮演光明磊落的保護者角色,尚伊夫也只「提供了某種程度上的撫慰」,對女主角的困境「沒什麼實質作用(“I can be of some comfort to you . . . Though not much use.” )」(頁 40)。這句戲謔式的註腳若與故事真正的英雄相互參照,則可見卡特對於傳統童話結局鞏固異性戀浪漫愛的薄弱基礎之批判。
最終解救女主角倖免於難的是母親:這名「騎士」身著「紮進腰際的黑色短裙」,以便在「身穿喪服」的狀態下,「狂暴雄偉」地駕馭奔馳中的駿馬(頁 41)。她在運用其「母親特有的心電感應(maternal telepathy)(頁 44)」能力後,察覺女主角深陷危險,便取代缺席的白馬王子而英勇登場。在手握父親佩槍的女騎士面前,藍鬍子只能瞠目結舌地望著眼前的「梅杜莎」,迎接即將到來的命運。
其實從一開始,讀者便知道女主角的母親並非等閒之輩:年輕時在中南半島冒險、「如鷹般不屈不撓」的母親「面對一群中國海盜時睥睨全場、在瘟疫來襲時獨力照護全村村民、甚至親手槍殺一頭食人猛虎」(頁2)。在這裡,我們看到童話中少有(而薩德作品裡可謂不存在)的母親形象:堅毅、勇敢、並一肩扛起撫育的責任。這裡當然多少複製了某種對神聖母職的預期,但也因為卡特筆下男主角們可有可無與結局白馬王子與母親形象重疊而多了一層女女情誼的酷兒意味。
至於心電感應這個乍看宛如天外救星(Deus ex machina)的情節設計,或可理解為卡特式的惡趣味──以母親近乎敢曝(camp)[14]的華麗登場,凸顯/嘲諷/顛覆了異性戀本位的童話傳統中女女情誼和被父權社會禁錮的女性彼此支援之不可能,而傳統上帶來救贖的男性角色也徹底被排除在這種敘事結構之外。
最終女主角繼承了侯爵的遺產,並將這筆龐大的財產捐獻給慈善機構並開設音樂學院。與原著不同的是,卡特筆下的侯爵夫人開宗明義便承認自己為了繼續在音樂領域深耕才委曲求全嫁給富裕的藍鬍子。「妳確定妳愛他嗎?」面對母親這個問題,女主角的回答是:「我確定我要嫁給他。」此時她心心念念的只有如何「驅逐長年盤旋在寒酸餐桌前的貧窮幽靈」(頁2),而這個棄絕愛情以換取穩定物質基礎的決定也伴隨著主動參與侯爵情慾遊戲的羞恥感,如影隨形地縈繞在她的婚姻裡。
多數童話中輕描淡寫帶過甚至取消的物質性與女性負面情感,到了卡特筆下可謂無法不直視。從這角度來看,我們不妨把〈染血之室〉理解成對童話的修復與女性話語權的重奪。卡特選擇不輕放女性沉重的枷鎖,在魔幻寫實的改寫中積極肯認女性的能動性,卻不隱蔽支撐能動性的基石底下始終存在犧牲與殘酷之重。
- Bettelheim, Bruno. The Uses of Enchantment: The Meaning and Importance of Fairy Tales. NY: Vintage, 2010.
- Carter, Angela.The Bloody Chamber. US: Penguin, 2011.
- ——. The Sadeian Woman: An Exercise in Cultural History. UK: Hachette, 2015. Google books. Web. 16 Jan. 2018.
- Donne, Mary Ann. “The Woman’s Film: Possession and Address.” Re-Vision: Essays in Feminist Film Criticism. Eds. Mary Ann Doane, Patricia Mellencamp, and Linda Williams. US: American Film Institute, 1984.
- Dworkin, Andrea. Pornography: Men Possessing Women. US: Penguin, 1989.
- ——. Woman Hating: A Radical Look at Sexuality. US: Plume, 1974.
- Modleski, Tania.Loving with A Vengeance: Mass-Produced Fantasies for Women.US: Routledge, 2008.
- Mulvey, Laura. “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 Screen16.3 (1975): 6-18.
- Lang, Andrew. “Blue Beard.” The Blue Fairy Book. Ed D.L. Ashliman.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mpany, 1889. 290-95.
- Sage, Lorna. Introduction. Flesh and the Mirror: Essays on the Art of Angela Carter. Ed. Lorna Sage. London: Virago, 1994.
- Sheets, Robin Ann. “Pornography, Fairy Tales, and Feminism: Angela Carter’s ‘The Bloody Chamber’.”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1.4 (1991): 633-57.
- Sontag, Susan. “Notes on ‘Camp’.”Against Interpretation: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Penguin, 2009. 275-92.
- Steinem, Gloria. “Erotica and Pornography: A Clear and Present Difference.” Take Back the Night: Women on Pornography. Ed. Laura Lederer. NY: 1980. 35-39.
- Williams, Linda. “When the Woman Looks.” Re-Vision: Essays in Feminist Film Criticism. Ed. Mary Ann Doane, Patricia Mellencamp, and Linda Williams. US: American Film Institute, 1984.
作者介紹: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碩士,研究興趣為酷兒理論、情感研究、
[1]同樣對童話提出女性主義修正式(revisionist)閱讀的還有賽斯頓(Anne Sexton)重述格林兄弟的詩歌集《蛻變》(Transformations)和愛特伍(Margaret Atwood)〈藍鬍子的蛋〉(Bluebeard’s Egg)。
[2]此處的佩羅版本出自蘭格(Andrew Lang)編譯彙整之世界經典民間童話故事集《藍色童話(The Blue Fairy Book)(1889)》。
[3]哥德羅曼史時興於十八世紀英國,背景設定常為有異國情調的莊園古堡和中世紀廢墟,涉及超自然與恐怖元素,題材為未經世事的年輕女主角(家庭教師或新婚妻子)與身懷黑暗秘密的男主人間的戀曲;代表作品有《奧托蘭多城堡》(The Castle of Otranto)、《舞多佛的秘密》(The Mysteries of Udolpho)、《簡愛》(Jane Eyre)等。〈染血之室〉便可見多處對古典哥德羅曼史的仿擬:例如女性被家庭囚禁的恐懼、女主角對於婚姻/丈夫的不信任和害怕步上母親(藍鬍子的前任妻子們可視為母親角色的變體)後塵的被害妄想(paranoia)、陽性主導男角(Super-Male)與陰性陪襯男角(Shadow-Male)對照組(71)等,詳見莫德列斯基(Tania Modleski)。
[4]部分性別研究者主張用語上應嚴格區分色情(pornography)與情色(erotica):前者被定義為女性的壓迫與物化;後者則指雙方互相取悅、並給予女人足夠權力積極選擇下的情慾表述或性行為。但這樣的區分本身便預設了不同女性觀影者在觀賞色情影像時皆佔據一種調和(coherent)且穩定不變的位置,不僅隱蔽了情色內在固有的侵略性,也一併取消了色情中認同與慾望同時並存的可能。關於色情與情色的定義詳見史坦能(Gloria Steinem)的著作。
[5]《薩德式女人》,頁34。
[6]同註五,頁30。
[7]Lorna Sage. Introduction. Flesh and the Mirror: Essays on the Art of Angela Carter. London: Virago, 1994,頁13。
[8]同註五,頁8。
[9]例如英國批評家鄧克(Patricia Dunker)就認為卡特對女性情慾的描繪依然局限於等待男性啟蒙/喚醒的被動姿態,在被動享樂的前提下女人無法掌握情慾自主權;(Sheets 1)另一方面,德沃金也主張女性的自由始於對受虐情節的拒斥,這兩種立場都再度強化了受虐者與喪失能動性的連結。值得注意的是,受虐標示的是一種痛苦與愉悅並存(pleasure-in-pain)的矛盾狀態,在這種狀態裡受虐者無論生理性別為何都佔據了「陰性位置」。然而施受虐實踐中強調的戲耍、扮裝與表演性質,在在顯示這種情慾互動中的主導權是由雙方往返協商,權力亦在過程中不斷流轉,受虐方並非單方面承載施虐方慾望的容器。
[10]不妨把此處的求知理解為窺探/凝視的轉喻(metonymy):著名電影理論學者多恩(Mary Ann Donne)點出女性凝視在電影敘事中永遠伴隨著女性的遭罪(victimization)(72),亦即女性在探索知識真理時因為施展並僭越了陽性權力而受到懲罰。延續上述觀點,威廉斯(Linda Williams)則認為這正好解釋了女人的好奇心/慾望時常伴隨著被虐幻想的原因。(85)
[11]Robin Ann Sheets,. “Pornography, Fairy Tales, and Feminism: Angela Carter’s ‘The Bloody Chamber’.”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1.4,1991,頁643。
[12]同註五,頁81。
[13]莫薇(Laura Mulvey)主張男性凝視的權力行使可劃分為兩種:其一為虐待狂式窺淫,此類場景透過彰顯男性能動性來懲罰女性;第二種則為戀物式理想化(over-valuation),藉由刻劃過度完美的女性身體來控管其威脅性。易言之,女性在這種結構下只被給予兩種選擇:認同受虐位置或成為自身的慾望客體並背負其所招致的自戀罪名,詳見〈視覺快感與電影敘事〉(“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
[14]Camp有多種譯法(敢曝、露淫、妖等),定義也無法一言以蔽之,直觀意義為不自然、矯飾、浮誇美學,若參考桑塔格(Susan Sontag)在〈敢曝筆記〉(Notes on Camp)中的分類,此處母親登場之所以敢曝,在於其性別氣質的倒錯與誇大呈現。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裡的敢曝也指涉了女性特質和母職作為一種扮裝表演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