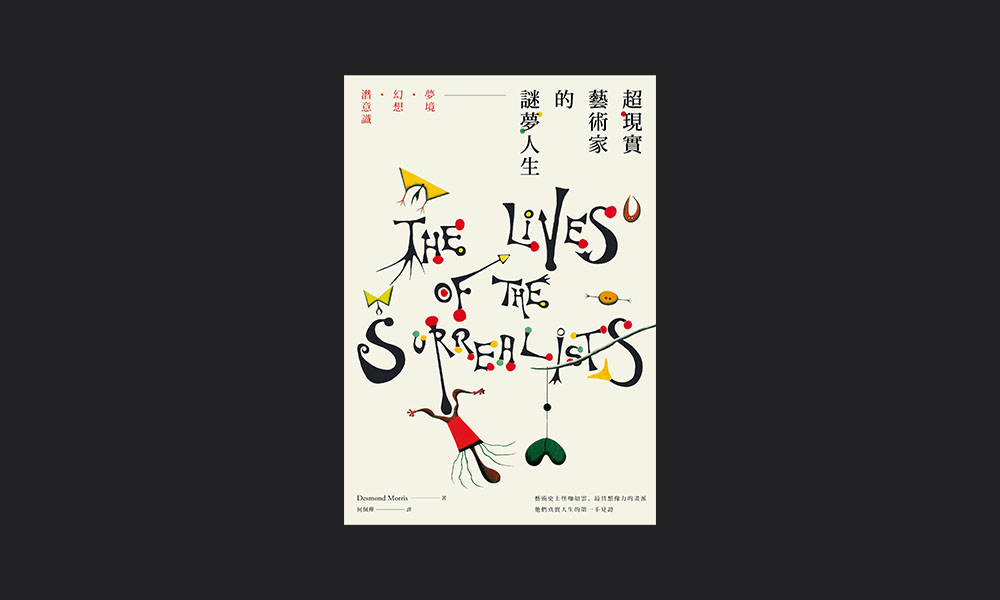記得初見披頭四 1967 年專輯《寂寞芳心俱樂部》(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 時,立即被唱片封面吸引:四人樂隊被一群頭像或胸像簇擁包圍,當時僅能勉強指認一二:馬克思、卓別林、愛倫坡、巴布狄倫、夢露......。私忖,其它我尚不認識的,或許同樣亦是頭角崢嶸的怪人吧,暗暗渴盼來日也許能在哪一本書或哪一部片裡不期而遇。
近二十年後,類似情境居然再度發生:黃亞歷《日曜日式散步者》(2016)裡的風車詩社,熱帶島嶼上的超現實主義詩人,於大銀幕上列隊現身,或同人合照、或文友寫真。雖然早在九〇年代出土但迄今依然鮮為人知的一段臺灣文學史,隨著這部電影,讓我們赫然驚覺我們對於這些詩人的面孔,竟然如此陌生。
也許讓多數觀眾同感陌生的,還有片中的歐陸超現實主義者。黃亞歷刻意抹銷了藝術家及其作品的「名字」,只讓臉孔、畫作或攝影作品,依隨敘事蜂湧襲來,除了摹擬風車詩人當年面對源自法國繞道日本而來的新思潮,繼而囫圇吞飲之際的應接不暇目眩神迷,也藉此向我們指出了我們認識的侷限──這個我們誤以為爛熟的世界其實還很尖新,一如才剛剖開的切口,要求我們像兒童那樣以手去指、去摸。
超現實主義的 (動物學) 入門
新近 (2018 年 9 月)出版的《超現實藝術家的謎夢人生:他們真實人生的第一手見證》,序言之後的正文扉頁也有一張「群像」圖:恩斯特(Max Ernst)繪製的《朋友聚會》。年輕時乃是超現實主義運動一員日後成為動物學家的作者,德斯蒙德・莫里斯(Desmond Morris),隨之一一點名,恰似在這些三〇年代歐陸超現實主義者的臉上逐個標示姓名,同時啟動敘事與書寫,依序述說他們的行誼軼事,最終以文字繪製了一卷超現實主義的封神榜──甚至,一本點鬼簿。
正是時候,我們擁有了一冊全新的入門書,讓我們重新並且從頭認識超現實主義:此時此地的物質基礎、接受結構,以及精神史環節提供了(必然迥異於舊的) 新的認識契機,而從「頭」(超現實主義運動有頭有臉的大咖們)開始,也是一塊輕脆的敲門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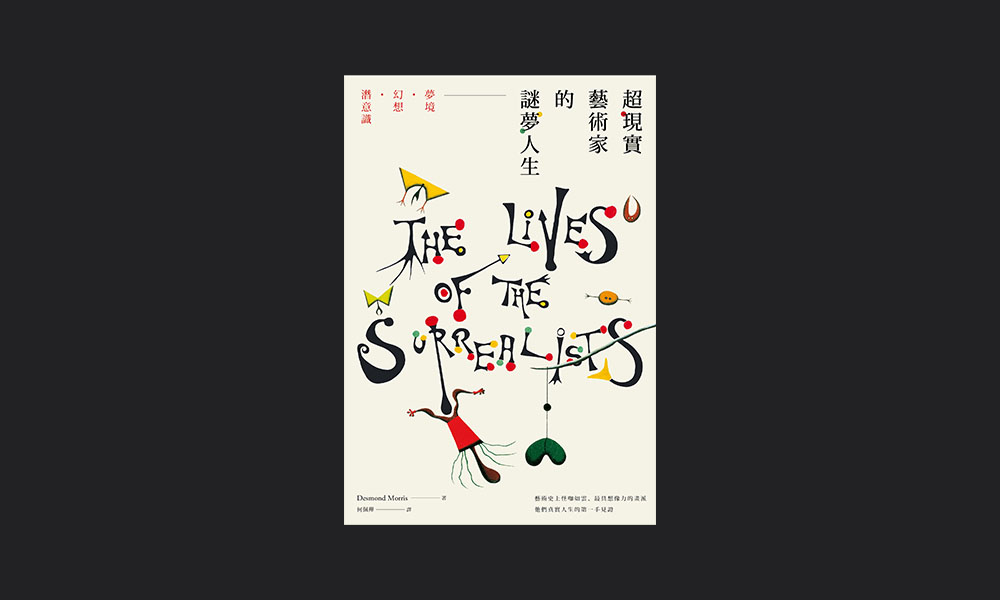
超現實主義「群像」的敘事策略
此書的「群像」敘事,一方面是作者莫里斯目睹親歷之後的「見證」體例(指證歷歷)或「說故事」體裁(娓娓當年),另一方面也是他另闢蹊徑的銳意選擇。與學術論述相比,「肖像」的勾勒也許會讓作品的詮釋落入「心理傳記」的侷限,然而,「群體」的集合與「個體」的交織,不但讓「超現實主義」此一乍看同質的全稱變得繁複分歧,也讓作者(敘事者)主觀的「記憶之獨裁」與「書寫的權力」獲得了相對的客觀性。
作者不時指證某件作品其實「只是」某人幼年創傷或成年性慾的「反映」,但當此人此作納進作者勾勒的群像時,卻又顯得「不只是」如此。
比如,培根(Francis Bacon)畫作裡或劇烈扭曲、或壓縮於囚籠方格裡的肉體,曾經親炙培根的莫里斯揭露,此一主題與風格只是培根個人「性愉虐」場景的「如實再現」而已,並非當代理論過度詮釋為「現代人處境」的「隱喻」──然而,培根不是超現實主義者唯一的 SM 成員,而且,現代人難道不都早已各自總是這種或那種 SM 的存在了嗎?

同樣的,貝爾默 (Hans Bellmer)肢解女體模型、以女體部件組裝而成的一件件詭譎異色的人偶裝置,除了確實反映了個人病態的性嗜好,但也無法斷然否認他與它們不是父權體制的具體呈現(這是當代論述的詮釋)──個人的即是政治的,男人的即是父權政治的。
這種基於作者個人「我在現場」的交遊見聞所揭露的小道消息,最終不但沒有塗銷、反而補充了既有的藝術史詮釋,甚至不乏重寫藝術史的八卦。書中經典一例,即是作者從證據推敲進而揭穿杜象(Marcel Duchamp)以「現成物」小便斗所轉化製作的「作品」《噴泉》(1917),其實晚於、甚至乞靈於杜象的密友洛琳霍芬男爵夫人(Elsa von Freytag-Loringhoven)。但作者在揭露之後也承認,藝術史書寫的論述邏輯,面對主要以藝術論述構作而成的當代藝術時,很難不繼續仍以杜象為第一人。
性,動物,與政治
作者從小見大(而非以小搏大)、見樹繼而見林(同時反之亦成立)的超現實主義「群像敘事」裡,最引人注目與側目的,無疑是超現實主義者們的性愛(與)政治。
從三角戀到三人行,從出軌外遇到交換伴侶,從恩斯特的風流史到畢卡索(Pablo Picasso)的性殺伐旅(sex safaris)......超現實主義男人的惡名昭彰不是新鮮事,但超現實主義者們開放性關係的尺度仍然令人咋舌。
在這男人網絡或父權圈子裡,許多女性藝術家(或groupie)成了超現實主義的受害者,比如卡琳頓(Leonora Carrington)成了「瀕臨崩潰邊緣的女人」,多次進出精神病院。但同時也有相反地持「超現實主義化身」權柄的費妮(Lenrnor Fini),一生情人不斷,掀揚石榴裙,席捲男人、所向披靡。

不過,並非每一超現實主義者都符合 (被打造的或被再現的)「瘋狂藝術家」形象。馬格利特(Rene Magritte)似乎是假扮成一位過著資產階級生活的平凡人、藉以掩蓋他是怪人的事實;米羅(Joan Miro)只在作品裡反叛,在生活裡循規蹈矩;亨利摩爾(Henry Moore)則根本像是一位簡樸礦工那樣地雕刻作品。
臥室裡的超現實主義者各以不同動物原形現身,廣場上的超現實主義者則有陣營敵對、口號對立的人。反布爾喬亞社會的超現實主義者,理應左傾 (根柢上超現實主義哲學基礎之一即是馬克思主義),但亦有極右派──國際上最知名的超現實主義藝術家達利(Salvador Dalí),除了是一位美式浮誇藝人、商業嗅覺靈敏的媚俗富翁之外,他先後擁護甚至崇拜希特勒和佛朗哥;而且,與多數性慾賁張的同人剛好相反,達利是一位性無能的手淫狂。
肖像畫裡個別私密性史的背後,則是群像共同經歷的政治史:二次大戰,法國淪入納粹指爪,超現實主義者們或流亡紐約、或避難南法,或加入地下反抗軍,猶太裔者則必須設法全身而退。西班牙內戰也在超現實主義圈內引起漣漪,林飛龍(Wifredo Lam)加入游擊隊,他一生私淑的畢卡索則創作了《格爾尼卡》(Guernica, 1937)。戰爭也改變了超現實主義的運動軌跡──二戰之後布勒東返回巴黎,但超現實主義圈子已然四散,美國的抽象表現主義則在超現實主義戰間期的點燃之下誕生。
異端的內部矛盾,異質的多重起源
檢視莫里斯對 32 位超現實主義者的點兵次序,似可發現,他刻意從達達派、被逐者、遭黜者、女人等「非正統超現實主義者」(異端裡的異端)說起,最後則以超現實主義的「異質起源」以及「多重起源」收束,這是一個高度矛盾的敘事立場──然而,在這二點異端之間,他也提供了當今超現實主義公認論述的入門。
比如,作者反覆強調了超現實主義的多處「內部矛盾」。以《超現實主義宣言》作為(巴黎)超現實主義運動領袖的布勒東(André Breton),極為父權,乃一獨裁暴君,憎恨女人與同性戀──毫不「進步」遑論「前衛」。他也極度迷戀權力,因而玻璃心易碎,動輒開會(假民主程序)開除不合紀律(或不合己意)的成員。以布勒東為首的(正港)巴黎超現實主義團體,一邊鼓吹(反布爾喬亞社會的)自由與放縱、一邊強制嚴守規範(主義及其宣言的紀律),自始便充滿了自相矛盾的張力。
作者也多次重申,超現實主義最初其實並非一場「藝術運動」(甚至根本絕緣於視覺藝術),而是一種銳意悖逆布爾喬亞社會的反叛生活、知識論和存有論、文化與社會的激進革命。藝術形式上,超現實主義始於文學(阿波利奈爾、布勒東、阿拉貢、艾呂雅......),爾後反以繪畫廣為大眾所知(尤其達利),其詩歌根源漸被遺忘。儘管書寫和繪畫對立,各自也有內部辯證;「自動書寫」牽涉的「知性論 vs. 潛意識」;馬格利特調度與部署「寫實元素」(甚至學院傳統元素) 藉以構造「超現實」前衛作品;米羅先有以繪畫反繪畫、後有以「畫框」替代繪畫做為作品......。凡此種種,「悖論」也許是推進超現實主義的首要動力。
莫里斯透過群像敘事,一邊分析超現實主義論述與實踐的內部矛盾結構,一邊講述國際流動、多點起源、交互影響(或鬥爭)、此消彼長的超現實主義史。立體派、達達派、基里訶 (Giorgio de Chirico)等,對超現實主義的誘發與影響甚鉅,而這些源點在超現實主義活力最充沛時被成員們高速吸收、轉化、甚至揚棄──基里訶早期作品被奉若神明、後期作品被棄如敝屣,即是一例。米羅、馬松(André Masson)、馬塔(Roberto Matta)、帕倫(Wolfgang Paalen)等人則對二次戰後美國抽象表現主義的興起發揮作用,雖然帕洛克(Jackson Pollock)的畫布,在作者(以及布勒東)眼裡,可能比許多歐陸超現實主義者更接近超現實主義的原初場景。
待全書接近尾聲,莫里斯才讓畢卡索終於正式登場──雖然他始終沒有加入超現實主義任何一個派系或圈子。同被作者納入超現實主義群像,畢卡索與他的鐵粉布勒東,卻抱持近乎相反的觀點:布勒東定義超現實主義為一種「哲學」與「社會革命」,畢卡索卻從「藝術再現」上解釋它。1924 年布勒東發表第一份《超現實主義宣言》之際,尚未納入視覺藝術,但稍早 1917 年畢卡索應考克多 (Jean Cocteau)之邀、為芭蕾舞劇《遊行》(Parade)設計布景時,已然提出「超現實主義的視覺再現」觀念──而作者不無認同畢卡索自稱「超現實主義第一人」。

眼球的故事
詩人考克多的電影已被納入超現實主義電影的系譜,但系譜裡最知名者仍是西班牙導演布紐爾 (Luis Buñuel) 的《安達魯之犬》(Un chien andalou, 1929)。那個驚世駭俗的開頭──劃破一個眼球,可以視作超現實主義在大銀幕上的宣言:割除眼翳,一如刮除船腹的纍纍藤壺,好讓船艦得以向前航行。
無獨有偶,作者在書裡也摘錄了多則超現實主義者關於「眼球」的隱喻。恩斯特認為「一隻眼往外直視現實,另一隻眼(內在之眼)向內直視自己。」意外失去一隻眼睛的布羅納(Victor Brauner) 將這只瞎眼加以神話化:「睜一隻眼,閉(瞎)一隻眼,反而看見人生的靶心。」費妮因為少女時代一段「醫用繃帶長時間矇住雙眼的幻想練習」的時期,而預先鋪設了通往超現實主義視界的道路。觀念藝術第一人、以西洋棋標誌其智力遊戲形象的杜象則一向反對「視網膜藝術」。
擲去超現實主義畫筆、日後成為一名動物學家的莫里斯,曾經邀請米羅參觀他任職園長的倫敦動物園。這趟參訪之旅,莫里斯陪同米羅行過了鳥禽館、夜行館、昆蟲館、爬蟲館...。今日觀之,這本莫里斯遲至九十高齡才出版的超現實主義者之群像,恰似遙遙呼應了多年以前那趟動物園之旅,形形色色的飛禽走獸一一現身,聲色犬馬、各有擅場。
莫里斯記憶猶新,當天在動物園裡,年邁的米羅像是興奮的孩子,當一尾色彩斑斕的爬蟲向獵物襲擊時──「幾乎能聽見他眼睛亮起來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