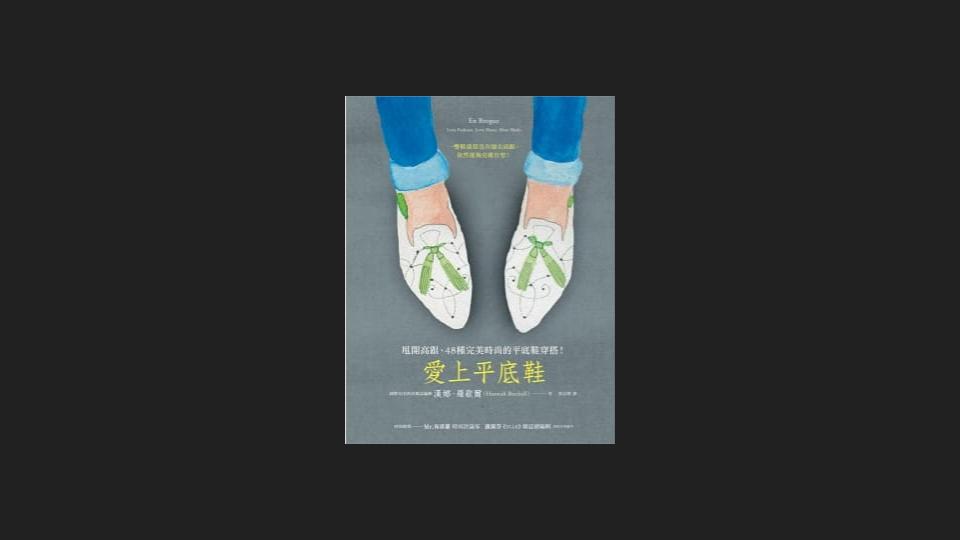1960 年 1 月,就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的一場會議之後,與會者莫不為剛果的命運感到惴惴不安。
那是在剛果共和國獨立的前夕。來自殖民地的 13 個政黨領袖,組成一股強大的團結勢力,否決比利時政府規劃的獨立時程表,並提出立刻選舉的訴求,企圖於當年 6 月 1 日,就要剛果宣布獨立。
然而,即便剛果人已經迫不及待要迎接奪回自主權的一天,當地先前卻從未有過全國性選舉的機會,遑論由本地人實際治理的經驗。加上殖民政府的刻意打壓,剛果截至 1960 年為止僅有 30 位大學畢業的本地生,嚴重缺乏接替政權的治國人才。
由於這樣薄弱的政治基礎,當那 13 個政黨領袖在很短的時間內,因礦業利益爭奪、與外來勢力藕斷絲連等問題而分崩離析,而美國又試圖要介入影響剛果內政的情況下,剛果在獨立不到兩、三年的時間內,再度陷入混亂不堪的局面。
這樣的歷史脈絡,便是美國作家芭芭拉・金索沃(Barbara Kingsolver)寫作《毒木聖經》的背景。
該書描述一個來自美國的傳教士家庭赴剛果傳教的經歷。金索沃採用牧師太太及其四個女兒的視角貫穿全書,呈現出他們一家人因衝突、拉扯,進而被迫正視家庭內部性別與權力課題的張力。面對擇善固執的牧師先生/父親拿單,這些受到非洲文化與生活經驗衝擊的女性既反思他們的家庭,也開始對家庭以外的他者與彼此間的關係有了新的理解。
在這裡,牽引著這群主角向前走去的大歷史是一股持續形塑其樣貌的力量;後殖民時期剛果的困頓與出路,也透過這家人的故事具體而微地被描繪出來。女性敘事因此成為一種隱喻非洲的聲音,讓家庭與殖民關係這兩條軸線在行文間交錯並相互印證。
但這本書所要述說的遠遠不只如此,它同時還隱約顯露出金索沃在思考政治改革的企圖。從角色設定看來,傳教士一家人各自有其程度不一的失能之處──這裡所謂的失能,是在文化概念下身體、語言或者互動關係的失衡,於是有些人的感知因此遭到限制,也有人便藉此超脫出原先看待世界的方式。後者的經驗甚至成為是她們得以反省,且翻轉其認知世界的重要基礎。
從這樣的關懷做為出發點,我認為金索沃其實是在剛果的土地上,企圖說一個屬於美國的故事。在這個故事裡頭,反思殖民與援助連帶而來的權力關係只是一個層次,顯然作者更積極地想要帶出這些個人和不平等關係翻轉的可能性,讓《毒木聖經》成為是驅策社會改革能量的一種媒介。
失能者的毒木聖經
在《毒木聖經》裡頭,牧師拿單是一個特別的存在,看似本書的靈魂人物,卻從未發出自己的聲音。換言之,我們只能夠藉由旁人的敘述認識這位一心一意只想教化並改變剛果人的白人牧師:一方面對於上帝之言深信不疑,另一方面卻又因為這樣的特質失去同理與傾聽的能力。
舉例來說,初抵欲傳福音的村莊基蘭加之際,拿單即當著眾人的面斥責袒胸露肚的婦人是「黑暗的靈魂」。習得些許剛果語之後,拿單立刻想要跳過當地人轉譯的冗長過程,自己混雜著英、法語和剛果語傳授福音,反而往往辭不達意又弄巧成拙。即便如此,拿單從不覺得自己有哪裡做錯,認為是當地居民不願接受上帝的祝福。
這些拒絕認識和同理的舉措,就像是他那過去因打仗而受傷的左眼,模模糊糊地好似已經理解了風土民情,真要描述或是與人真正的互動起來,卻與實際情況有著不小的落差,預示了他最終的失敗。
然而,就算家中的其他人看見他的盲點,她們在家父式權威的影響下,仍無所遁逃。牧師娘奧利安娜在口白中透露出自己的痛苦與絕望,但她的身體、她的靈魂卻無法擺脫以拿單為名的家庭想像、宗教理想和非洲願景。為了丈夫與孩子們,她失去自主的能力。
奧利安娜驕縱的大女兒蕾切爾,心心念念舒適美好的家鄉,在父親不斷堅持要留在當地傳教的情況下,只能夠堅持自己的那道防線,至始至終不願去理解剛果人,喪失了開闊心胸的能力。
相較於前面兩個人的消極抵抗,老三艾達的視角就為讀者帶來驚奇,彷彿可從她的眼中窺見非洲人的心思。艾達雖然因偏癱生為瘸子,這卻使她能夠以有別於他人的視角認識世界。比如她注意到基蘭加居民並不會將殘疾者與一般人視為不同,不良於行的母親就算爬行,也得履行母親的責任──四處奔波為孩子張羅每一頓飯。
對當地人來說,失能不過是生活附帶而來的產品,是日常的一部分,西方人看待身體正常與否的界線在這裡並不存在。這在艾達看來,並不是什麼完全新穎的概念,反而更加堅定她內心的想法。她自小便意識到身體與他人的差異並非侷限,反倒是開創更多可能性的契機。
比如語言,她喜歡玩文字遊戲,喜歡一本書從頭讀到尾以後,再從後面讀到第一頁。就在反覆不斷重組與排序的練習之後,她意識到剛果語裡的許多單字和某些英語單字一樣,都可以反向理解,意思互相對立:「西耶波」,指可怖的毀滅性暴雨,但也可以表達截然相反之意。
藉由艾達的對白,書中許多對話的場景躍然紙上,拿單之所以始終無法與居民溝通的原因昭然若揭。這也才令我醒悟到,人們很多時候會誤以為彼此正在對話,實際上卻往往只是在喃喃自語。
剛果共和國獨立之後,基蘭加酋長於一次牧師佈道時,走入教會,要求在場民眾一起投票,決議是否讓拿單繼續他的傳教事業。無視於拿單的反對,酋長鐵了心表示,遠在白人來到這片土地以前,老人家要他們學著坐下來聽別人講話,透過分享交流的方式,直到每個人都感到滿意。
「白人卻告訴我們」,酋長說,「快投票…你們用不著都同意,這沒必要!如果兩個人投贊成票,一個人投否決票,事情就搞定了…就算小孩子也能明白這樣的事會怎樣結束。火堆裡需要放三塊石頭才能架起一口鍋。拿走一塊,只剩下另外兩塊,會怎麼樣?鍋子就會在火堆上潑翻。」
投票終了,耶穌以 11 比 56 票輸給基蘭加居民。「耶穌是白人,所以他會理解少數服從多數的法律。」酋長達成目的之後揚長而去,獨留耳邊不斷迴盪這句話的拿單一人。
努力想要引入基督宗教與民主制度的拿單及其所代表的西方勢力,或許不見得都是要帶來壞東西,卻因為缺少實質的溝通理解,最終淪為如此下場。就像是「毒木聖經」所隱含的文字陷阱:剛果語的班加拉意指珍貴之物,若聲調略調整則變成是含劇毒樹液的毒木。當美國白人牧師在佈道時高喊「耶穌是班加拉」,人們極可能僅因為細微差異,反倒視耶穌為毒木般的存在。這是文字意涵的翻轉,也是拿單傳教生活的翻轉,更是西方主流價值在剛果的翻轉。就在這一來一往的過程,人與人之間不但沒有因為理解而拉近距離,反而更是加深彼此間的鴻溝。
自我覺醒後的翻轉
村民明白地拒絕基督教還不算是個轉捩點,小女兒露絲的死亡是這本書開始翻轉的起點。在她死後,這一家的女性終於擺脫父親的束縛,往各自的人生道路上走去。奧利安娜選擇帶著女兒們離開獨守基蘭加的丈夫,蕾切爾因受不了一路上的磨難而選擇與非洲的白人權貴出走,艾達則是最後唯一與母親回到美國生活的人。
至於尚未提及的二女兒利婭,她早先總亦步亦趨地跟隨父親,卻在遭逢如此重大的變故之後嫁給一位剛果人,從此與做為運動倡議份子的丈夫為生活、為剛果的未來共同奮鬥著。
說到利婭,因為直接見證到剛果獨立後數十年的動盪局面,她算是《毒木聖經》後半部比較關鍵的角色。在共和國甫獨立之後不久,首任總理盧蒙巴要求聯合國協助趕走比利時部隊,建立一個實質獨立的國家。盧蒙巴卻在聯合國尚未回覆之際,又再宣稱要請蘇聯幫忙,想藉此要脅聯合國就範,導致美國政府後來安排了刺殺盧蒙巴,並且介入剛果內政的計畫。
利婭與她的丈夫一方面因為過去跟隨盧蒙巴的緣故,不斷遭受新政府打壓;另一方面仍持續串連國內運動網絡,並嚮往著於1970至80年代與蘇聯結盟,正致力於打造共產主義社會願景的鄰國安哥拉。
為什麼會說這是在剛果土地上的一個美國故事呢?我認為像是利婭的種種經歷,是金索沃企圖在告訴讀者即便有許多界限仍難以跨越,美國人卻是有機會能夠與過去這些被壓迫者站在一塊,追尋更美好的未來。雖然也是可以和奧利安娜、蕾切爾一樣,終究選擇回到舒適圈,那些殘存於體內的非洲碎片卻將揮之不去,影響著自已的生命。
而跟著母親回到美國的艾達,在書中奇蹟式地擺脫了偏癱的痼疾,成為在醫學院研究熱帶疾病的專家。在我看來,偏癱的治癒像是一種隱喻,當她從剛果走了一遭回來,便在文化意義的翻轉過程中治癒了她的失能,使她得以擺脫西方的偏見,像「正常人」般的生活著。
那麼剛果呢?它在獨立後翻轉的可能性又在哪裡?《毒木聖經》把它定位為美國等強權的受害者,還等不到真正的獨立,便在冷戰框架下因共產主義遭受苦難。利婭與其丈夫對安哥拉的憧憬雖帶來一絲希望,卻似乎仍框限在前述的困局之中,好像只有自由民主、共產思想這些外來的力量,才真正有辦法帶領他們走出泥淖。
什麼才是剛果人的出路?直到闔上這本書的時候,我都還是感覺金索沃筆下描寫的剛果困境與出路,似乎並不真的屬於這個國家,感覺更只是屬於一般大眾對於非洲與第三世界國家刻板印象中的那個框架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