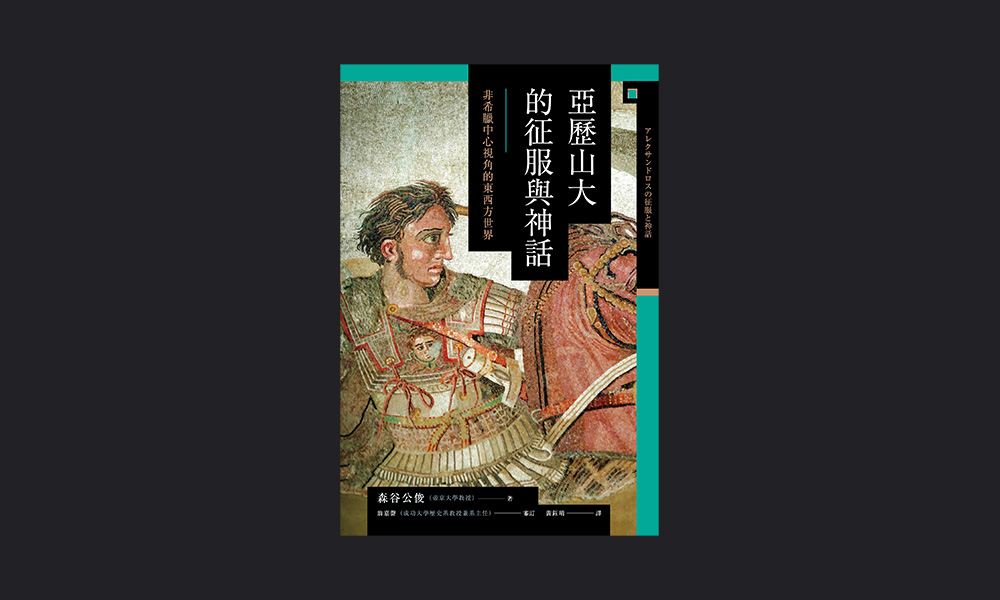本書是關於西元前一四六年[1]羅馬攻陷北非迦太基和希臘科林斯,勢力邁向尖峰,但同時也見證羅馬共和開始發生系統性崩潰;之後接著發生一連串改革、反改革,甚至暴力及內戰,直到西元前八○年蘇拉這位羅馬「最後的共和主義者」[2]贏得內戰,重整憲法,恢復共和為止。
這是羅馬共和最後一次力圖振作的戲劇性時代,充滿不同政治理想及立場的對抗,以及有趣政治人格的刻畫。當蘇拉在西元前七八年過世,這復原的共和及和平立即化為雲煙;之後便是前後「三巨頭」政治以及更大規模內戰及殺戮的故事。羅馬共和憲政架構在如此衝擊下無以為繼,最後不得不代以專制獨裁的「元首政治」(Principate),來統治這地理遼闊、族群複雜的多元文化帝國。
羅馬演說家西塞羅在蘇拉時代初次任官、最後在三巨頭政治中殞命,經常懷念更早時期的共和,認為那時各階層同心和諧、凝聚共識,但舉目自己所處的時代,羅馬已經淪為藏汙納垢、齷齪不堪的「羅穆盧斯的糞坑」。
羅馬人的政治智慧
羅馬人是尊重歷史及傳統的民族。他們在提出任何主張時,會援引 mos maiorum 為據。這詞有「祖宗成法」(the way of ancestors)或「多數做法」(the way of the majority)的意義。
傳統對羅馬人不是包袱,而是種經過時間批判及揀選後的正面力量,具有權威及引導的地位。因此當西元前五○九年推翻專制獨裁的王政後,羅馬開始共和,除非在緊急狀況創造出任期有限的獨裁官外,會一再強調國家必須集體領導、相互制衡(如一年一任、互有否決權的兩位執政官,及能否決其他官員並互相否決的十位護民官)。任何有與他們最厭惡的「王」[3]相關的行為或言論,如在饑荒時個人出錢賑災來討好群眾,或提案分配公地給人民等的民粹行為,羅馬人都會大為警惕防範。
羅馬人民從最早時候被分做「世家貴族」(patrician)及一般「平民」(plebeian)兩個階層(ordones, orders)。這分別如何而來,已不可考,但可能與宗教有關:世家貴族與生俱來便被賦予執行徵詢神意儀式(taking auspices)的權力,而共和國主要官員如執政官,在執行被授予的 imperium(指揮權)時,如出征,需先獲得神意許可。
世家貴族因此在羅馬共和早期壟斷重要官職。這特權又因為羅馬社會存在「侍從主義」(patronage)的上下紐帶關係,而更形鞏固:上層保護主階層與下層受保護階層,雙方存在著具有準司法地位的權力與義務關係,如在政治上後者支持前者或前者在法律上庇護後者等。
但平民在受壓榨或欺凌,無處申冤、忍無可忍時,唯一反抗方式是集體脫離羅馬,另立城邦。這招時常奏效,因為當時羅馬共和作戰方式已從貴族率領隨員以騎兵為作戰方式,轉變成地中海主流之民兵密集步兵隊形作戰,因此能屢屢強迫貴族讓步。這種衝突被稱為「階層鬥爭」,被認為是推動羅馬政治演變的力量。
這在羅馬歷史上曾發生多次,如西元前四九四、四五一、三六七及二八七年,因而陸續有護民官及平民會議(Concilium Plebis)設置、《十二木表法》公布、執政官開放給平民,以及最後通過象徵階層鬥爭結束的《豪登西亞斯法》(Lex Hortensia):護民官主持的平民會議(Concilium Plebis)可以立法約束全體公民。
在這羅馬政治演變過程中,最明顯特色是不同階層不會將自己主張推到極端,強迫對方全盤接受,而是努力求取雙方都能接受的共識。例如在西元前三六七年當執政官開放給平民時,貴族同時設立一個專門負責司法的法務官,但僅限貴族擔任,因此貴族既給出、但又拿回。每次這樣的改革都能塑造出更具凝聚力的社區,而這提供羅馬良好的擴張基礎。
改革後的羅馬依序在拉丁姆平原,然後在伊特魯里亞及坎帕尼亞等地,逐漸擴大羅馬勢力範圍;羅馬在西元前四至三世紀征服亞平寧山難纏的薩莫奈人;最後在西元前二七五年擊退希臘化國王皮洛斯(Pyrrhus),雄霸半島南部的「大希臘」(Magna Graecia),統一波河以南的羅馬義大利。
羅馬在擊敗鄰邦時,並未採取當時常見的屠殺役齡男子、販賣其他人為奴的政策,而是要求懲罰元凶、賠償戰費、沒收領土[4]及接受羅馬領導,提供兵源參戰。這對戰敗者是難以拒絕,且能加入羅馬這強大國家的擴張,分享戰利品。羅馬這樣的做法其實是重現在階層鬥爭時,雙方所展現的誠意。
於是羅馬領導下的義大利逐漸形成一個「義大利聯盟」(confederation of Italy)的架構。箇中成員因為不同歷史經驗,而與羅馬有親疏關係。如拉丁社區的菁英階層獲頒公民權,一般人民享有通商(commercium)、通婚(conubium)及移居羅馬便享有公民權(migratio)的準公民地位;或次一等者,享有沒參政權的公民權(cives sine suffragio);或雙方關係由個別條約明訂之。
羅馬則視盟邦表現而提升或降低地位,但對背叛則是無法容忍。在古代世界,軍事行動是種投資極大、風險極高,但利潤也極大的事業,而羅馬既然如此成功,曾經的手下敗將樂於加入聯盟,分享戰利品及土地。加上羅馬是貴族寡頭共和,盟邦寡頭領導階層也往往受到羅馬支持及保護,因此向心力極強。所以即使羅馬在漢尼拔戰爭最黑暗的時刻,大多數盟邦仍始終不渝。
另外,聯盟每次出征,都會提供羅馬一半以上的軍力,使羅馬可以承受如漢尼拔在西元前二一八至二一六年的連續重擊後,卻仍可在二一五年另闢馬其頓戰線,這在古代世界無人可及。羅馬動員的人口比例,直到拿破崙時代,或甚至一次大戰時,才可相比。
裂解的羅馬共和
羅馬內部政治整合以及建立義大利聯盟有極密切關連,每次更高內部共識的凝聚,促成對外擴張的成功,而成功又增加羅馬人的自信,促成更進一步的政治改革,為下階段對外擴張奠基。這加乘的效果使得擴張節奏愈來愈快。羅馬共和花費兩百多年統一義大利半島,經過第一及第二次迦太基戰爭的六十年後獨霸西地中海,但僅僅約十年便讓東地中海的希臘化三大王國向羅馬俯首稱臣。這些成就是羅馬人政治智慧所帶來的,而元老院主導這過程,威望極為崇高穩固。
希臘化時代史學家波利比烏斯讚嘆這些成就,將之歸諸羅馬的「平衡政體」(balanced constitutions)或「混合政體」(mixed constitutions)。其中以元老院代表貴族政治,執政官代表王政,而公民大會代表民主政治;三者都有發聲機會,但又彼此制衡。[5]所以在西元前一四六年前羅馬菁英成功地將羅馬平民、義大利盟邦以及在擴張中提供各項軍需服務的羅馬和義大利騎士階層[6],整合進入這過程中。當羅馬勢力踏出義大利時,這又包括行省居民及附庸國家。
這些成分經過長期磨合,在西元前一四六年到達高點後,但卻因為種種如本書中所提之問題而開始迅速裂解;其中各成分更因彼此影響而迅速惡化,化為連環爆炸,迅速帶來動亂、甚至內戰。這最後必須以蘇拉的武力及獨裁來重新整合。希臘及羅馬史家常毫不遲疑地以道德敗壞來形容晚期共和政治的崩解。這是因為政體如果是國家靈魂,而平衡政體帶來健全的共和國,那貴族菁英的貪婪自私及其他階層人士過度的索求,要為這系統的崩壞負責。
但早、中期的羅馬貴族何嘗不是同樣富於野心及貪得無厭?但羅馬在晚期共和已經宰制整個地中海,利益糾葛已經不再限於羅馬或義大利,而是如波利比烏斯所言的當時「已知全世界」,競爭因此更加激烈,常到不擇手段的程度。這包括政客大膽利用共和體制的弱點。羅馬政體既然由許多「祖宗成法」構成,疊床架屋、相互矛盾之處所在多有,例如羅馬至少有四個由公民組成、部分功能重疊的「大會」。
任何人都可以在豐富的過去歷史中,找到自己所需的祖宗成法。因此若當初羅馬貴族以最後一位國王「傲慢的塔克文」專制濫權、侵犯貴族的「自由」(libertas),在西元前五○九年將之驅逐,開始共和,那當蘇拉堅持自己的 libertas,帶兵攻打羅馬城,同樣是以要驅逐當時羅馬的僭主、恢復共和,來為自己其實形同僭主的行為辯護。
另外,羅馬人以 SPQR(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羅馬元老院及人民」)來指稱自己國家,但元老院的統治基礎基本上是道德性及社會性的,如auctoritas(moral authority,道德威望)這字所顯示。只有人民組成的大會才有權通過法律(lex),而元老院只能給的是「建議」(consultum),即使「緊急建議」(SCU,即 Senatus Consultum Ultimum),也只是給執政官緊急處置一種「道德支持」,官員事後還是會被法庭或公民大會追究。
元老院在西元前一四六年之前因為成功領導羅馬及壓抑社會矛盾,力能說服人民通過需要的法令,但一旦這 auctoritas 遭到質疑,例如出現愈來愈多無產階級人民、奴隸戰爭不斷爆發或兵源不足導致戰事失利,元老院威望一步步削弱時,人民在適當領導下便可能取而代之。
之前平民以退出羅馬城為手段,來消極抗拒,但西元前二八七年《豪登西亞斯法》允許護民官主持平民會議來立法,強迫冥頑不靈的元老貴族就範,這造成護民官迅速崛起,操弄這極具破壞力的憲政武器。
其實《豪登西亞斯法》通過後一百多年期間,因為貴族領導得當,此法存而不論、備而不用,但潛力卻常隱隱浮現,例如西元前二一七年被漢尼拔殺死的弗拉米紐斯(Gaius Flaminius)、出征西班牙及北非的「阿非利加征服者」老西庇阿、擊敗馬其頓腓力五世的昆克修斯・弗拉米尼努斯(Quinctius Flamininus)等人的生涯,都是以訴諸「民意」,越過傳統元老院在幕後「喬共識」的政治運作方式。
政治上的潘朵拉瓶子
史書一直強調西元前一三三年的提比略・格拉古改革的歷史背景,正是當時貴族領導階層在統治整個地中海及掌握和分配龐大利益上,處處捉襟見肘、拙於應付。這讓人民所具有的政治潛力隱隱浮現,而格拉古走出憲政治舞台,提供他們適當的領導人,釋放出這股難以控制的力量。
格拉古改革的著眼點是要重新黏合那已經逐漸瓦解的羅馬貴族、平民、騎士階層及義大利盟友組成的共同體,而土地法便是針對回復原先貴族與平民的關係,以及曾經讓羅馬偉大的民兵制。但這回復會打擊到貴族的既得利益,並涉及義大利盟邦的權益。
另方面,這改革對任何出身高貴如格拉古是個難以拒絕的機會;他若成功的話,受益人民將會被一起收納到他的政治隨從(clientela)之中,使他成為在政壇上無人匹敵的新勢力,而這其中的武器便是護民官主持平民會議來通過土地法。
類似改革需求其實在格拉古之前已經有人提出,如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的好友萊里亞斯(Gaius Laelius)。他被稱為「智者」(Sapiens)是因為當他提出類似議題時,被元老院勸阻下,識相地撤銷。
元老院不盡然全是利益薰心、毫無良心之徒,因為即使如提比略・格拉古背後也有群為他規劃、尋找法源的權貴人士。但這樣法案所涉及的政治地景重組及權力再分配,實在無人能預期會如何發展,擔心這是否如潘朵拉瓶子一樣,一旦打開,禍福難料,或貴族能否承受損失及衝擊。
提比略曾設法與元老院協商,但被拒絕,因為這想必已是經過數十年被不斷討論的議題,不是只有格拉古才有的真知灼見。結果最後是提比略強迫攤牌,在平民會議通過土地重新分配;另外,提比略因為改革經費,插手帕加馬國王遺產,侵犯元老院外交及財政的傳統特權。
這些透露出更多權力重組的變數。元老院一向追求共識政治的做法,面對這種硬幹,別無選擇,也以暴力回應:這代表的是元老院也無能為力,只能胡亂反應。之前的羅馬政治演變未曾流血,但這一旦發生,只會愈演愈烈,最後像龍捲風一樣失控。
這西元前一三三年不祥的格拉古改革開啟晚期共和動亂的歷史。在政治上出現一群以護民官為首的 Populares(the Populars,群眾派),利用平民會議立法的憲政手段為武器,進行激進改革。他們所面對的是原先的保守元老院勢力,現在稱為 Optimates(the Best,貴族派)。
群眾派立場所涵蓋的主題在提比略弟弟蓋烏斯改革中被全面提出。簡單的說,他的改革是要將這幾百年來曾被元老院領導階層整合成功,但逐漸忽略、壓抑及最後失能的不同力量,都給一一找回,重新黏合成完整平衡的共和國。所以蓋烏斯繼續分配土地給平民、提供給羅馬市民穩定、補貼價格的糧食、設置殖民地安置無地市民、在司法上賦權騎士階層來壓制貪贓枉法的元老,以及計畫頒贈義大利人民羅馬公民權。
格拉古兄弟的做法是要將歷史時鐘的指針往前撥,回到美好的過去。但這些改革包裹既廣且重,政治效應完全無法預期。任何同情改革的穩重元老恐怕都無法短期內消化任何一項議題,何況是面對整個法案包裹。經過十年仍不知如何回應的元老院,只好又再度以暴力回應,而群眾派再度受挫。元老院像是無能的父親,只能以家暴來對付妻兒子女。
群眾派的回應則是更激進的立場,並將改革勢力武裝化。他們一方面將政治暴力引進到政治運作中,這後來在三巨頭時期發展到如克勞狄烏斯(Clodius)及米羅(Milo)的政治幫派,橫行街頭,讓羅馬政治完全失控。另方面,這股勢力也與軍閥聯手。
這始作俑者是政治新人(novus homo)馬略(Gaius Marius):他引進普羅無產階級[7]進入軍中,承諾在解甲歸田後,會與護民官聯手通過土地法,安置他們。這使得軍閥與護民官利益一致,在政治上結合,更使貴族派無力回應。
軍隊也不再效忠羅馬,而是招募他們的將軍。這對共和國更是警訊,而護民官反而變成配角。現在國家統治基礎不再是元老院的 auctoritas 或公民大會/平民會議的立法權,而是擁兵自重的軍閥。當群眾派政客想頒贈公民權給義大利人及改變投票方式,因為會損及羅馬公民權益,而遭到抗拒時,這些激進改革者也向義大利盟友伸手,結果爆發羅馬人與義大利戰友、形同內戰的「同盟戰爭」(Bellum Socii)。
這些分裂當然都有歷史環境來促成,例如在南方的朱古達戰爭及緊接著北方辛布里人和條頓人入侵,使得原先可能是權宜之計的做法,變成既成事實,例如馬略在七年內擔任六次執政官。馬略在群眾派崛起的過程中極為關鍵,但他招募無產階級的人當兵,豈不也是宣告提比略·格拉古的土地改革無效?在他第六任執政官任期間積極向貴族派靠攏,是不是也透露出他對激進改革的疑慮?但動機已經不再重要,因為暴力釋放出的歷史力量會將人推著往前走,不管他願不願意。
最後只有蘇拉的暴力才能暫時終止歷史的推進力量。他除了要贏得內戰,還需對改革派的政敵進行大規模整肅清算,然後再以獨裁權威,重新修憲,恢復共和。這實在是很弔詭:若當初羅馬因為最後一任國王獨裁專制而推翻王政,開始共和,現在的共和卻是必須藉由獨裁專制、殺戮肅清來重新啟動。
但誰能對蘇拉自己立下的榜樣視而不見呢?他自己進軍羅馬,發動內戰,透露出共和政治所預設的凝聚共識其實不再可能;他改造後的共和彷彿只是用葉克膜來維持不知那是否該救的生命。何況他身邊有如此多比他更肆無忌憚、毫無政治理念,但手握兵權的軍閥,如龐培或克拉蘇。當他在改革後安然退休,壽終正寢,新任執政官雷比達立即興兵攻打選他出任執政官的羅馬!這正說明赤裸裸的暴力現在是唯一的統治基礎。
奧古斯都的選擇
凱撒對蘇拉放下大權不管,以為改造的共和會自行運轉,因此批評蘇拉不懂政治 A B C。這當然是正確的看法。但凱撒那種貿然將數百年共和傳統視為敝屣,認為只是假象,最後換得殺身之禍。共和體制雖然行不通,但共和感受或氛圍對那些仍自視有天命分享羅馬政權的共和貴族來說,仍是難以擺脫的幻覺。
更有智慧的屋大維知道這點,理解要有更多耐心及時間,來等待這曾經偉大共和傳統的消逝。所以他以共和外衣來包裝自己的專制獨裁,提出在祖宗成法裡常出現的 princeps(如首席元老,princeps senatus),但後面不加 senatus 或 populus,來形容自己的地位:他是「眾人之首」(primus inter pares),既強調共和傳統以及他獨享的專制地位,但同時超越兩者、超越 SPQR。
儘管他的權力或是兵權是史無前例地強大及穩固,他對悠久的共和傳統至少在表面上表示敬意。他既沒像蘇拉一樣放下權力,退休養老(但屋大維那時也只有三十三歲!),也沒流露出凱撒那對共和的輕蔑而遭致暗殺。他統治超過四十年,在七十七歲時壽終正寢。這虛實兼顧,才是完美政治家的本色。
蘇拉常被稱為「最後的共和主義者」或許有其根據,因為他可能真的相信外,也努力實踐,無論手段如何。西塞羅也一樣相信,甚至提出元老及騎士這些「好人」(boni)的「階層和諧」(concordia ordinum),必須成為風雨飄渺之羅馬共和的穩定力量,但沒人聽進去,因為他手無寸鐵。
早、中期共和在成功地整合許多勢力,建立橫跨地中海的帝國後,已經完成它的歷史使命,將無以為繼。提比略・格拉古等人的改革或是蘇拉的恢復共和,好像是企圖將一個曾細心組裝的機械鬧鐘,在運作失靈、崩解後再重新組裝,但每個零件其實都與之前不太一樣,組裝結果只能靠著膠水固定或束帶捆住,但已經無法正常運作。另起爐灶恐怕是唯一的辦法;這是屋大維的選擇。
本書因此是介紹這段「失敗」的過程,所以副標題說這是「羅馬共和殞落的開始」。誠然,書中詳細說明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對話及爭執,以及那些努力想恢復共和憲政理想之各式人物的故事。但當我們進入前、後三巨頭的時代,我們只會見到赤裸裸的權力鬥爭以及更多生命及財產的無謂耗損。暴力決定一切。這是如此無意義、如此徒然,人民最後也接受屋大維的選擇,選擇專制獨裁及和平繁榮,這所謂的「奧古斯都的和平」(Pax Augusta)。
(本文作者為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
[1]羅馬共和經常被分為三個時期:⑴早期共和是從西元前五○九年推翻王政,到西元前二六四年第一次迦太基戰爭爆發;這其中的主題是羅馬共和內部政治整合以及統一羅馬義大利。⑵中期共和則是在地中海的擴張時期,一直到西元前一三三年的格拉古改革。⑶從西元前一三三年到西元前二七年(或西元前三一年),則是晚期共和,這是一段極為動盪的時期。
[2]這取自Arthur Keaveany的書名:Sulla: The Last Republican。
[3]拉丁文的「王」(rex)在羅馬政治史中並非單純的「王」而已,而是影射一位能力超凡、僭奪原來屬於大家共享之權力的人,是種負面、甚至近乎汙衊的指稱。這概念與希臘的「僭主」(tyrannos)極為相近。任何被認為會壟斷權力、將自己抬舉到他人之上的行為,都招人懷疑,被認為是僭主。格拉古兄弟當時便是被如此看待而遭殺害。
[4]常是三分之一,這成為羅馬「公地」(ager publicus)主要來源之一。
[5]但有人批評波利比烏斯在西元前一五○年時寫下這樣的評論時,似乎無視羅馬元老院的絕對領導地位,更何況他深處羅馬政治魔術圈裡,而他的保護主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更是貴族中的貴族。但這種批評忽略了希臘人如何理解政體(politeia)的思想史傳統。元老院有如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所提之三分化靈魂(tripartite soul)的「理性」(nous),專事思慮判斷,而執行的官員則代表「義氣」(spirit,thumos),人民則是代表本能的「欲望」(epithumia),專門負責生產。羅馬元老院未曾如此盲目,會將人民或 populus 完全忘記。
[6]羅馬缺乏官僚,常將國家業務「外包」(outsource)給後來成為騎士階層(Ordo Equitum)的人來承包,從事承包國家業務的這些人統稱為 Publicani,並非只有包稅而已。羅馬可能是歷史上最常將政府業務外包的政權,也使得可以以最低成本來經營共和國及帝國。騎士階級的財富使他們有機會間接或直接介入權力運作。他們是所謂的 moneymen 或 moneyed class。
[7]Proletarii,那些除了自己後代(proles)外,無可申報的人;或稱 capite censi,普查時只有「人頭」可以申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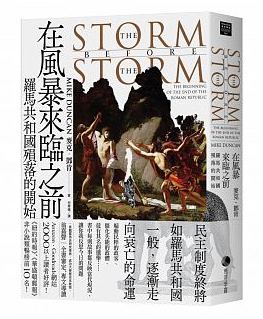
羅馬征服了迦太基與希臘,終於以地中海強權之姿崛起,但共和國的成功卻正是它毀滅的原因。本書以編年體方式,帶領大家回到兩千年前羅馬共和國殞落的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