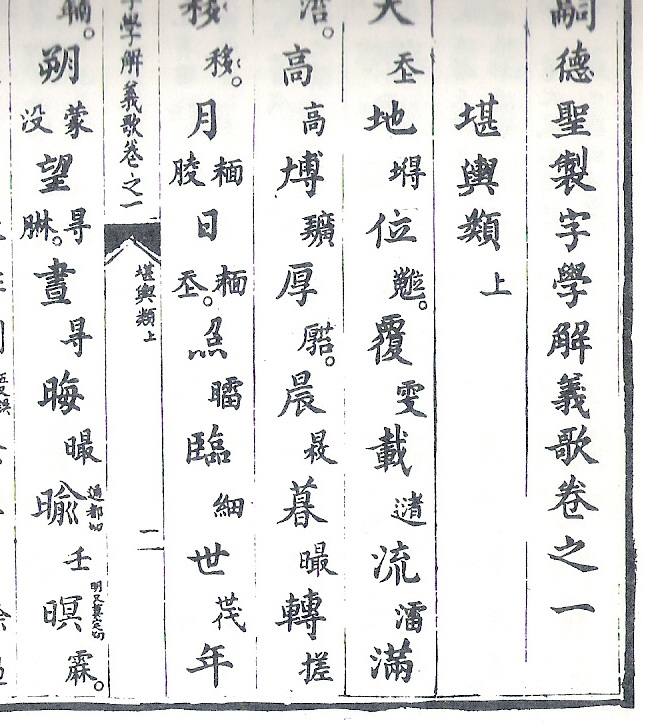一部以越戰告終為背景──或是以南越遭北越「解放」──為開端的英文小說《同情者》,已在近期譯成中文上市。雖說是《同情者》,這部小說卻毫不留情地批判了美國社會的越戰記憶。
作者阮越清是在美越裔的第二代。對於像他和他父母兩代的美籍越裔來說,美國主流的越戰電影,不僅構不上「創傷文學」,反倒自曝了美國的「超級病」(一種敝帚自珍的疾病)。阮越清透過主角之口,揭露了美式越戰電影近乎「篡奪他人記憶」的無賴面向:
我很同情天真的法國人,竟以為要開發利用一個國家就得先去瞧瞧,好萊塢的效率好多了,想開發利用的國家,用想像的就好了……這是第一次由戰敗者而非戰勝者為戰爭寫歷史。
不同立場,一樣「攘夷」
「廣義的」越戰歷史,應該可以追溯到法國殖民越南的年代。自此,一群堅信殖民者盡做壞事的越南反抗者,跟隨列寧信徒胡志明高呼「沒有什麼比獨立與自由更重要」的信條。這話不只說給《印度支那》(1992 年法國電影)的法國軍官與莊園領土們聽,更要說給 1954 年以後,在摔角場邊與法國人擊掌換手的《沉靜美國人》(2002 年美國電影)聽。特別是這個新角頭是以《獨立宣言》起家的。另一群被美國人牽著、哄著,或是自以為能利用美國人來消滅共產黨的越南民族主義者,則在法國人留下的城池中泅泳,至終游不到一統越南的彼岸。
這兩群在意識形態上南轅北轍的越南志士,儘管在越戰期間互斥對方為越奸、賣國賊,或是「醉生夢死之人」(trùm chăn)。但雙方根本是在「分工」之下,打著「攘夷」延長戰──一場始於 1860 年代,為越南封建王朝所發動的反殖民之戰。
更諷刺的是,以反封建掛帥的北越政權,仍得仰仗舊有的「集體主義」,這才打贏了「民族解放」而非「個體解放」的戰爭。而該場惡戰最為顯著的「成就」,自然是「解決」了「共和越南」,進而「放領」了「社會主義越南」。
失去「共和越南」而厭惡「社會主義越南」的許多南越遺民,無奈前往為他們「第二厭惡」的美國。特別是那些如故事所述,在戰爭期間受惠於美軍的南越軍官,以及在戰後仍然期待華府協助其「反攻復國」的「不死老兵」,對於美國往往憎惡更深。憎惡的原因不僅僅是 1970 年代起美國「越戰越南化」政策所代表的擺爛與背叛,更為深遠的理由,還是在於越美之間「同床異夢」的文化衝突。
一位真實存在的南越軍官,曾經在西貢報紙上控訴了雙方的歧異。他說:「我們永遠不會瞭解對方,儘管我們為了共同的目標而就死,我們仍將以不同儀式而就木。」(Tran Nu-Anh 2006)附帶一提的是,1960 年代初老蔣與南越總統吳廷琰之所以轉趨熱絡,跟雙方私下大有共鳴,一齊痛批老美「不識東方」、「反共不得其法」有著直接關係。
混血兒的原罪
小說中的老美,即使是美國大學的東方系主任、大費周章拍攝越戰電影的名導,乃至於被認為是越南通的博士暢銷作家,對於越戰及東方文化仍然認知偏頗。遠離火海的南越遺民,在這樣的美國社會之中,依然難以立足。越戰移民的困境,應該是身為難民之子的阮越清,最不需要資料便能輕易描述的部分。但也確是《經典老爺車》(2008 年美國電影) 裡,標準老美不易覺察與承認的事實。
認同與被認同的問題,是身為法越混血主角終其一生的心魔。就跨文化問題的角度來看,《同情者》的故事,可以說是「ㄈㄈ尺」(鄙視異國戀「CCR」的鄉民用語)劇目《蝴蝶夫人》與《西貢小姐》的「番外篇」,只不過,一個混血之子即使有機會長大成人,卻仍然得不到幸福。
這樣一個苦主,僅僅渴望做一個平凡人,一個血統單純的越南人,因為做一個血統單純的被殖民者,也比做一個有一半殖民者血統的混血兒來得強,至少他的愛國情操與愛人權利,不至於輕易被人鄙夷,至少,他不會變成一個「自我認同」衝突的「雙心人」。
這樣一個苦主,他的痛楚來自於衝突角色之間的穿梭,而非出自間諜身分旦夕曝露的恐懼;他的痛楚造就「此角色」對於「彼角色」的同情,卻無關乎自己「不是富家子弟」(這是美式[越南]戰爭片「指定曲」Fortunate Son的名句,也可說是主流美國越戰世代的聲音:It ain't me, it ain't me, I ain't no millionaire's son 那不是我,那不是我,我不是富家子弟)。
作為少數中的少數,他恰恰是自己的同情者,也是眾多對越戰認知偏頗之人的同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