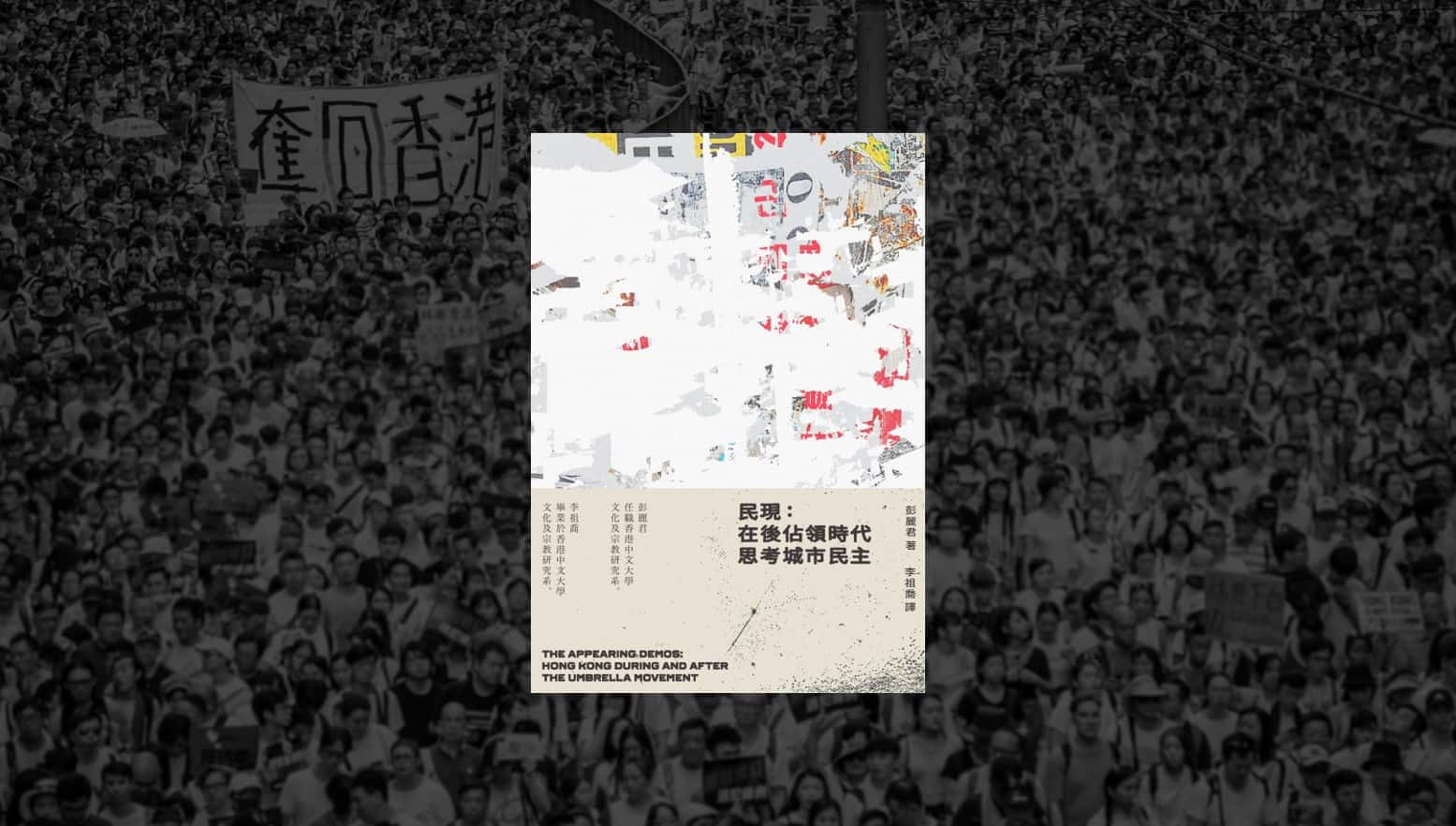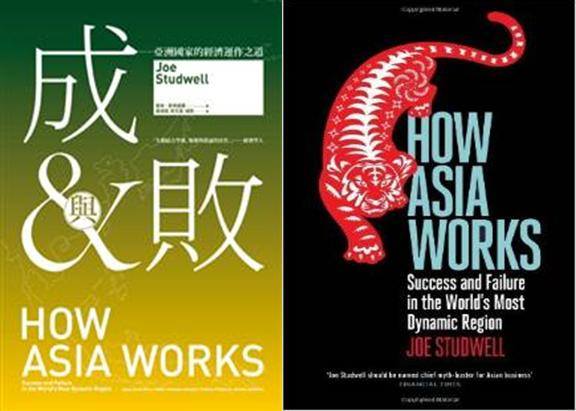當前世界正處在重重危機之中,出人意料的大事接踵而來,一再衝擊我們的固有想像。在這樣彷若無法喘息的時代,我們還有辦法思考嗎?
回顧香港的民主運動,從 2014 年轟轟烈烈的雨傘革命,到最近仍餘波蕩漾的反送中運動,事件不斷發生,我們真的能好好停下來思考已經發生過的事件嗎?在這危機時代,是否思想不得不像黑格爾筆下的貓頭鷹那樣,待至黃昏,方能起飛?
香港中文大學彭麗君教授的《民現:在後佔領時代思考城市民主》一書,展現了在當前、在持續處於危機之中的香港,「思考」如何可能。這樣說首先並不意味著這本書作為「思考」的成果如何正確、無可爭議,而是在閱讀該書的過程中,我們能夠感受到一種思考的真誠,一種縱然不乏猶豫、困惑,但仍然堅持進行論說的態度 。
該書有兩個容易引發爭議的地方:一個是作者似乎對於香港本土派引發的排外傾向持保留態度,另一個則是作者在批評民族國家主權模式的同時,似乎較樂觀看待一國兩制下的城市自治。在香港當前的緊急狀況下,這兩處恐怕會引來一些評論者的微詞,何明修教授就對此提出了明確的批評。
筆者看來,《民現》一書能探討的主題極為多元,但其背後蘊含著某種具有連貫性的思考線索,而那些引發爭議的文字,也是此種思考所導出的一部分。
作者將《民現》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討論雨傘運動的特徵及其中的參與者,第二部分分析運動中的社交媒體、藝術作品以及紀錄片,第三部分則轉而討論更為普遍的政治思想,包括城市權、香港價值以及法治問題。雖然作者並未明確說明這三部分之間的邏輯關係,但第二部分的分析實際上承接了第一部分開啟的線索,進而支撐了看似有所跳躍的第三部分。
其中的關鍵就在於,藉由佔領運動中呈現的「民現」、「共居」,要如何推導出反對單一主權的城市共同體構想。換言之,該書的特色就是,作者試圖通過雨傘運動內部的具體樣態,而非其運動理念、運動成果,來構建香港的政治想像。
打破新自由主義的想像:現身的複數個體
相較於其他社會運動研究,該書另一大重要特色就是,它始終貫穿著對於著名政治思想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書中譯作阿倫特)的討論,其篇幅幾佔全書三分之一,以至於該書中文譯者李祖喬表示,作者曾考慮在中文版中刪掉這些部分。不過,我認為這一偏重理論反思的部分頗為關鍵,它不單單是一種頗具深度的鄂蘭研究,並有力地推動了該書的思考線索。
首先,該書標題以及第一部分對於雨傘運動的整體討論,很大程度上借助於鄂蘭的「現身/顯現」(appearing)概念。在鄂蘭看來,政治意味著人們勇於公開地展現自身,並由此開啟一個共同行動的公共空間。作者藉此解釋了在雨傘運動中現身的民眾,如何打破新自由主義環境下人們原本對於政治的悲觀想像。
不過在第一部分的討論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對於「佔領作為象徵」與「佔領作為過程」這兩者進行了區分。
簡單來說,「象徵」層面意味著,各種佔領運動都會為了實現運動宗旨、凝聚運動能量,而力圖維持一個集體性的抽象「我們」;作者卻同時在作為「過程」的運動中發現一個個自主性個體,擁有屬於自己的「執意」(willfulness)與固執,並每每偏離運動的整體方向。雖然這些「執意」的個體會為運動目標的達成造成麻煩,但作者認為恰恰因為這些自主性個體的存在,才使得運動真正具有政治意義。
該書對於複數的自主個體的強調,並非僅僅停留為理論性的主張,相較於其他關注運動宏觀進程的研究著作,作者更以細膩、生動的筆觸,為我們描繪了一個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參與者形象。除了知名運動領袖黃之鋒、周庭外,作者更重點刻畫了王婆婆、王澄烽、大黃伯這些各有其堅持與故事的人物群像,讓運動「過程」中的眾多個體有血有肉地「現身」。
不過隨著雨傘運動的黯然退場,這些曾經「現身」的個體又都重新隱沒在現代大都市的日常景觀之中。從結果來說,雨傘運動大體上是失敗的,那麼這些「現身」是否並未留下任何政治意義呢?
實際上,這同時也是鄂蘭政治思想自身中存在的一個難題。依鄂蘭所述,藉由眾人聚集而形成的共同行動,總是脆弱不定又稍縱即逝,一旦眾人散去,則此「現身」之政治空間亦不復存在。
然而,作者似乎不想局限於這種短暫的「現身」空間,而是力圖將此「現身」轉化為更具持久性的「共居」生活。[1]佔領期間的民眾無疑處在某種暫時的「共居」狀態,但此狀態已隨著運動的結束而消逝無痕。該書第二部分對於社交媒體與藝術作品的討論,則試圖告訴我們,「共居」可以不僅僅是佔領空間中的短暫相遇,還有望構成這座城市的日常。
運動給我們留下了什麼:社交媒體與作品所構成的共通世界
《民現》的第二部分逐章討論了社交媒體、藝術作品以及紀錄片這三個主題,表面上看,作者蕩開一筆 ,另闢出一個側寫佔領運動的專題區塊,亦有不少評論者稱許這一部分的獨特貢獻。
我認為這部分不僅僅是獨具特色的專題探討,而且在全書的整體寫作上隱然具有承前啟後的樞紐性作用──唯有經過對於社會、作品與記錄的分析,第一部分的「現身」政治意義才得以維持、延續,而終章的普遍性政治思考也才得以免於架空,免於淪為作者的個人信念。
要理解這一點,就必須注意到作者在第二部分中,對於鄂蘭思想進行了兩個創造性解讀、改造的地方:一個是關於「社會」與「政治」之關係的理解,另一個則是關於(藝術)作品的政治意義。
首先,鄂蘭的政治思想有一個極為關鍵卻又引發後世諸多爭議的地方,就是她嚴格區分了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並認為政治行動必須是藉由行動者放下私人的利益、興趣而進入公共領域,才得以出現。
鄂蘭身後數十年來愈加盛行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浪潮中,這種公私區分無疑很容易遭到質疑,因為它意味著不應該將個人身份認同、主觀感受,直接帶入公共領域的討論。作者對於鄂蘭的這種區分亦有所不安,因而創造性地改造了鄂蘭的另一個概念,即「社會領域」(social realm)。[2]
鄂蘭原先的思考脈絡中,「社會」多半具有較負面的意涵,因為「社會領域」的興起正意味著公共領域被私人領域全面入侵的現代危機。然而,作者卻根據鄂蘭一篇評論美國當時種族問題的文章,主張鄂蘭實際上強調要保護社會領域,因為它不可或缺地連接了公領域與私領域。
強調社會領域的中介連結作用,對於該書具有關鍵性意義,這意味著在公共領域「現身」的民眾不會在離開運動後,就馬上遁入獨善其身的私人領域,而是在社會領域中通過各種社交媒體,形成具有延續性的「主體互聯」(intersubjectivity)。作者接著也由此延伸討論了社交媒體如何有助於反送中運動的產生。
書中看似耗費許多筆墨,糾纏在鄂蘭對於社會領域的理解問題,作者也提出自己的另一種觀點,但事實上,鄂蘭的立場本身就有其合理性與批判力,因此這是一個具有討論價值的普遍性問題。
我認為社交媒體對於當代社會的影響,本來就有其利弊兩面,就負面效應來看,當今網路世界所煽動的各種極端化情緒動員,乃至同溫層、後真相等現象,可以解釋為私人情感、信念擾亂公共領域的結果;至於社交媒體對於政治運動的正面作用,作者確實提供了有力的解釋。這不僅是對於鄂蘭思想的一種創造性發展,也為該書所討論的「現身」政治提供了穩固依托。
另外,作者同樣巧讀妙解了鄂蘭對藝術作品問題的詮釋,就是相較於我們吃喝拉撒的日常消費品,房屋、道路等不會輕易被耗費用掉的人為產物,構成了我們所居住的、且往往會比個人生命更加長久的共通世界(common world),唯有這個共通世界存在,政治行動才得以展開。在這些人為產物中,藝術作品跟政治具有某種同構性,因為兩者同樣為公共世界提供可以觀看的「顯象」(appearance),而藝術作品又同時是最具持久性的一種作品,能夠為轉瞬即逝的政治行動保存其偉大意義。
作者通過分析雨傘運動的參與者在「共居」佔領空間中,如何自發性地創作各種生活藝術品,從而巧妙地將一種更具持久性的共通世界,帶入了脆弱的「現身」現場。
簡言之,通過對於佔領運動中的各種生活藝術品的探討,作者達成了為「現身—共居」賦予延續性、持久性的目的,因為生活/藝術作品一方面會在運動結束後繼續持續留存,構成我們這個「世界」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這些作品的出現也已然永久地改變了,人們對於城市公共空間的想像方式。
關於雨傘運動相關紀錄片的探討中,作者有意避開了一些更為知名的作品,主要關注那些未經加工的作品,這種處理方式引起了一些讀者的疑慮,比如何明修就質疑作者為何刻意沒有提到《地厚天高》這樣更具影響力的作品。但作者的這種安排,其實與她對於「運動作為過程」的強調有關,相較於那些製作更完整統一的作品,較為粗糙的作品更忠實地記錄了運動中分散、自主、難以輕易歸類的複數個體。這些記錄的存在,也讓雨傘運動無法被簡單歸結為某個單一主題或單一符號,為後世保留了更多的可能。
對抗單一主權想像的城市自治
該書第三部分開頭的說明或許造成一定的誤導,作者表示相較前述探討運動實踐的層面,接下來要開始回到象徵層面的探討,這似乎意味著已經轉移到另一個層面,而與前面的討論並無直接關聯。不過作者實際上恰恰是要通過前面部分呈現的「過程」,也就是過程中複數個體之「現身」、「共居」實踐,來為最後部分的理論性探討奠定基礎,以免陷入象徵層面之探討常容易引發的單一化、抽象化的宏大敘事。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討論城市權與法治的頭尾兩章中,各自包含著一組對立──施密特(Carl Schmitt)的主權邏輯與鄂蘭的分權理念的對立,以及傅柯(Michel Foucault)所分析的現代國家「生命政治」(biopolitics)與鄂蘭所提倡的以法治為基礎的「政治生活」(political life)的對立。
由此可見,我們不應該孤立地理解作者對於香港政治體的理念構想,而是應該意識到這兩組對立中都包含著與中國政治形態相對抗的理論意圖。
在城市權部分,作者提出一個重要歷史脈絡,香港一直以來就是一個外來人口不斷進出流動的難民城市,其邊境始終維持著一定的開放性。在界定香港人口性質的時候,更為重要的是「居民」(residents)而非「公民」(citizens),其政治權利亦重在「居留/移動」的權利,而非固定封閉的主權。
應該說,對於香港作為難民/移民城市的描述,正與佔領運動中的「共居」經驗遙相呼應:如果說,在需要凝聚集體力量來達成目標的社會運動中,參與者們仍不免分散為各自為政的自主個體,那麼我們就不應該過度想像整體統一的人民意志;如果在香港的城市日常中,早就蘊含著與來自世界各地的移動人群共同生活的經驗,那麼我們就更不應該自我遺忘,試圖建立排他性的主權治理。
在這樣的思路下,香港對於中國的現實對抗性強度可能會有所削弱,若將多元共居的理念也延伸到中港關係中,那麼就不難理解作者為何沒有全面否定一國兩制。不過,相對於本土派強化國族認同、主權邏輯的論述,作者的觀點或許在現實對抗性上有所削弱,但反而在理念對抗性上有所增強。如此一來,作者所提倡具有多元性、多層次性的城市自治,正站在中國政府當前主權邏輯的對立面。
同樣地,在論及法治問題時,作者看似有些讓步地以香港自身法律制度的保存,作為城市自治的基礎。去年爆發的反送中運動,或許恰恰驗證了正是法律問題觸及了香港人民的政治底線。作者不乏新意地強調正是法律構成了人們從私領域進入公共空間的保障,從而得以抵抗生命政治的暴力統治,其中亦可見作者對中國政府明確的批判態度。
在全球疫情引發對生命治理、安全、人權等議題進行激烈討論的情勢下,作者以生命政治解釋中國政治形態,力圖建構以香港為模型的法治政治生活來與之對抗,這也為我們帶來了很重要的思想啟發。
結語
閱讀完這本書的讀者恐怕仍不免有所疑惑,自去年的反送中運動以來,香港的政治形勢早已今是昨非,作者如何還能夠根據六年前雨傘運動的經驗,來對當前的香港提出政治構想呢?
對此,似乎連作者本人都難免有些猶豫、躊躇。若對照前後兩場運動在有關暴力的態度、組織形式、傷亡狀況等方面的重大差異,那麼雨傘運動確實已成為遙遠的過去,當前則有著更多不得不如此的全新事態。
不過若借用鄂蘭在《過去與未來之間》(Between Past and Future)前言中,提出的一種觀點來看,在單向而必然的歷史性時間中,人藉由思考實踐的介入,能夠讓過去與未來這兩股原本水平交匯的力量產生方向偏移,進而產生作為合力的第三種力量。
思考常常不以行動為結果,因為行動的發生是無法預知的,然而思考可以在必然性選擇之外,為行動備下不同的空間。就此而言,彭麗君教授這本書藉由述說來自過去的經驗與力量,或許正為晦暗沉重、無可選擇的當下,保存了更多的可能與希望。
(本文作者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1] 值得說明的是,「共居」(cohabitation)不像「現身」(appearing)那樣直接源自鄂蘭的實際書寫,而是受到鄂蘭影響的巴特勒(Judith Butler)所提出的概念。作者在與筆者的通信中表示,她原本曾試圖在書中對兩者之間的關係進行解釋,但後來因太過複雜、離題而刪去。
[2] 作者在書中亦坦言鄂蘭並不關注身份政治,而對於這種公私領域之區分的不安也構成了貫穿該書的重要線索。作者實際上試圖藉由對運動經驗的具體研究,來凸顯「社會領域」的政治意義,進而為此難題做出理論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