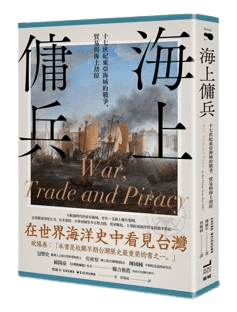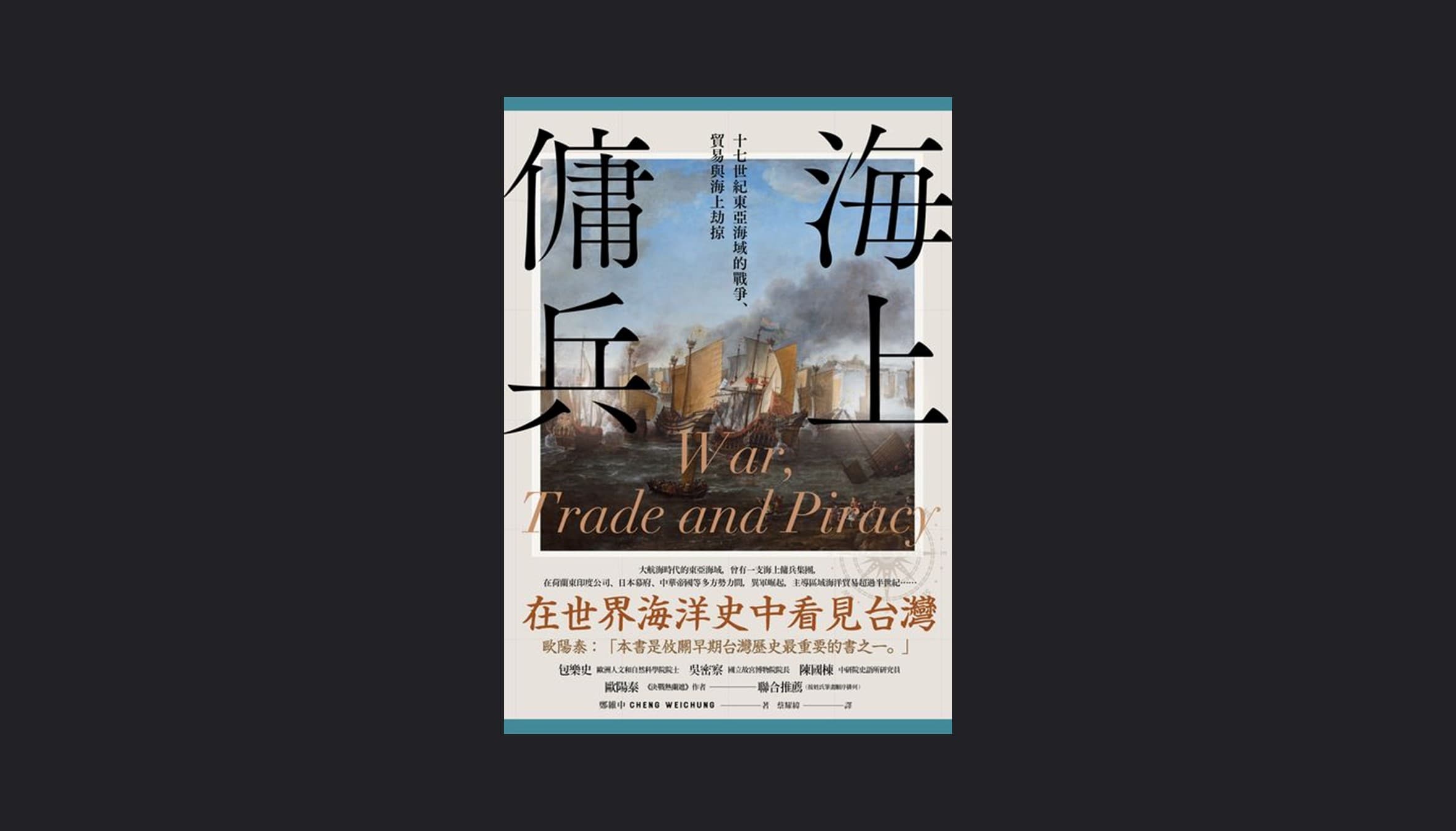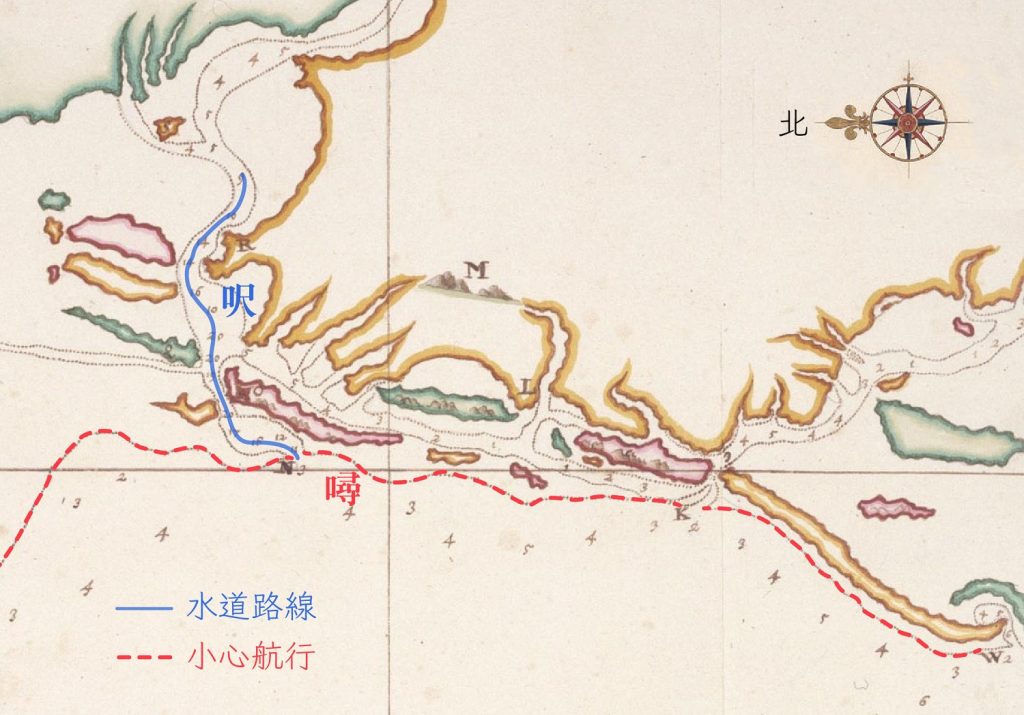鄭維中(Cheng Weichung)著,蔡耀緯譯,《海上傭兵:十七世紀東亞海域的戰爭、貿易與海上劫掠》,衛城出版,2020。
有一句引申自德國社會學者齊美爾(Georg Simmel)主張的名言是這麼說的:
愛的反面不是恨,而是無動於衷。
Der Gegensatz von Liebe ist nicht Haß, sondern Gleichgültigkeit.
相較於上一個世代臺灣人認知之中「不共戴天」的冷冽與堅決,鄭、荷兩方在歷史上的現實關係無甯較接近於「愛、恨、痴、纏」等種種複雜情緒交織,一言難盡。走過戒嚴時代「善良與誠實」者,對於北韓人民那種素樸的情感表達,會有點似曾相似的感覺。
倒是,在逐漸成熟民主社會生活的人們,應該對於這種「愛恨交加」的情緒,並不陌生。僅管我們每日都要做出若干決斷,也不得不承認任何決斷都只能基於歷史一瞬中相對的正確感覺。任何通曉「千金難買早知道」這句話真確況味的人,都早已脫離了那種信仰歷史書寫為「月旦春秋」的素樸認知。
戰後臺灣歷史書寫中,被定性為「民族英雄」的鄭成功打敗,而被「驅逐」的荷蘭長官揆一,因此被安上「竊據者」此一野蠻罪犯「夷酋」之角色。甚至,揆一的後代來台旅遊時,還得借「感謝鄭成功寬大為懷,饒赦他們祖先的小命」的姿態來表達善意,以滿足某些臺灣大眾的「感覺良好」。
然而,在我們的生命體驗裡面,真的能夠對所有一切是非,總是如秋霜烈日般洞澈明辨,而得以用非黑即白的標準判斷一切,不容一絲灰色地帶嗎?我們真的總是能毫不遲疑的做出風險極大的決定,而不擔憂留下任何一絲悔恨?在1661年4月底,鄭成功決意率兵渡海攻台,發動奇襲。這一決定翻轉了歷史局面,對臺灣乃至東亞的歷史的造成深遠的影響。
然而,就在 1661 年的 3 月底,揆一寫給巴達維亞的報告裡面,卻也清楚策劃並提出荷軍應當如何與清軍聯盟,發動奇襲的方案。他並強調必須趁此時機,將鄭氏集團的勢力一勞永逸的掃除。
揆一很清楚,鄭成功從南京敗歸之後數年,清軍已於福建沿岸完成部屬,開始壓迫鄭成功的部隊。與此同時,鄭荷雙方的談判已經觸及底線,即使暫時和平,日後仍隨時有爆發衝突的可能。最重要的是,荷蘭人早已於 1656 年,抵達北京向康熙皇帝朝貢。此後,已經正式取得大清朝廷承認,可以展開國家層面的交涉,不再如同明代一般,被拒之於門外。
鄭、清之間的殊死鬥與荷蘭無關,荷蘭與何者結盟乃是利害關係的問題。雖然清軍在海上無從與鄭氏匹敵,但也正因為如此,倘若清軍與荷蘭艦隊聯盟,一舉殲滅鄭氏集團,則有可能複製 1639 年的日本經驗,讓荷蘭東印度公司因為協助清剿有功,順勢成為代理中國對外貿易的獨家窗口。因此,1661 年在鄭氏集團尚無防備的情況下,直接派出艦隊偷襲金、廈兩島,將可使東印度公司艦隊一躍而成為東亞海域最大的勢力,根本是穩賺不賠的上算。
揆一甚至應該能在送出報告六個月前,即 1660 年 11 月派船前往廈門質疑鄭成功是和是戰時,即利用艦隊發動奇襲。當時四艘荷艦駛入廈門港落錠,即受到禮遇接待,未曾卸下任何一座艦砲。從戰艦舷側伸出的砲口,其射程涵蓋廈門市街與鄭氏在港停靠的軍船。
當時,市街上壅塞著由福建沿岸逃亡而來避難的老弱婦孺。在這鄭軍大開友誼之門,毫無還手之力的條件下,即使只有四艘荷蘭戰艦,只要開砲轟擊,直接毀掉鄭軍艦隊的可能性仍然非常之高。而當時揆一沒有發動攻擊的理由,只是因為鄭成功明確表達沒有攻擊臺灣的計畫。儘管在這一局面下,鄭軍出兵攻取臺灣本屬合理推測,且同時揆一也在盤算發動先制攻擊,他始終沒有把握住這樣的機會。
回顧類似的情況,1633 年揆一的大前輩普特曼斯長官,在推算鄭芝龍勢力擴大,可能背叛與荷蘭人先前締結之同盟後,就曾義無反顧的發動過奇襲。因此,即使揆一當時未經巴達維亞上級同意即自行發動攻擊,作法上也沒有什麼可議之處。
在揆一擬定的軍事計畫提案剛從臺灣送出後約一個月,鄭成功即率大軍登陸臺灣。揆一還來不及進行偷襲,就被鄭成功搶了先機。因為只要鄭氏獲得了清軍無法企及的海外的基地,就有機會重新與荷蘭人進行合作貿易,避免被清荷兩方夾殺的絕路。這也是鄭成功在 1662 年於安平與揆一簽訂降約時的設想。
鄭成功盤算,只要荷蘭人接受了鄭氏集團已然存續,且在海上仍優於清軍的事實,在清廷的海禁之下,最終荷蘭人還是必須繼續尋求透過鄭氏集團的走私管道,取得中國貨物。熱蘭遮城之失,主要還是揆一沒有搶先痛下殺手,選擇了相信鄭成功的善意。為何當時鄭成功與揆一會走向這樣的爾虞我詐的對峙?為何雙方的即使極端相互不信任,仍要維持表面和諧?
這一切多層次的複雜表現,都說明了鄭荷之間過去峰迴路轉、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絕對不是「民族英雄驅走野蠻罪犯」這種意識形態定性那麼簡單。就如同十七世紀世界史的變化,不能用一句「明亡清興」就帶過去一樣。
這一多面相的複雜具體事實,就是本書所要探討並試圖向讀者呈現的內涵。本書主要呈現的是鄭氏集團的發端,擴張,與消滅。
在本書當中,筆者對於 1661-1662 年荷鄭臺灣之戰的上述細節著墨不多。衝突──尤以武力衝突為最,背後必然有其結構性的因素。任何影響深遠歷史事件的發生,通常是多面向深層結構變化的一個綜合表現。
筆者所關心的,與其是戰爭衝突當中那些戲劇化的場面,還不如說是影響鄭氏集團誕生與消滅的種種長期結構性因素。在這些政治、經濟、地理、氣候等,種種層面變化的條件限制下,個人的選擇固然與其一致的性格有關,但也與人群之間的利益分歧、文化差異、名分認同、親疏遠近、愛恨情仇有關。
上述揆一未曾實現的軍事計畫與鄭成功不獲下屬認同的跨海偷襲行為,都屬於鄭荷兩方面幾代人,數十年以來亦敵亦友,相互間又愛又恨關係一個側面的表現。而這些來去分合,都是在這結構交錯、層層相因下造成的具體歷史運動所致。
本書敘事的主題「海上傭兵」,乃指向一群因應一組特殊歷史結構而存在於世的集體。在具體的事例上,這裡多指涉鄭芝龍、鄭成功、鄭經及其帶領的一群軍事人員,因海上貿易的利益而立足於東亞海域當中,大概可以與岸本美緒教授所說的「邊境軍事勢力」等同。
上述鄭荷之間在 1660-1661 年間前後這種詭蹫的對峙,之所以為參與衝突的各方默默維持,正由於敵我雙方對於涉及利益的種種結構條件變化,有相當近似的評估。同樣,雙方在發動戰爭的時機上,也因此有極為合致的判斷。就此而言,本書關注的並非個人層面上的恩怨情仇與道德秉性,而是作為群體領導者,因應變化、紆衡情勢所做出的決策、其反應與後續影響。
本書不否定個人情感好惡、品行特質、價值信念可能影響判斷與決策,但亦認為在長時段的利害關係結構演變之下,個人行動的意義只有從集體在歷史結構中的特殊存在樣貌裡,才能獲得適當詮釋。個人的主觀臆想,往往未能與種種結構衝突中變化的萬般趨向一致。這種「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情況,大體上對於一個開放社會的成熟個體而言,應該並非陌生的體驗。
是故,即便本書對於鄭芝龍、鄭成功的個人經歷時有描繪之處,主要也是探討其行動對於海上傭兵群體的意義,而不在作傳評價或描寫其性格、心理變化。若讀者細心閱讀本書,當可對鄭荷兩方為何最終會落入這種「愛恨交加」的糾結現實,能有所體會。在這種歷史認識之下,大概能避免那種如同罐頭笑聲般平面乾枯的歷史比附。祈願本書協助讀者在達到理解過去變化的瞬間,各自找到歸屬於當下的「歷史感」。
本書當中特別關注影響眾人命運的結構性因素為:地緣政治、白銀流動與海域網絡。在此焦點之外,關乎個別人物的命運、特定戰役的細節等,若非對追溯前述結構性的歷史運動有重大意義,多不細談。因此,雖然筆者已盡力比對若干歷史人物身份,但因史料限制,仍有未竟之處。如 Gamsia, Bendiok, Huanbam 等人,讀者應詳查註釋之說明(尤其譯者特別查對之處)。若干尚未完整考訂的貿易品項上,亦做同樣處理。又,本書雖指出,最終鄭經在台灣建立了一個「港市國家」,但正如同前述所說,本書著重於描寫探討「邊境軍事勢力」,並未細考其最終是否朝向建立「國家」的方向演變,或由何時起可認定為一「國家」。
所幸此一主題,早先有義大利學者白蒂(Patrica Carioti)教授,同時或後來則有香港學者錢江(J. Chiang)、美國學者杭行(Xing Hang)教授加以論述,對此有興趣的讀者可自行延伸閱讀。而 1683 年,施琅取得臺灣的一連串應對,大體上與本書所探討之一連串變化有關,讀者也可自行參閱。由於篇幅所限,本書即使涵蓋了由 1622-1683 年之時間斷限,仍僅只描述鄭氏集團興衰的梗概。總之,本書之貢獻,在於將歷史全貌因漢文史料記載不全所屏蔽的部分,還原於萬一。至於細節,難免仍有錯漏,在此仍請讀者多加警覺、諒察。
最後需在此說明,何以此書對於臺灣史研究亦有相當的貢獻。自原住民的角度觀之,大約從十七世紀起,臺灣社會即不斷被捲入全球化體系的各種網絡當中,造成了其社會文化的巨大變化。既然臺灣住民被捲入東亞海域的歷史運動當中,帶有強烈的非自願成分,而由於各種海外元素(包括移民)的加入,迅速塑造了新型態的社會相;那麼,對於促動東亞海域變化的諸種歷史動力,與那些最後或多或少因此被納入臺灣的種種元素,自不能不給予相當的關注。
用個比較跳痛的譬喻來說,近日醫療院所推動的「雲端電子病歷交換」,主要是要避免病人因跨醫院、跨科別就診領藥所造成的「藥物交互作用」問題。臺灣社會從十七世紀起,所產生一系列的變化,主要與捲入東亞海域前述的種種結構性(地緣政治、白銀流通、海域網絡等)歷史過程及其交互作用有關。
同樣,近日亦有於市場推動「食物履歷」的作法,明確標示所消費的食物來源。這些都是在追索個人自身成長與變化時,考慮到外界因素對身體內部的長期性影響,基於稽核的目的,必須達成的措施。由於十七世紀初期起,臺灣島外透過東亞海域所受到的外部影響,乃是史無前例的深廣。
而臺灣內部社會經濟的變化如出售鹿皮、種植米糖等,多與連結新市場,納入新居民等交互作用的結果有關。鄭荷兩者數十年的互動,往往也與陸續前來臺灣的唐人移民形貌,或多或少有所關連。倘若研究臺灣史的目的在於讓臺灣人獲得掌控命運的工具,如同稽核醫藥食物獲致健康一樣,那麼本書所提供,對於這些結構性力量作用歷程的詳細解析,顯然同屬不可或缺。
假想臺灣住民仍然對結構性的外界影響保持無知,或者未察覺其交互作用的後續效果,那麼儘管其對本身發展的記載能做到無限的精詳,也將無法透見出手掌握自由之鑰的打擊點。就像在藥物交互作用下,即便病人所服的每顆藥在各科診療上都正確無誤,還是可能造成傷亡一樣,臺灣史的研究者也必須適度的對一連串的歷史脈絡加以追索。因此此書雖非臺灣史的著作,對於關心臺灣史發展的讀者,也具備相當的參考價值,請讀者注意。
本文作者為荷蘭萊頓大學歷史學博士、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