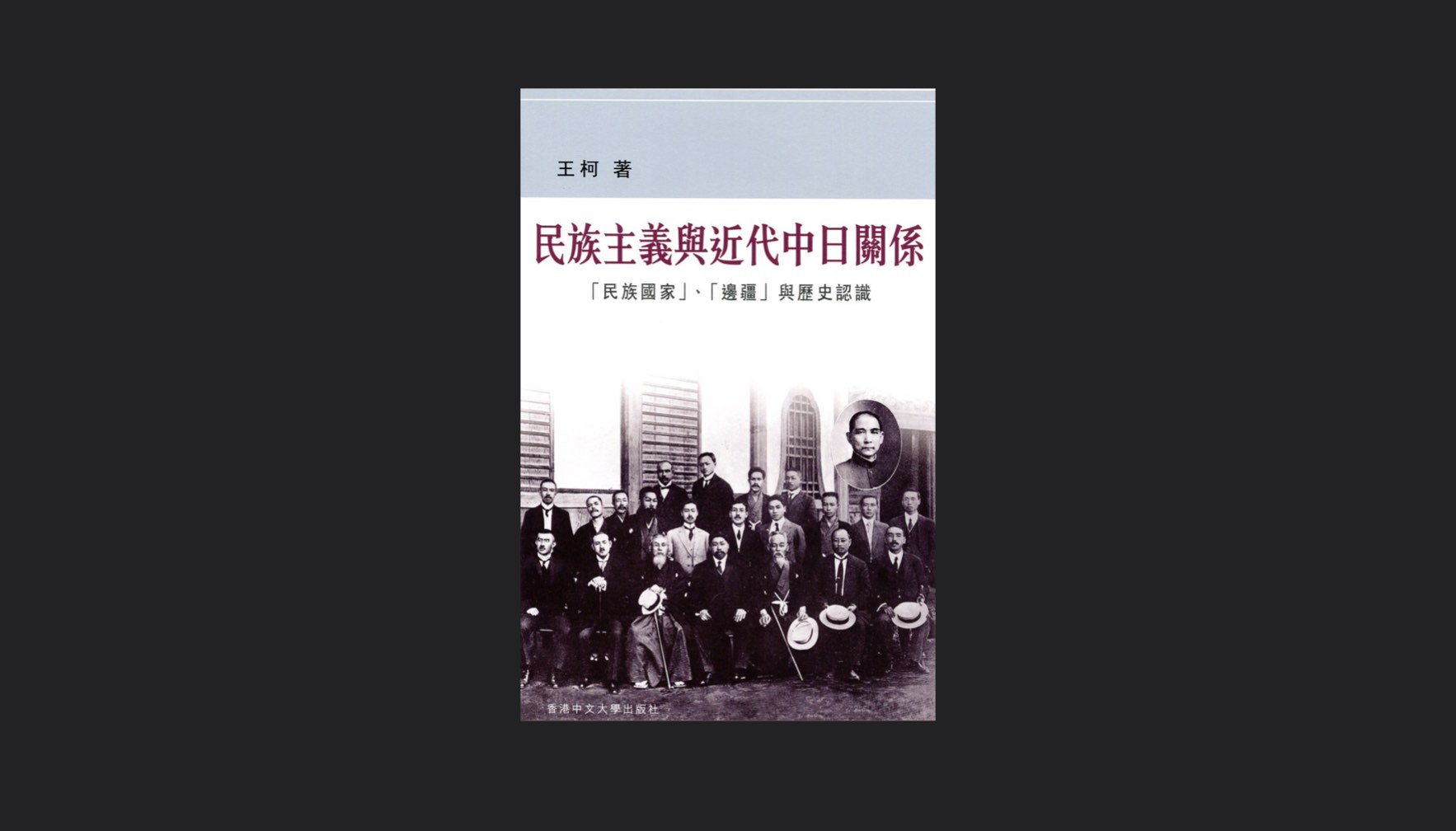一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夾在秦漢帝國與隋唐帝國之間,一段動盪不安的年代,常被形容為歷史曲線兩次高峰間的低潮,在傳統的治亂史觀之下,甚至被認為是一個黑暗的分裂時代,好像是一段只有戰亂、複雜難懂又沒有光彩的年代,因此在一般大學的歷史課上,不是完全被漠視,就是被三言兩語簡單的帶過。然而,歷史畢竟是連續不斷的,每一段歷史都是承先啟後的,換言之,要暸解全體而完整的中國歷史,無論如何是不能忽略魏晉南北朝的,何況真實的魏晉南北朝史,其實是多彩多姿的。
日本出版界經常規劃推廣學界研究成果的系列叢書,其中堪稱出版界巨擘的講談社,已數次邀請學界名家,撰寫一系列深入淺出的中國歷史全集,如一九七四年出版的《中國の歷史》全十卷,一九七七年出版的《新書東洋史》全十二卷,都廣獲各界好評。二〇〇四年至二〇〇五年間,講談社為慶祝創立一百週年,又籌畫出版了《中國の歷史》全十二卷,由專業史家執筆撰寫面向一般大眾讀者的中國史讀物,本文要導讀的即為其中第五卷,由川本芳昭教授執筆的《中華的崩潰與擴大:魏晉南北朝》,這本書可以相當程度的改變過去對魏晉南北朝史的刻板印象。
川本芳昭先生為九州大學的教授,是已故九州大學教授越智重明先生的得意門生。越智先生曾受邀來臺灣大學歷史系任客座教授,當時筆者為博士生,親受聆教,也因越智先生的介紹,認識川本先生,至今已是三十年的老朋友,現在川本先生的著作要在臺灣出譯本,筆者試為之導讀,深感與有榮焉。
川本先生的專業為東亞古代、中世的民族問題、國際交流、政治史,已出版數冊專著,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學術著作為《魏晉南北朝時代の民族問題》[1]、《東アジア古代における諸民族と國家》[2],本書作為面向日本讀者的大眾性讀物,一方面要廣納各方研究,儘量兼顧全時代各領域的歷史發展,另一方面又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呈現其自己在專業領域上的研究成果。整體而言,誠如閻步克先生在本書簡體中文版的「推薦序」中的評語:「深入淺出,文筆兼平實與活潑之致,頗具可讀性;其對魏晉南北朝史的敘述和解說,來自川本先生長期研究的個人心得,也能反映日本學界對此期歷史的許多看法」。[3]
本文做為臺灣繁體中文版的導讀,一方面希望儘量符合原著本意,以一般大眾為對象,介紹全書要旨,避免學院式的理論爭議,另一方面為讓讀者擺脫以往教育所留下的刻板印象,介紹筆者所思索的幾點「基本認識」,希望有助於讀者理解本書要旨。最後再列舉數點本書精彩論點,與讀者共享。
二
首先,關於魏晉南北朝是黑暗的分裂時代問題,這一種觀點,雖然不能完全說錯,但至少是相當偏頗的。相較於秦漢與隋唐為統一大帝國,魏晉南北朝可以視為是「分裂的時代」,問題是這種思維背後可能是受《三國演義》所述「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影響,預設有個固定領域的「天下」,進而認為中國歷史演變是依循「統一」與「分裂」而循環,而成為一種以大一統為常態的分合史觀,這種史觀只囿於形式而完全忽略歷史的實質內涵(如國家形態之差異等),進而掉入「歷史宿命論」或「歷史循環論」的錯誤之中。
至於把「分裂的時代」,進一步認定為「黑暗的時代」,則可能是受孟子「一治一亂」說法的影響,或是因這個時代常被視為是中國的中古時代,而被比擬於西洋的中古黑暗時代,事實上西洋的中古時代,早已不再被視為是黑暗時代,而孟子「一治一亂」之說,也未必妥當。不論政治體制是否維持統一的秩序,或政治權力是否一元化,都不必然決定歷史其他方面的走向。換而言之,政治上的動盪不安,不必然會導致文化上的黑暗。
譬如孟子自認所處是周道衰微(封建體制瓦解)的「一亂」時代,但當時在文化上卻也同時是中國歷史上「百家爭鳴」的古典黃金時代,同樣的,魏晉南北朝雖然在政治上確實是動亂不已,但也是中國歷史上繼春秋戰國之後,又一次在文化發展上輝煌燦爛的時代,不論是學術上玄學興起,突破僵化的經學,宗教上道教、佛教的廣泛而深入的傳播,乃至文學、史學、書法、繪畫、彫刻藝術等方面,都有畫時代的成就。
文學上,曹丕《典論・論文》一句:「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無異是文學獨立宣言,陶淵明的田園詩,更是流傳千古;史學上,陳壽《三國志》、范曄《後漢書》,已占四史中的二部,更別說還有其他更大量與更多樣性的史著;書聖王羲之的書法,畫聖顧愷之的繪畫,雲岡、龍門等佛教彫刻藝術,都是千古的成就,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本書的「前言」對此時期文化上的成就,也有清楚的說明,限於篇幅,在此無法一一詳述。[4]
其次,關於魏晉南北朝是民族大融合時代的問題。魏晉南北朝承漢帝國崩潰之後的後遺症,民族(或稱族群亦無不可)非常複雜,衝突對立非常嚴重。傳統的觀點,多從漢族本位出發,認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野蠻「五胡」(匈奴、鮮卑、羯、氐、羌),利用西晉八王之亂而起兵做亂,所謂「五胡亂華」,其後五胡諸國皆因仰慕中國文化而漢化,即「入中國則中國之」,最後融入漢族,而永嘉之亂後逃到江南的中原漢族,則帶來先進技術開發江南,教化蠻越,最終南北再統一為隋唐帝國,同時完成中華民族再一次的大融合。雖然從最後結果來說,或有見仁見智之論辯,不過其對過程的論述,顯然是過度一廂情願的。
基本上,「五胡」起兵帶來的永嘉之亂,以及隨後牽動的南北民族大移動,可視為是漢帝國對外擴張帶來的後遺症,或者說是漢帝國對四邊擴張作用力的反作用力。兩漢帝國對外的擴張,從今天的眼光看起來,可說是標準的霸權主義,但是教科書上卻美化為對外「經營」的所謂「武功」;而周邊被征服的族群,淪為「少數民族」,接受被奴隸般壓迫的命運,卻被形容為接受王道文化的教化。
就是這種歧視性的壓迫統治,導致二世紀中葉的「羌亂」,東漢帝國因而下衰,而西晉的永嘉之亂,更帶來全面性的叛離,因此舊史所謂的「五胡亂華」,實際上是被奴隸的「少數民族」的獨立運動,只是他們從塞外進入華北已數百年,長期接受漢文典籍的影響,已具有大一統的中華思想,因此他們的起兵叛離,並不是要回到塞外再過游牧生活,而是要在中原建造統治胡漢的大一統帝國。
然而,胡漢之間長期累積的矛盾與仇恨,並不是那麼容易化解的,因此這個時期的族群衝突此起彼落,如何超越胡漢之間的藩蘺,反而是有為的胡族君主的歷史課題。從後趙石勒、前秦苻堅、北魏孝文帝到北周武帝,無不致力於所謂「族群融合」的政策,但其中薀涵著許多迂迴曲折的理念演變,川本先生在本書中,對這些迂迴曲折的理念演變有精闢的分析,其精彩過程絕非舊史一句所謂「仰慕中華文化」可含糊帶過的。
話再說回來,不論胡族君主如何的「漢化」,胡族國家的主體性在「胡族」,這一點無庸置疑,因此當漢族勢力威脅到胡族統治時,其血腥鎮壓絕不手軟,如北魏太武帝屠殺漢族名門崔浩的「國史之獄」,「清河崔氏無遠近,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魏書・崔浩傳》)。
不過檢視華北的胡漢衝突,固然屢見胡族視漢人為「漢狗」的迫害事件,但不可忽略屠殺最慘烈的,反而是漢族奪權之後的報復,如漢族冉閔自後趙奪回政權後,親自帶兵屠殺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尸諸城外,悉為野犬豺狼所食」(《晉書・石季龍載記》),甚至一些高鼻多鬚的漢人也遭到誤殺,可見其屠殺之濫。另外,華北之族群衝突不限於胡漢之間,各胡族彼此之間的衝突,亦非常複雜,這些在川本先生這本書的第二、三、七、八章,都有非常精彩的深入探討。
華中、華南的族群問題,又是另一番景象。華中、華南的非漢族土著族群(包括被稱為蠻、越、俚、獠、溪等各族群),在總人口數上遠多於漢族,[5]但由於地形多山川沼澤,部落組織鬆散,缺乏集中化的政治組織,大多處於被漢族統治的命運。早在三國時代的孫吳政權,即對土著山越展開大規模的征討,掠奪其土地與人民,動輒數以千計的斬殺,大肆搜括人口,「彊者為兵,羸者補戶」(《三國志・吳書・陸遜傳》)。永嘉之亂後大舉南逃的北方漢族,在大致上是孫吳舊境的華中、華南地區建立東晉流亡政府,其領導階層被稱為僑姓士族,把持政經大權,直到南朝,南方之吳姓士族亦受其壓抑,而居於社會最底層的非漢族土著幾乎是永不得翻身。
因此,華中、華南的族群問題,最嚴重的是,漢族政權以開發之名對非漢族土著進行無止境的搜括與屠殺,其慘烈之狀,梁代沈約在《宋書・夷蠻傳》載:「(劉宋朝廷)命將出師,恣行誅討,自江漢以北,廬江以南,搜山盪谷,窮兵罄武,繫頸囚俘,蓋以數百萬計。至於孩年耋齒,執訊所遺,將卒申好殺之憤,干戈窮酸慘之用,雖云積怨,為報亦甚」,如此慘烈的屠殺,沈約寫到這裡想必也是流著眼淚的,這就是民族大融合的真相吧。本書作者川本先生,在本書第六章對此一主題有深刻的探討。
再其次,關於門閥貴族制的問題。兩漢四百年大致和平的統治,社會經濟的發展,導致了貧富差距的擴大,地方社會形成擁有大量土地的各種形態的豪族階層,又由於獨尊儒術,推行儒教國教化之後,出現大量「通經致仕」,進而「累世經學」成為「累世公卿」的知識份子官僚群,其結果是一君萬民(或說編戶齊民)的扁平社會結構,發生巨大的變化,社會產生許多具有地方勢力或深具民望的中間領導階層,這個階層可稍為細分為地方性較濃厚的豪族,以及中央官僚性較濃厚的貴族,不過有很多人物是兩者兼而有之。傳統史書對其較上層者多以門閥、門第或士族(還有甲族、膏腴等)稱之,日本學界則多以貴族稱之,其地位稍次者,則又有豪族、豪強、大姓等等用詞。
由於從東漢中後期到唐代中期,這一社會中間階層普遍存在,日本以內藤湖南為首的京都學派,以此特色把這一時期界定為中國史的中世(中古),這種歷史觀點在戰後的日本史學界有正反不同意見的激烈論戰,論戰的焦點在於這一中間階層(門閥貴族)是自立存在於地方社會,或依附皇權的寄生官僚,此一論戰直到二十世紀末才漸趨緩和。[6]本書作者川本先生的老師越智重明先生,並不屬於京都學派,不過川本先生此書也有不少參酌京都學派的觀點。蓋此論戰基本上是理性的學術對話,在論戰過程中產生大量優秀的研究成果,後繼者乃能兼採並用,另成體系,這也是本書的特色之一。
在此無意對此一學術論戰做細部介紹或評論,只想對門閥貴族常被誤解的刻板印象,稍作說明。一般對門閥貴族最常見的聯想是:他們是壟斷政治、經濟權力的特權階級,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奢華無度、壓迫無產階級的大地主,所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倡導「士庶之別,如同天隔」、「門當戶對」婚姻的階級論者等等。
以上確實是這個時代門閥貴族常見的部分負面現象,但並不是全部。在這個動亂不安的年代,有許多門閥貴族秉著知識份子的良知良能,批判腐敗的政治,或帶領民眾逃離戰火的蹂躪,散盡家財救濟生死邊緣民眾,保存經典文物致力於文化傳承,甚至探索新的文化出路等等,這些也都是不可抹滅的事實。[7]這是階級鬥爭史觀經常忽略的事實。總之,門閥貴族階層是經過長久的演變而形成的,在當時的歷史同時具有正負面的影響。
另外,與此門閥貴族制密切相關的選用官吏的制度:「九品官人法」(舊稱九品中正制並不妥當) ,也有許多被誤解的地方,經常被朗朗上口的「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即批判這一制度維護了門閥貴族的特權,不過這是這一制度運作之後被權勢扭曲的負面結果,並非制度創立之本意。
平心而論,在一個教育未普及的年代,政府要如何公正又有效的選拔人才任官,並非易事。與漢代選用官吏主要辦法的察舉秀才孝廉相比較,九品官人法算是比較進步的。蓋漢代地方州郡長官向中央推薦人才的察舉秀孝制,只憑地方州郡長官一人之薦舉,通常都是薦舉自己的學生或部屬,所謂門生故吏,其循私情形絕不會少於九品官人法,而且是更方便於權勢的干涉,如東漢末年何南尹田歆本欲推薦六名孝廉,但迫於宦官的壓力,五名被內定,他只能說「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
相對的,九品官人法在創立之初,每郡設一中正官及其助手人員,依簿世(譜牒家世)、狀(個人行狀)、輩目等標準,專責評定人才等第(鄉品),再依制度任用,比較上是較客觀的,至於在門閥貴族勢力盛行的時代,該制度被扭轉成保障門閥貴族之工具,那又是另一層面的問題。
最後再談談學術思想問題。這個時代最常被誤解的是清談玄學。兩漢經學發展到最後,失去了生命力而僵化,解經之文,極為煩瑣,「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因而有玄學的興起。玄學並不是否定經學,也不是否定儒家,而是以道家的態度與思維,重新解釋經典,當時最被重視的是《老子》、《莊子》、《易經》三部書,稱為三玄。這種學術思想的大轉變,余英時先生認為是知識份子的新自覺與新思潮,[8]而這是和當時的時代背景息息相關的。
漢末黨錮之禍,漢帝國的人才「氣節之士」,多被捕被殺,黃巾之亂、董卓亂政,經學中心被摧毀殆盡,如此變局自然會刺激知識份子,重新檢討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的儒教意識形態,而曹操主政發布「唯才是舉」的求才令,「盜嫂、受金」之徒,亦加以重用,無異是對人們數百年的精神依托給予沈重的打擊,因而重新思索人才的標準,所謂「才性問題」成為玄學清談重要的議題。
曹操謀臣荀彧的少子荀粲更倡言:「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三國志・魏書》卷十注引何劭《荀粲別傳》),因而大談性與天道之類的人生、宇宙哲理,流傳到曹魏第三任皇帝曹芳正始年間(西元二四〇~二四九年),有所謂「正始之音」的清談。司馬懿奪權政變之後,有竹林七賢抗議司馬氏的清談。
清談與玄學的關係,簡單的說,清談是玄學的表現形式,而玄學則是清談的內容,因此清談絕不是漫無邊際的空談,而必須邏輯清晰,攻防有序、言之有物、推陳出新,才能在士大夫之間博得聲譽,從何晏、王弼的「貴無論」、裴頠的「崇有論」、到郭象的「獨化論」,都對傳統的宇宙論有學術上的突破,至少比起兩漢停滯的經學有重大的學術貢獻。雖然東晉以後,玄學思想發展到了瓶頸,清談也逐漸流為名士之間的社交活動,但隨著佛學思想的傳入,學術思想也再轉往佛理的探討,而整體學術風氣的轉變,思想束縛的解放,也促進知識青年對佛學的鑽研,以及佛教在社會各階層的傳播。
清談與玄學被污名化,主要是肇因於永嘉之亂的打擊。魏末竹林七賢抗議司馬氏的清談,傳聞許多放達不守禮法的言行,在西晉清談名士或貴游子弟中,廣泛的宣揚與仿效,而西晉清談領袖人物王衍,職掌朝中大權卻無所作為,導致永嘉之亂,臨死前自責:「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晉書・王衍傳》),東晉士人也因而經常反省清談之弊,范寧甚至直指何晏、王弼:「二人之罪深於桀紂」(《晉書・范寧傳》),明末清初顧炎武在《日知錄》裡,亦直言:「劉、石亂華,本於清談之流禍」,此後「清談亡國」說幾成定論。
然而,有一次王羲之勸謝安不要清談,以為:「虛談廢務,浮文妨要」,謝安卻直接打臉:「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世說新語・言語篇》)實際上,不只打勝淝水之戰的謝安是清談高手,中興晉室的名相王導,也是重新倡導清談的靈魂人物,清談與亡國實在沒有必然的關係。[9]
三
以上是筆者所思索的幾點「基本認識」,主要是澄清一些以往對本時期的誤解,希望讀者在閱讀本書時更容易理解。以下則想摘錄幾點本書精彩的論點,與讀者共享,並略做省思。誠如川本先生在簡體中文版的自序所說,本書是對魏晉南北朝時期進行了整體的簡單描畫,特別是中國北部的胡漢問題、中國南部的蠻漢問題,以及東亞全境內的國際關係,這幾項都是作者長期鑽研的核心,而本書用淺白的文字呈現給非學院內的一般讀者。
就胡漢問題而言,川本先生補足了京都學派內藤湖南所說,這時期是外部種族的自覺反過來影響中國。五胡各族之起兵叛離,並非只是尋求獨立,而是要取代漢人成為統治包括胡漢民眾的帝王,這是胡漢問題的核心。
漢族士大夫懷著傳統的偏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倡言:「自古以來,誠無戎狄為帝王者」,胡族君主則直接反駁:「夫帝王豈有常哉,大禹出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顧惟德所授耳」(《晉書・劉元海載記》),此後胡漢關係的發展,即沿著兩極端的自我認同意識而相互轉變,從起初漢族心中對胡族有著文化優越感、鄙視感,以及在政治及軍事上遭到打壓的屈辱感與恐懼感,而胡族心中對漢族有著軍事上的優越感,卻又對漢族文化抱持著互相矛盾、衝突的自卑感與反抗心態,不過華北漢族士大夫也不全然認同東晉王朝,呈現正統性多樣化的面貌,到後來迂迴曲折而逐漸轉變到承認胡族統治,並加入胡族政權試圖改造胡族政權成為貴族制的王朝。
胡族統治者的心態與理念,也是多樣化的,劉淵、慕容廆、石勒、苻堅、拓跋燾、拓跋宏(北魏孝文帝)、宇文邕(北周武帝),都有自己獨特的認同意識,不過終極目標,都是懷抱著一種新的中華意識,要實踐成為統治包括胡漢民眾的理想中的帝王,隋唐帝國的出現,即是延續此一歷史軌跡而來的。以上胡漢雙方各種認同意識迂迴曲折的演變,正是本書最精彩的部分。
就蠻漢問題而言,川本先生特別強調這是漢民族的形成問題,當時的華中、華南遍布著各式各樣的非漢民族(蠻),其總人口數應多於從北方南下的漢族,但始終受漢族的統治。漢族王朝以國家公權力名義,對非漢民族進行大規模的討伐戰爭,非漢民族要不是被屠殺,就是被編入戶籍、成為士兵或奴隸,遠離自己的家鄉或同胞聚落,逐漸喪失自己的主體性,而被迫漢化。但由於其人數眾多,非漢民族的漢化,使得後來的漢族融合著許多非漢民族的成分,同時原來的漢族也不可避免的會有蠻化的情形,本書精彩的部分,即指出此時期南方各地到處存在著非漢民族(蠻)的元素(如畜蠱、洞),以及蠻漢交流、融合的具體事例等等。
最後,就東亞全境內的國際關係而言,川本先生指出在這五胡入華所展現的東亞動亂年代,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包括朝鮮、日本都受到影響。從五胡到北朝,胡族統治者懷抱著一種新的中華意識,要實踐成為中華世界正統的帝王,而這種中華意識也擴散到朝鮮半島與日本,使得當時的高句麗、百濟、新羅,都有某種形態的中華意識,這些中華意識都表現為皇帝尊號、天下觀、採用年號、產生中華和夷狄等概念上,其形成都是來自傳統的中國政治思想。
簡單的說,漢帝國的崩潰,意味著傳統中華世界的崩潰,然而此一崩潰卻促使受中國政治思想所影響的胡族君主懷抱著中華意識,再造中華世界,而隨著整個東亞的動盪與人民的移動,中國的政治思想更擴大影響,連帶著中華意識也傳播到朝鮮半島與日本,而從北朝的基礎發展起的隋朝,滅了南朝,以南朝為中心的世界體系崩潰了,由五胡、北朝非正統的王朝發展成了中華的正統王朝,其主導的世界秩序擴大到東亞各地,比起秦漢時期,整個中華世界更為擴大了。川本先生在本書最後的兩章(第九、第十章),對以上過程做了細膩的論述,這又是本書另一精彩的部分。
由以上可見,川本先生畢生的學術精華,都濃縮在這一本普及性的讀物,其真知灼見非常值得我們參考。做為讀者同時又職責導讀的筆者,最後想對這一時代的歷史意義,略陳己見。
從我們今天的角度來看,秦漢帝國對當時周邊各地域,雖亦有文化傳播的正面意義,但其帶有霸權主義的中華思想及天朝體系,無疑地也為周邊各地域帶來重大的災難,五胡各族未起兵前遭受中原王朝統治的悲慘命運,即為明證。
從這一觀點來說,中華的崩潰對整個東亞各地域的民族,未必是一件壞事,整個東亞政治秩序若重新洗牌,不論是三國鼎立或南北對峙,或因「勢力均衡」而持續各種形態的國際秩序,或許中國歷史上的中華思想與天朝體系,早已改觀,至少多元體系的相互制衡,可減少霸權主義的禍害。
然而隋唐帝國再起,中華世界擴大了,同時也意謂著帶有霸權主義的中華思想與天朝體系的復活與擴大,往後更進一步出現君主獨裁專制體制,其負面影響直到今日。當然,歷史不能假設,我們回顧這段歷史,胡族君主受漢籍經典蘊藏的中華思想的影響,起著關鍵性的作用,思索至此,不得不對漢籍經典蘊藏的影響力,敬畏三分。
本文作者為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1]川本芳昭,《魏晉南北朝時代の民族問題》(東京:汲古書院,一九九八年)。
[2]川本芳昭,《東アジア古代における諸民族と國家》,(東京:汲古書院,二〇一五年)。
[3]川本芳昭著,余曉潮譯,《中華的崩潰與擴大:魏晉南北朝》(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一四年)。
[4]可再參見川勝義雄,《中國の歷史・3魏晉南北朝》(東京:講談社,一九七四年),頁一~五;鄭欽仁等編著,《魏晉南北朝史》(臺北:國立空中大學,一九九八年),第一章〈導論〉,頁五~七。
[5]關於此時期華中、華南非漢族土著,總人口數遠多於漢族(華夏),參見魯西奇,〈釋「蠻」〉,收於氏著,《人群・聚落・地域社會:中古南方史地初探》(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二),頁二三~五六;羅新,〈王化與山險―中古早期南方諸蠻歷史命運之概觀〉,《歷史研究》二〇〇九:2,頁四~二〇。
[6]相關研究回顧甚多,可參考葭森健介,〈中國史における貴族制研究に關する覺書〉,《名古屋大學・東洋史研究報告7》,(一九八一年),頁六二~八三;川合安,〈六朝隋唐の「貴族政治」〉,《北大史學》39號(一九九九年11月),頁八四~九九;谷川道雄等編,《魏晉南北朝隋唐時代史の基本問題》,(東京:汲古書院,一九九七年) ,谷川道雄執筆〈總說〉,頁三~三二,此書有中譯本:《魏晉南北朝隋唐史學的基本問題》,(北京:中華書局,二〇一〇年)。
[7]參見錢穆,〈略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係〉,原刊於《新亞學報》5:2(香港,一九六三),頁二三~七七,後收入氏著《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三)》(臺北:東大圖書公司,一九七七年) ;谷川道雄著,邱添生譯,〈六朝時代的名望家支配〉,收於《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二》(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三年),頁一五四~一七六。
[8]余英時,〈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收於氏著《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一九八〇年) ,頁二〇五~三二七。
[9]關於「清談誤國」說之商榷,可再參見前引鄭欽仁等編著,《魏晉南北朝史》,第十三章〈魏晉南北朝的清談與玄學〉,頁四三三~四三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