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筆者搬家準備離開臺北的那一天,因為貨運公司久候不至,所以就去住處附近的書店「臺灣ê店」走走。自從搬到這家書店附近住之後,即經常造訪這間書店,買到了在很多書店裡買不到的書。這本絕版多年的《雙鄉記》,就是在這天,我與它在這個偶然的時刻遇到,或許也是有機緣。因此決定要寫篇文章,紀念上天這巧妙的安排。

作者楊威理根據葉盛吉的日記、遺文等資料所寫就的這本書《雙鄉記:葉盛吉傳—臺灣知識分子之青春.徬徨.探索.實踐與悲劇》,細緻地描寫了葉盛吉──一位殖民地人民內心的諸多轉折──以及作者內心的軌跡、時代的痕跡與變動。[1]
楊威理跟葉盛吉是畢生摯友,懷抱著滿腔理想與熱血,想要為戰後的中國與臺灣做出事情。兩人的道路在戰後分道揚鑣,一個去了中國,一個留在臺灣,但卻都受盡磨難。楊威理追隨謝雪紅,歷經中國的政治變動,彷彿原罪的「臺灣人」身分,讓他在中國的政治運動中被扣上各種帽子,遭受惡毒的誤會與磨難,儘管最後生存了下來,卻被迫離開故鄉數十年,並在最後離開中國,移居日本。而葉盛吉,最後則在中共駐臺人員蔡孝乾的背叛與供出名單後,殞落於馬場町,留下妻子與剛出生的兒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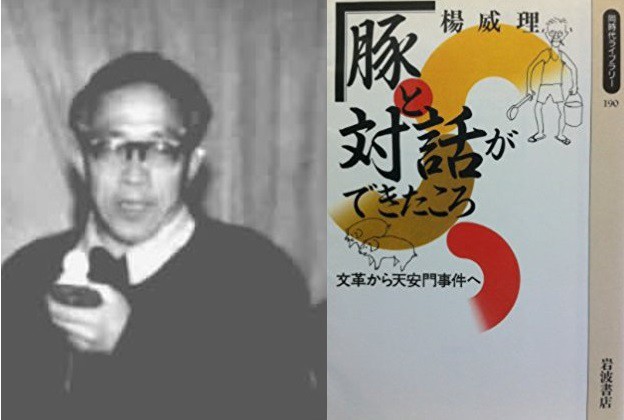
楊威理探訪葉盛吉一家消息的過程,也因為兩岸政治局勢而困難重重,但葉家人將葉盛吉的日記等全部良好地保存,在國民黨的統治下,這是一件非常困難且令人感到佩服的事情。因此楊威理寫成文章,先散刊於報紙,後來在戴國煇的建議下,將此書出版,由陳映真翻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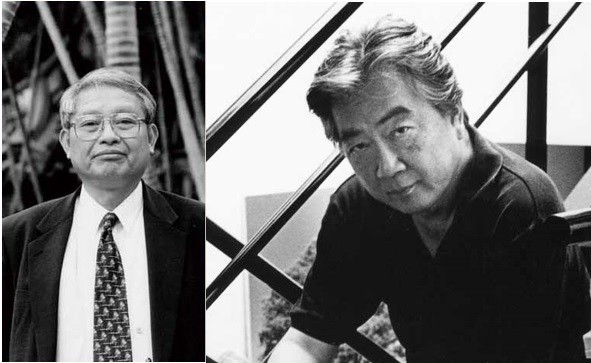
在荊子馨《成為「日本人」:殖民地臺灣與認同政治》一書中,指出當前臺獨的思想與日治時代人民反抗殖民統治的不同,在於日治時代的人們始終在民族主義中國、殖民地臺灣與帝國日本之間擺盪。臺灣人對中國的情感,始終是一種「幻想(imaginary)的共同體」的呈現,對於臺灣所要扮演的角色是中日之間的特殊媒介角色。而臺灣人對於日本,也是一種對於被認同的渴望,以及被平等待遇的要求,但日本的同化政策壓制這種要求平等的政治主張(議會請願運動),而之後與同化政策有所不同的皇民化,則是用來消弭「認同掙扎」(並進一步抹掉了其他可能性),意圖消滅尚稱寬容的同化政策下,臺灣人仍然具有的本地與中國認同,將殖民地與殖民地人民的主體性徹底扭轉,將其徹底「日本化」,讓他們認為「不當日本人是不行的」(儘管這仍未給予相應的對待)。[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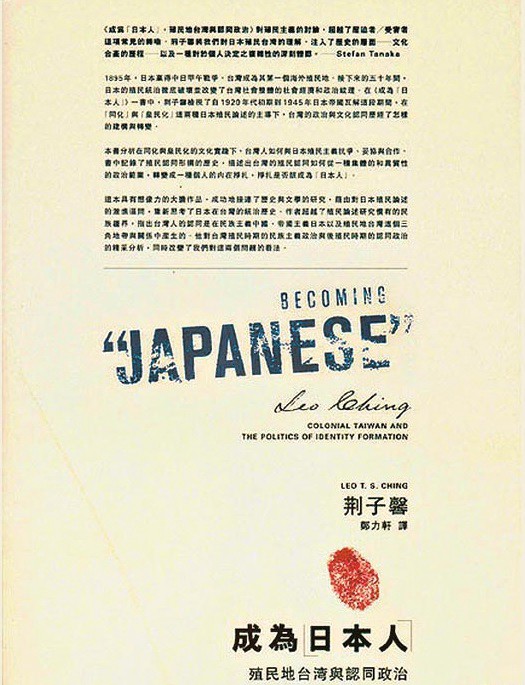
透過葉盛吉,我們得以探索殖民地臺灣許多人的心路變化。從最早開始仰慕日本的文明與現代化,到發現殖民地人民與日本人中間始終無法磨滅的差異與歧視,以及對臺灣的生活、傳統等的珍視渴望,再到透過皇民化的行為與教育,意圖「成為日本人」。我們可以看見,從同化政策期間,臺灣人在兩者之間的掙扎,而到了皇民化時期,葉盛吉的變化一直受到日本政府政策的牽扯,而他本身較為陰鬱的性格,也讓他對臺灣人身分感到壓抑。
但是這種認同的掙扎,並沒有因此結束。葉盛吉到日本受高等教育,受到更強烈的日本「皇國」思想的影響,進一步變得更像日本人。不過,他對臺灣人命運的思索並未因此中止,他的理想性格與強烈的人道主義精神,使他意圖透過改造「八紘一宇」思想,來改變東亞人民,特別是臺灣人與日本人差異命運的思考,更曾經受到改造納粹反猶太思想的日本反猶右翼主張所影響。但之後隨即因為戰爭,他們學生們去到地方上的工廠做事,遂產生巨大的轉變。因為與楊威理的相處,對於中國的好奇心與學習,對日本人的看法產生變化,以及看穿八紘一宇思想的落差,使他對於中國的認同日趨強烈,對於底層人民和上層階級之間的關係,也有著更為擴大的認識,亦是因此埋下了日後走向社會主義的種子。然而,葉盛吉此時對於日本與日本底層人民、師長的感懷,加上從小接受日式教育等等的經歷,已經使得日本成為他心中的另一個故鄉,而這也是臺灣人在主體性扭轉以後,受到日本影響所無法抹去的痕跡。
只是在日本戰敗後,對於未來他前途茫茫,遂決定回到臺灣。然而一回到臺灣,看到的卻是國民黨腐敗無能的獨裁統治、臺灣人民的困苦、二二八事件後的殘暴屠殺,使得本具有高度理想性性格的葉盛吉,漸漸開始受到社會主義與中國的吸引,而當時他所就讀的臺大醫學院,則給予了接觸這些思想的環境。[3]當時作者與葉盛吉對於國民黨的不滿,使他們倒向共產黨一方,他們認為臺灣最終會由新中國統治,國民黨將會敗北。然而,因為沒有選擇離開臺灣,在國民黨鞏固統治基礎的時間,葉盛吉最後死於國民黨的槍下。

在這個悲劇過程中,葉盛吉的性格自然影響了他自己,但是外在環境卻有更大的影響。日本政府的政策、時代的氛圍以及生活的環境,在他與諸多臺灣人身上留下了無法除去的烙痕,但這並無法使他成為日本人,民族的差異始終困擾著他。而日治時代的臺灣人,處在「民族主義中國—殖民地臺灣—帝國日本」三者之間的拉扯之下,儘管喊出「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的口號,但他們仍然在中國與日本之間作抉擇,而戰後局勢的變動,最終也使得他英年早逝。那個時代的臺灣知識份子,乃至一般的臺灣人,處在這樣的環境下,想左右突圍,如同葉盛吉般,卻發現無處可走,本來生命中無限的可能,就這樣白白消耗、殞落於其中,是時代和許多人所造成的悲劇。
日治時代的統治,在臺灣人身上已經留下無法褪去的痕跡。臺灣主體性的建立過程中,除卻思考消解國民黨帶來的壓抑,如何針對日治時代的狀況去作出反思與解殖呢?目前似乎還沒有解答。[4]由於並未對日本殖民時代進行反思,加上對中國的厭惡、對日本的不了解,而對日本產生臺日連帶的「幻想(imaginary)的共同體」,導致臺灣的過度親日與媚日情況。

另外,日治時代臺灣人對中國的「幻想(imaginary)的共同體」的模糊狀態,雖因為國民黨的殘忍而破滅,但是隨著國民黨退守臺灣帶來的「大中國」認同,以及對「中國」產生各種扭曲的認識,使得不少臺灣人又再度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有著一種「幻想(imaginary)的共同體」的感覺,歷史似乎又再度重演,這樣的現象足堪玩味與反思。[5]
荊子馨在分析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時,指出臺灣在這兩者徘徊之後,最終有著自己的路,因為臺灣雖然都具有兩者的某些特徵,但都已經不被本質化的兩者所接受,因此最終會走向自己的道路。這也是日治時代臺灣「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與戰後臺灣的臺獨思想中,最不同的道路。[6]

要走這條道路,建立臺灣「自己」的主體,正是要去除日治時代與國民黨威權統治時代的雙重幻想的影響。比起資訊流通並不發達、當年選項並不多的前人們,我們站在他們的肩膀上,已經看到了更多的歷史,過往的經驗告訴我們,上述的兩種選項都是不能走的。不管這兩種選項是以左派的社會主義口號、或是右派的文化連帶主張包裝,二者皆只是外層包裹的糖衣,唯有走自己的道路,才能擺脫「誰都不是」的孤兒這個過去。當你成為你自己,認同自己就是自己,不再需要靠著變成他人來獲得承認,有著以臺灣本土為出發的視角,並以此為行動規律的基礎時,你就不再是需要承認的「孤兒」,而是一個自足、自我認可的「成年人」。
同時,唯有當我們識破用各種他人的「民族主義」,是工具性地利用各種主張(例如社會主義、左派等),將這些主張從他人的民族主義口號中拯救出來,我們也才能在自我成長的過程中,真切地去理解這些主張,並用以完善自我、參與政治,建立起一個本土的政治秩序及政治空間,從事政治實踐,形塑出屬於自身的政治共同體。[7]當我們不再是夾縫於「統/獨」之間,而是一個獨立自尊的國家,才能夠完成更多的可能。
回顧過往,葉盛吉、楊威理與許多前人們,當年沒有想過這個選項,也確實沒有這個選項可以走。但現今的我們,或許可以不用再重蹈覆轍。儘管這條路本來不存在,但就像中國偉大的小說家魯迅所言:「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1] 楊威理的介紹,參見本網址: https://www.ptt.cc/man/MdnCNhistory/D84F/D3E2/M.1408947383.A.8F1.html 。本文的系列文後來即為《一九四六,被遺忘的臺籍青年》一書的內文。
[2] 荊子馨,《成為「日本人」:殖民地臺灣與認同政治》,臺北:麥田出版,2005,頁81-181。
[3] 藍博洲,《消失的臺灣醫界良心》,臺北:印刻,2005。
[4] 主體性的簡單說明,可以參考這一篇文章。吳豐維,〈何謂主體性?一個實踐哲學的考察〉,收於《思想》第4期,臺北:聯經,2007,頁63-78。
[5] 阿布,〈讀禁書有人開竅,有人則不,Why?〉,網址:https://goo.gl/eDchVk
[6] 荊子馨,《成為「日本人」:殖民地臺灣與認同政治》,頁 233-277。
[7] 這裡得益於這篇寫得非常棒的書評的啟發,參見林易澄,〈《重構228》的止步之處〉,上報,20170301,網址:http://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129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