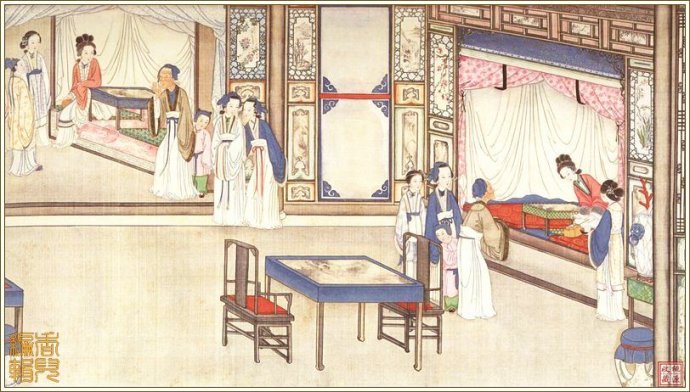在歷史的長河中溯源
縱橫歐亞
從宏觀分期來看,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個階段最重要的課題,毫無疑問是上古民族、語言的形成及分布。現代人已可利用 DNA 基因鑑定來判斷民族屬性,如針對骨骼進行分析;又或者利用科技來判斷金相成分及其來源,進一步斷定新石器時代各文化類型的交互關係。拜科學技術進展之賜,這些方面現在都有了許多便利的工具,大大有助於我們的研究。
對於上古時期,我們尤其應該著眼於民族語言文化的分布。語言分類的問題,至今仍未得到徹底解決。學術界有把握的,只是幾個主要語系,其他如臺灣南島語系範圍的問題及澳大利亞早期住民語言的問題都還沒有解決。日本語、韓國語無法歸類,歐洲高加索一些語言沒法歸類,阿爾巴尼亞、古代義大利半島伊特拉斯坎語(Etruscan language)也沒法歸類。這些都是重要的問題。
就中國而言,我想兩漢時期的阿富汗和塔里木盆地,絕對可以獨立成一個篇章,做為中外文化交流的第二個大階段。以具體問題為例,邢義田教授的研究我便很佩服。他透過殘留下來的象徵符號和形象描繪,追溯了赫克力斯(Heracules)的形象如何自西方流傳至中國,進而說明了中外文明許多要素的傳播和相互影響。將來隨著材料不斷增加,我們便可能進一步透過這些材料,來建立當時文化交流和互動的面貌。
兩漢時期的阿富汗和塔里木盆地,不僅是部派佛教以至大乘佛教滋生發育的溫床,也是中國與希臘化文明、羅馬文明交流互動的主要場所。一個具體例子是有關玻璃的問題。傳到東方的羅馬玻璃不在少數,特別在阿富汗地區,即可以發現這方面交流的例子。
透過對阿富汗地區本身及其做為媒介的研究,我們今天要理解玻璃在中外交流中的角色便容易多了。阿富汗的重要性,無論如何是應該更進一步強調的。我們可以把阿富汗視作中亞的一部分,但我覺得一般說的中亞,在古代還沒那麼重要,而阿富汗肯定是非常重要的。
隋唐時期是中外文化交流史篇章的第三個階段。這個時期,中國的西方有大食的阿拉伯世界,北邊有突厥人、回鶻人,南邊的吐蕃也很活躍。此時正值歐洲的中世紀早期(early middle ages),基督教文明發達。過去認為這是個暗淡的時期,現在看來,這種說法不怎麼準確,但當時歐洲確實沒有一個重要的強權。
拜占庭相對來說算是個強權,但地位遠不如過去的羅馬帝國。總的說來,阿拉伯世界的力量要勝過歐洲的基督教文明,這就埋下了中亞地區伊斯蘭化和中亞語言突厥化的種子。
蒙古人興起後,建立了大帝國,打通歐亞,中外文化交流進入第四階段。蒙古人促成的文化交流也為未來明末清初的地理大發現、基督宗教東來打下了基礎,那可以算是第五個重要階段。第六階段始自十八世紀末,西方完成了工業革命後再東來,當時西方的政治體制、科技文化和多科性學術都發生變化了。於是清末中國人、東方人再與西方接觸,便產生了西化的問題。在日本,這個問題以「脫亞入歐」的口號被提出來。中國人不講脫亞入歐,講的是要「現代化」,但其實現代化的本質也就是西化。
這個學期(2009)在臺大歷史系講漢學,實際也就是談比較當代的文化交流問題。我沒有泛泛地鋪敘這中間的轉變,而是拿羅振玉、王國維做為轉折時期的代表人物,深入分析他們的治學方法和思想意態,說明他們的代表意義。海外方面,我選了日本的內藤虎次郎,也選了法國、普魯士到德國、俄羅斯階段的幾位名家。
儘管有些地方仍不夠細緻,但這應該可以用來解釋說明當代文化交流的一個層面。關於中外文化交流史宏觀分期的問題,我已考慮很長一段時間了,上個學期開設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實際就是用以上所論的體系做為課程綱領。未來如果有年輕朋友願意跟我一同合作,也許這個分期架構可以更進一步、更細緻地加以發揮,並正式發表成果。
中外文化今昔
我在「我的學思歷程」演講的末了,歷史系的客座教授田浩(Hoyt Tillman)先生給我提了個問題。他問我現在看中外文化交流,中國學外國,最值得學的是什麼?外國學中國,最值得學的又是什麼?對於這個問題,我有些基本的想法。
嚴格說來,中國從先秦諸子百家開始,對客觀世界就不像西方人,如希臘人那麼重視。希臘從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時就開始注意以數學語言來描述宇宙。相對來說,從先秦開始,中國思想家重視的就是人本身。道家比較注重人的解脫,所以一直發展出養生、求仙等面向。儒家則比較重視仁、義、禮、智、信的人際關係。
子思「仁、義、禮、智、聖」的五行學說,由於簡帛〈五行篇〉的出土,受到了我們的重視。五行說到了孟子,又形成了四端的學說。儒家重視人的自身發展,到了秦以後,形成內省、修身養性、齊家治國的思想傳統。今天看起來,儒家的政治學說和倫理思想的某些部分,如三從四德,無論如何是得揚棄了,它不符合人類尊重每個人意志及個體發展的方向。
但內省的工夫仍是極為重要且珍貴的,我個人假若不是靠著中國的這些東西,我也活不到今天。像司馬遷的〈報任安書〉、王陽明的〈瘞旅文〉,這些關於人在被動的時候如何保持正常心態的思想內容,可以說是中國人對人類的重要貢獻。
我便感覺,在我看來不成問題的一些事,西方人就非得看心理醫生,給心理醫生做分析、引導不可,他們自己沒法排解。不過西方人表裡一致,無論孩子、中年人還是到了老年,他排解不開就是排解不開,排解開就沒事了。中國人表面很客氣、周到,但遇到不愉快,兩個人的關係就可能永遠緩和不來了。這是中外很不相同的地方。
西方人客觀在哪裡呢?張灝先生曾引用一位德國馬丁路德派的牧師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的話,他對人性的看法比較符合實際。他認為人心裡頭有陰暗的一面,有做惡的可能性,所以民主是必要的。民主可以提供互相箝制,提供輿論以及制度面的約束。他也主張,人心也有向善的一面,將其發揚,民主才成為可能。
簡單的說,因為人有性惡的可能,所以民主成立是必要的;人有向善的一面,所以民主有成立、落實的可能。我認為這些話比較中肯、深刻、接近實情。
我認為人應該按照柏林(Isaiah Berlin)說的,只有消極自由,不能想怎麼做便怎麼做。沙特(Jean-Paul Sartre)說他人是你的監獄,這走到極端了。但無論如何,只要活在社會上,你就不能全按自己心願生活,就得照顧到他人。如此一來,這中間就需要某種自我約束。從子思、孟子,再到宋代濂、洛、關、閩,特別是程朱一系的學說,以及陸、王,到後來以王艮等人為代表的泰州學派,裡頭有很多強調如何先從調理自己、修養自己做起,再應用到人際關係上的深刻見解。我想這絕對是東方文明、中華文明的一個重要貢獻。
西方的貢獻,就是提醒人們要注意,人的思維是可以做為一個客觀對象來進行研究的。當然,對客觀的強調,也表現在他們對自然的研究上。西方人在這方面建立了一套思維方法和研究工具,值得我們接受、吸收。按照牟宗三先生的坎陷說,過去中國的注意力沒有集中在自然科學上,所以這方面是落後的。無論接不接受他的論證,中國在這一方面確實有必要加以補強。
(本文作者為劍橋大學東亞系博士生)
- 張廣達,〈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及其影響〉,鄧小南、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11卷(唐宋時期的社會流動與社會秩序專號)(北京,2005.12):5-71。收入張廣達,《史家、史學與現代學術》(張廣達文集之三)(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9),57-133。這篇文章耙梳了日本漢學重要的流派論戰,不論是反對或贊成「唐宋變革說」,內藤的理論都影響了日本漢學的發展。
- 李丹婕,〈張廣達專訪:中國歷史的實態與表述〉,澎湃新聞。
- 李丹婕,〈張廣達專訪:沙畹與法國現代漢學〉,澎湃新聞。李丹婕女士(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是張教授的再傳弟子,也是中國中古史學界一位充滿活力的青年學者,她在澎湃新聞的專訪中,記錄了張廣達教授對於漢學的獨到見解,值得一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