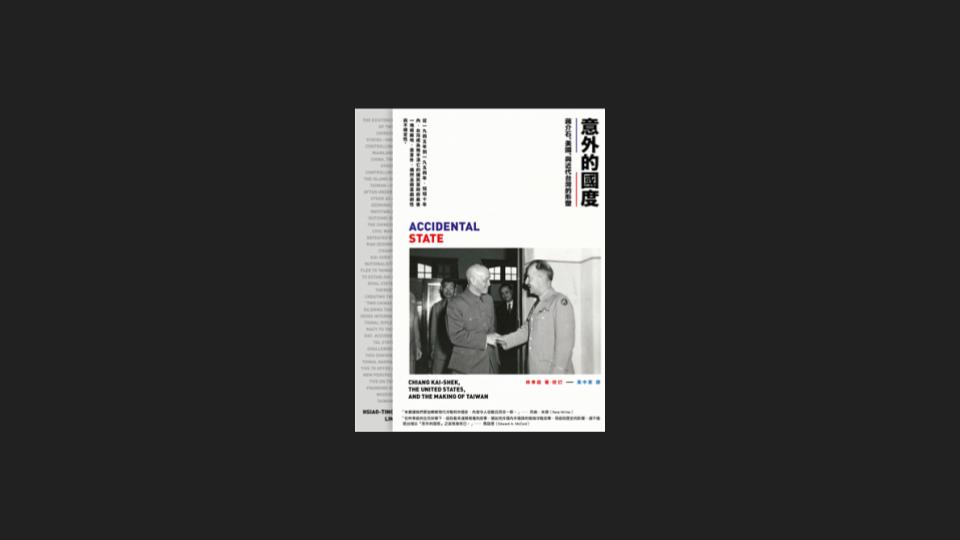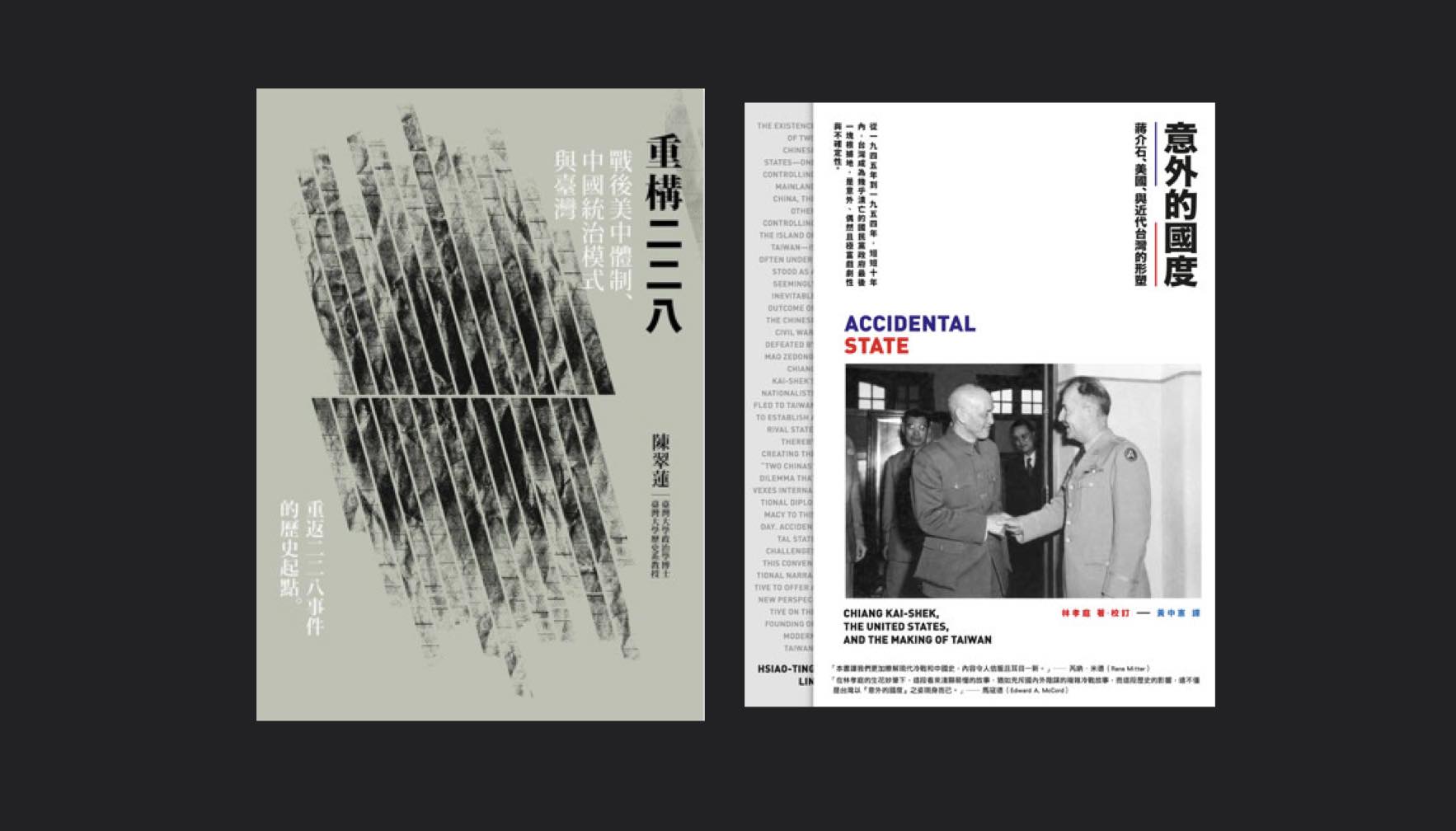蔣介石對權力有著異乎尋常的執著,據說最高紀錄是同時身兼二十七職,還有人算出他有八十餘個頭銜,可謂「官癮」超大。有人打趣稱:「當他是蔣總裁時,他還是蔣委員長;當他是蔣主席時,他還是蔣總司令;當他是蔣總統時,他就一直是蔣總統。」
然而除了這些顯赫職務外,蔣介石還曾擔任過一年半的大學校長——不是軍校,而是所學術型高校。蔣介石的形象似乎很難和知識分子、文人雅士相關聯,這個弔詭的錯位也確實產生了諸多歷史的尷尬。
教育部長「搬救兵」
1943 年,因抗戰內遷陪都重慶的國立中央大學爆發學潮,起因是換校長風波。時任校長顧孟餘同教育部長陳立夫在國民黨內分屬改組派及 CC 系(中央俱樂部組織"Central Club"的簡稱,為中國國民黨在 1930 至 1950 年代之主要派系),兩人又素來私交不睦。當校長已當得「神經衰弱」的顧孟餘素有「清高」之名,自然受不了陳立夫的窩囊氣。某次衝突後一怒之下竟掛印而去,致使校長一職出缺。

師生間隨即盛傳 CC 系將派要員前來任職,甚至還有說法稱陳立夫本人要兼任校長,由此引發學潮。師生直指陳為「黨棍」,高呼黨派應退出大學校園。
中大頭頂「中央」之名、地處天子腳下,派系林立、盤根錯節,被戲稱為「四十幾個土司的聯合衙門」,遴選校長實非易事。百般無奈之下,陳立夫只得求助於蔣介石。然而,蔣卻出了一個大大出人意料的主意。
1943 年 2 月某日,正和兒子蔣經國吃晚飯的蔣介石約見陳立夫並提出,既然全國的軍事學校都由蔣自己任校長,不如索性所有的大學校長都由他一併兼任。
興許是覺得當校長當上癮的蔣嚴重低估了此事難度,陳趕緊力勸:軍事學校重服從,容易管,文學校則大不相同。陳還提出建議:如蔣實有意,可兼任教育部長,陳自任次長。蔣略作思索後讓步:「那麽我先試一個學校好不好?」
陳「不好意思不同意他試」,只得應允,並以中央大學作為「試點」,蔣由此走馬上任。既然委員長親自出山坐鎮中大,發起學潮的師生便不好再說什麼,風波由此告一段落。
委員長親自當校長
但蔣校長顯然未把「上司」陳部長的忠告當回事,輔一上任就將軍事院校的一套帶入中大。3月4日他身著戎裝,首次赴校視事,隨扈前呼後擁,引得學校教師紛紛議論,稱蔣不似校長,倒像是個三軍統帥。首秀如此失敗,蔣此後只得著便服入校。
服飾雖然變了,蔣長年戎馬的習慣一時半會還是改不了。他提出要在學校內做軍事化管理,對學生進行更加嚴格的軍事訓練,並將全體學生依年級劃分為四個大隊。此後直到蔣離任,校園內甚至一直有憲兵駐紮。
可是,一通折騰下來卻成效不彰。1944 年 7 月蔣傳諭陳立夫,無奈表示:「該校學生軍訓毫無改進......自下學期起,似均可停辦。」
對學生如此,對教師也是。某日國文系名教授朱東潤收到通知,要求全體教師到大禮堂集合,「由校長訓話」。朱憤憤不平:「我教了二十多年的書,還沒有聽過校長對教師訓話的事。」於是未出席。當晚就聽到有學生議論:校長把大家罵苦了,說「學生不像學生,先生不像先生」。
「訓話」的習慣很顯然來自軍校,因為就在訓話時,蔣校長竟一一點名,要求教師起立「應卯」。後來大概是真把教師都當成士兵了,蔣乾脆命人將禮堂的座椅全部撤掉,要求師生站著聆訊。許多教師更是藉故推託不來了。
蔣對執教中大的哲學大師方東美十分傾佩,此時正好「近水樓臺」,拜師學習。兩人見面時一執拜師禮,一還國家元首禮,在文化界曾傳為佳話。有次方東美應召與會,見禮堂椅子全部不見,一時勃然大怒:「既是校長,豈可以不敬師?」當場拂袖而去。此後即便蔣多次慰留,方還是堅持辭去了哲學研究所所長一職。
校長勇闖女生宿舍
抗戰開始前,政府就發起「新生活運動」,提出「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中大作為軍公教系統的執牛耳者,自然無法置身事外。但許多學生對此十分不以為然,早在中大南京時期就有一段順口溜諷刺時任校長,稱他「一身豬狗熊,兩眼官勢錢,三技吹捧拍,四維禮義廉。」
但時過境遷,此番既然由委員長親自督陣,那勢必要有所不同。後來以翻譯《呼嘯山莊》聞名、1942 年進入中大的借讀生楊苡還記得,有一次學校響應「新生活」號召,在宿舍開展衛生運動。她的室友們將杯子盆子等生活用品全堆到閣樓去了,亂擺放的衣服也已收拾停當。一些女生宿舍甚至還在桌面鋪上桌布擺上花瓶,顯得十分雅緻。
事實上,戰時遷來重慶的中大是借用四川省立重慶大學的一部分臨時興建而成的,條件艱苦。宿舍多是幾百人一大間的倉庫式平房,採雙層床、上下鋪結構。有些女生宿舍則像火車臥鋪格子小間,兩邊上下鋪,中間一個拼接的長桌。總體而言,宿舍狹小擁擠,居住環境不佳。

儘管如此,蔣校長對學生儀容衛生、生活內務仍然十分關注,1944 年甚至專門發布訓令,強調若有不肖學生服裝不整還不思悔改,「應不惜忍痛開除」。他本人也不時在校內巡視——董勝今、楊苡等人都曾在校園內偶然撞見過輕車簡從、身著「黑披風」的校長。
有一次,蔣突然出現在男生宿舍樓,因天氣炎熱,恰巧正在沖涼的幾個學生見到校長,猛然愣住,忘了行禮。尷尬的校長也只能乾笑著說了一句,「你們的體質還是很不錯的嘛!」
而楊苡的宿舍之所以乾淨整潔、煥然一新,也是為了迎接校長親自「查寢」。在蔣視察過後,楊苡宿舍的「破門」上被掛上了一個花籃,作為衛生獎章。宿舍每人還可領四個小饅頭作為獎勵,一時讓不少女生十分開心。豈料鮮花還未枯萎,某個星期天校長竟然殺個「回馬槍」,再度「光臨」。這回校方並不知情,蔣只帶了一兩個隨扈就徑闖女生宿舍微服私訪來了。
沒有事先得到通知的女生們此刻要麽坐在小板凳上聊天,要麽趁著週末趕緊洗衣服、洗頭或打掃,原先為應付檢查臨時放在閣樓上的東西也全部取出來到處擺放著,場面頗為「原生態」。
校長的「從天而降」把週末正優哉游哉的女生們嚇了一大跳。蔣可能忘記了「男女之大防」,也沒預料到眼前竟是這幅亂七八糟的景象,不覺大窘,趕緊退出宿舍。此後學生們紛傳「校長大人生氣了,以後不會再來了」。楊苡的一位相識倒是快人快語,直接開罵:「活該!我們還說他隨便進女生宿舍不講文明呢!」
委員長拉肚子啦
蔣介石出任校長的當年,1939 級歷史系學生唐德剛正要畢業。按唐的說法,他們受業於蔣,當屬「天子門生」。既如此,當然應得到些「天子恩賞」的實惠。事實上,蔣介石也確實給學生們帶來了一些好處。
最直接的「德政」是學生們多了件衣服。民初時不少大學生西裝革履、儀表堂堂,但戰事一起,經濟蕭條,國家動盪,能穿暖已是奢望。中大許多學生又來自淪陷區,千里跋涉來到重慶,衣著可謂「頂天立地、空前絕後」:下雨沒傘、腳下無鞋,膝蓋和臀部都磨破,情況十分悲慘。
蔣見此狀,命軍政部長何應欽給每位學生發了一套棉軍裝。重慶地處嘉陵江畔,冬日苦寒——儘管有校友回憶,棉服「次年天熱後就上繳了」,但畢竟解了燃眉之急。有人總結棉衣的作用:「不但保暖過冬,還兼有早上大食堂中搶粥的防禦衣的作用」。此話倒不全是調侃,因為若不「搶」粥就很可能要捱餓了。
民以食為天,戰時却條件艱苦,雖然政府給學生提供「貸金」——相當於不用還的學生貸款,但貸金食物數量十分有限。後來在臺灣官至央行總裁的1939級學生謝森中就認為,青壯的男生得吃三四碗飯才可吃飽,女生「斯文」,吃不飽就成了常態。這一點得到了他1944級學妹、後來的作家聶華苓生動的確認:
「早上,每個女孩子拿著碗筷去食堂搶稀飯。所謂搶,就是滿滿一碗稀飯稀里呼嚕喝完了,趕緊又去大木桶裡再滿滿舀一碗,去遲一步就完了。有人不甘心,用鐵飯勺在木桶底上刮呀刮的,刮了小半碗。」
因早上搶稀飯時戰況慘烈,常有米湯濺到身上,不少學生不捨得穿校長給的「防禦衣」,乾脆換上髒衣服去食堂,稱之為「戰袍」。有惡作劇者甚至顧不得體面,直接把口水吐到菜上,讓別人搶無可搶,好自己獨吞。
除數量嚴重不足外,品質亦不甚佳。飯中常摻有沙子、稗子、細石子、煤屑,甚至老鼠糞等,被戲稱為「八寶飯」。長此以往,學生不堪忍受,群情激憤。鑑於此情,中大當局趕緊上報蔣校長,稱學生以伙食為由頭打算發起「倒孔(祥熙)」學潮1。
1943 年 11 月某日,蔣校長遂親臨學生食堂,和學生一起體驗「八寶飯」。他一連吃了三大碗米飯和一盤青菜蘿蔔。吃完後,蔣也忍不住吐槽,「米質太差,要改善。肉也太少,貸金要加。」
在楊苡的回憶中,蔣校長到食堂吃飯還有個滑稽的插曲。她時當正吃完飯從食堂出來,就看見穿著中山裝的蔣介石趕緊鑽進食堂附近用破磚頭和籬笆圍起來的男廁所。有幾個看熱鬧不嫌事大的男生笑得前仰後合,大聲嚷道,「委員長吃我們的伙食拉肚子啦!」
不過,蔣介石此番「體驗民間疾苦」不止作秀,倒真是給學生們帶來了福利。他要求糧食部給予中大特殊照顧,供應中大的米為此改善了一段時間。此外,學校還設立了輔食部,「酌售面菜食物」供學生「打牙祭」,提供魚香肉絲、回鍋肉片、麻婆豆腐等等。至此,一場醞釀中的學潮才被壓制下去。
尷尬人偏逢尷尬事
可惜蔣介石的種種「德政」並未令大部分學生感恩戴德。1944 年 7 月,蔣親臨畢業典禮,校長終於要為「天子門生」們親授畢業證書了。教育長朱經農拿著畢業生名單喊學生上來接受校長授書,誰知竟全場寂然。一會兒才有學生表示,此人未到,他可代領——無奈之下只得如此。
誰知朱接下去點到的幾位學生竟都未到場,只得由他人代取。如此幾番後,蔣校長也失去了興致。估計是早已備好了的一番訓誡竟無處施展,實在沮喪。事實上,當天出席人員不及應到畢業生總數的一半,學生如此不給面子,校長盛怒之下只得悻悻離開。
也許蔣本是好意,但綜觀他為政中大期間的所為,在在令人感到錯位和不合時宜。借用《紅樓夢》中的一個回目,可稱「尷尬人偏逢尷尬事」。最為關鍵的是,作為一所「文學校」,蔣的到來,並沒有為中大學術水平的提高達到任何正面的效果——畢竟教師動不動得去聆訊,如何安心教書育人?
可能蔣自己也深感挫敗,畢業典禮後一個月,他就金盆洗手,結束了僅僅持續一年半的中大校長生涯,改任「永久名譽校長」,校長一職則由後來的中共領袖——江澤民的老師顧毓琇出任。此後,蔣介石再未出任任何一所「文學校」的校長。
曾在中大任教並擔任過蔣的侍從的古典文學專家劉持生,1949 年選擇了留在中國大陸。多年以後,文革如火如荼,極少談論政治的他卻一反常態,對家人說道:「蔣先生嘛,不如他自己說得那麼好,也不像宣傳說得那麼糟」。
- 人民網,《蔣介石兼職癖:最高紀錄同時兼任27個職務》
- 黃克武,《顧孟餘的政治生涯:從挺汪,擁蔣到支持第三勢力》,載《國史館館刊》,2015 (46):103-105+ 107-168
- 陳立夫,《成敗之鑑——陳立夫回憶錄》,臺北:正中書局,1994:頁307-308
- 東南大學校友總會,《蔣介石曾當過中央大學的校長》
- 周斌,《蔣介石就任中央大學校長往事》,國家人文歷史網站
- 季為群,《蔣介石在中央大學軼事》,載《江蘇地方志》,2001(05):57-58
- 高澎主編,《永恆的魅力——校友回憶文集》,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2002:頁185-213
- 張守濤,《焦土紅花:抗戰時期的國立中央大學》,載《同舟共進》,2017 (1):66-70
- 董勝今,《我迎面碰見蔣委員長》,看中國網
- 宋路霞,《唐德剛先生二三事》,愛思想網
- 楊苡 口述,余斌 撰寫,《一百年,許多人,許多事》,南京:譯林出版社,2023,參見第四章,「從聯大到中大(下)」
- 倪蛟,《抗戰時期國立中央大學的學生生活》,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7,參見第五章,「戰時中央大學學生的經濟狀況」
- 華苓,《三生影像》,北京:三聯書店,2012:頁118
- 王覺非,《逝者如斯》,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頁145
- 馬識途,《百歲識憶》,北京:三聯書店,2014:頁41-42
- 朱東潤,《朱東潤自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參見第十一章,「中央大學前四年(1942-1946)」
- 蔣寶麟,《民國時期中央大學的學術與政治》,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參見第五章,「國家與大學政治文化:抗戰時期中央大學的「易長」問題」
- 張守濤,《先生歸來:南京民國老大學的那些人和事兒》,南京: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2015,參見第五部分,「蔣介石:親任中央大學校長」
- 張建中主編,重慶市沙坪壩區地方志辦公室編著,《重慶沙磁文化區創建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頁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