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的隨從:伴隨戰爭而來的鼠疫
1910 年10 月,在東北地區爆發了一種神祕的鼠疫,它極不尋常的傳染力引發了嚴重的恐慌。隨著眾多擔任苦力的華工搭乘火車返鄉過年,這個疫病以史無前例的速度迅速傳播。此疫源起於中俄邊界的滿洲里市,在兩個月內就傳到了3,000 公里外的奉天,進而威脅北京以及中原腹地。工業發展帶來始料未及的惡果,三大鐵路樞紐──哈爾濱、長春與瀋陽(當時稱為奉天)──登時淪為疫情擴散的三大中心。
這場東北鼠疫不僅影響中國人民的生命財產,更直接威脅清廷本已岌岌可危的主權。清廷原本沒有認真看待這場疫情,直到西方外交使節團對於疫病進逼北京深感驚恐,開始對中央政府施壓之後,情況才有所改變。後來清廷之所以採取超乎尋常的行動,就是因為擔心日本與俄國會利用遏制疫情為藉口,趁機在東北地區擴張影響力。
使疫情迅速流竄的鐵路網是東亞三大帝國在世紀之交兩場歷史大戰的結果。1895 年甲午戰敗後,清廷企圖聯合俄國以阻擋日本擴張,所以簽下中俄密約,允許俄國建立與西伯利亞鐵路連結而橫跨東北地區的東清鐵路,並有縱貫東北的支線由哈爾濱向南延伸至旅順。但疫情發生的五年前,日俄戰爭(1904-5)爆發,又使得日本由俄國手中取得東清鐵路支線中由長春至旅順的路段,並改名為南滿鐵路。由於東北鐵路系統由三個在地緣政治上激烈衝突的三大帝國分別掌控,學者薩默斯(William Summers)指出:「(無論是基於)鐵路在行政管理上的複雜度、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乃至在運送鼠疫感染者上所扮演的關鍵角色,東北鐵路都無可避免地同時成為控制疫情的樞紐與各方爭議的焦點」。反過來說,僅僅 15 年之前,當這些鐵路都還不存在時,疫情絕不可能如此迅速在東北傳播,更不會造成清廷的主權危機。
如同學者內森(Carl Nathan)所言,化解這項主權危機的唯一方法,就是由中國自行設置一個抗疫機構,以至於「在醫療實務上盡可能地『西化』」的同時,中國仍得以極大化對於該機關的主控權」。這並不是清廷首次為了維護主權而被迫採行西方公衛措施。為了重新行使對天津的主權,清廷必須讓列強相信它決意延續外國人在義和拳亂之後建立的衛生機構,是以於 1902 年在天津設立中國第一個市衛生局。也許就是惦記著這項令人不安的前例,外務部右丞施肇基(1877—1958)緊急請求他的老友伍連德趕往東北。
伍連德與兩種鼠疫

在伍連德自傳《鼠疫鬥士》(The Plague Fighter)全書開場的第一段裡,這位年輕的醫師回想自己在一個寒風刺骨的聖誕夜抵達哈爾濱的情景。作者甚至還沒向讀者介紹自己,便迅速把鏡頭聚焦於到自己的手上,提著「一具小巧的中型英國製貝克顯微鏡,附有細菌學研究所需的一切配件」。伍連德以這個鏡頭為第一章〈黑死病〉拉開序幕,巧妙暗示了這些器具的關鍵角色。但是接下來的三天裡,伍連德完全沒有機會使用顯微鏡,直到他在極祕密的情況下解剖一具染疫身亡的日本女性屍體,立刻發現了一些微生物。這些微生物看起來就像是與日本科學家北里柴三郎(1853—1931)和法國科學家耶爾辛(Alexandre Yersin;1963—1943)在 1894 年香港鼠疫時共同發現的鼠疫桿菌。透過顯微鏡,伍連德又進一步觀察到一種新奇的現象,這些桿菌只存在於病患的肺裡,由此可見,滿洲鼠疫與香港鼠疫極為不同。
根據伍連德當時的推想,滿洲鼠疫是空氣傳播的肺鼠疫(Pneumonic Plague),鼠疫桿菌透過人與人的接觸而直接傳播,而不是像香港的腺鼠疫(Bubonic Plague)基本上只透過鼠蚤傳播。在北里和耶爾辛辨識出鼠疫桿菌的四年後,(不過後來證實耶爾辛所發現的才是真正的鼠疫桿菌,因此該菌在 1954 年正名為耶爾辛菌),法國科學家席蒙(Paul-Louis Simond)進一步發現鼠疫是透過鼠蚤傳播。鼠疫在香港爆發後傳至印度與世界各地,成為人類史上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十多年來奪走超過千萬人的生命,是以科學家們對腺鼠疫持續進行深入的研究。相較之下,肺鼠疫只被當成腺鼠疫的一種衍生現象而已。腺鼠疫流行時,在少數患者身上會表現為肺鼠疫,沒有淋巴腺腫大的現象。有時甚至會出現人傳人的原生型肺鼠疫(Primary Pneumonic Plague),但是規模往往非常小,也極為罕見,所以不受學者重視。在此要強調,不論是把肺鼠疫和腺鼠疫區分開來,或是描述肺鼠疫的臨床特徵,伍連德都不是第一人。不過,肺鼠疫幾百年來極為罕見,疫情爆發的範圍也非常有限;正是滿洲鼠疫才使國際科學界首度開始關注這種罕為人知的鼠疫類型。
伍連德立刻向哈爾濱與北京的官員通報了他的發現。他邀請地方官與警察長官前來,引導他們透過顯微鏡觀察,以確認這場疫病的真正肇因。在他們一致表現出懷疑的態度後,伍連德斷論:「要說服缺乏現代知識與科學基礎的人,常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過,這不是中國人特有的問題;接受過現代訓練的外國醫生,也得等到親嚐苦果後,才會承認這場疫病是肺鼠疫。他們深信自己擁有關於鼠疫的最先進知識,是以拒絕相信肺鼠疫竟會自成一種獨立的疫病且大規模爆發。
世界上首次出現「防疫口罩」
若想知道外國醫生如何堅決抗拒這個新知識,最好的線索就是防疫口罩所引起的爭議。伍連德以不久前才發明的外科口罩為基礎,設計了以紗布製成的防疫口罩,要求衛生人員與大眾正確佩戴,以避免呼吸道感染。就如醫療人類學家林泰里斯(Christo Lynteris) 所指出的,這是近代世界醫學史上首次發明的防疫口罩。
伍連德的防疫口罩反轉了外科口罩的邏輯。外科口罩是 19 世紀末細菌學革命的產物,主要的功能是防止醫護人員將病菌傳播到手術開啟的傷口上,用意不在於保護戴口罩的人,而在保護患者。伍連德的設計源自外科口罩,但目的卻是保護戴口罩的醫護人員,使他們不受到鼠疫患者傳染,所以是一種全新的用途。然而,基於腺鼠疫的科學知識,許多外國醫生(包括來自日本、俄國與法國的人員)不相信伍連德的判斷而拒絕佩戴口罩,即便是與重症病患近距離接觸時也不例外。

/public doman)
伍連德的回憶錄中特別提起一個故事,主角是抗疫團隊的資深同事法國醫生梅斯尼(Gérald Mesny),北洋醫學堂的首席教授。在梅斯尼強烈批評了伍連德對於肺鼠疫的判斷後,伍連德憤而向清廷提出辭呈。幾天後消息傳來,指稱梅斯尼造訪俄國醫院的時候沒戴口罩,因而感染了鼠疫。六天後,這位抗疫團隊的領導人不治辭世,眾人頓時認識到這個疫病傳染力之可怖,於是「街道上幾乎所有人都戴上了某種形式的口罩」。梅斯尼去世之後,又有數位與伍連德意見相左的人士先後染疫喪生,彷彿像是疫病直接幫伍醫師掃除他所遭逢的阻力。
與東北當地的官員不同,北京的官員(尤其是伍連德在外務部的老友)不需要顯微鏡就相信此疫是肺鼠疫。梅斯尼的悲劇後,他們積極支持伍連德據此判斷設定抗疫計畫,化解主權危機。在拍發給施肇基的電報裡,伍連德總結抗疫原則為:「這種疾病幾乎完全由人傳人而傳播,老鼠傳染的問題可以暫時存而不論。壓制疫情的一切措施都應當聚焦於人的移動與習慣。」雖然只是一名年輕而且缺乏經驗的醫生,伍連德卻建議擱置近十五年來針對鼠蚤傳播所創設的一切防疫措施,實在是非常大膽的主張。伍氏發出電報的幾個星期後,日本人經營的《盛京時報》還刊登了一篇名為〈論防疫行政宜極注意捕鼠〉的社論,指出臺灣也曾經深受鼠疫猖獗之苦,在臺灣總督府力行滅鼠後,鼠疫在臺灣幾乎已然絕跡。為了在大連複製這樣的成果,日本投注極大心力於滅鼠,到 2 月底就已經捕捉了超過兩萬隻的大鼠與小鼠。
但是後來情況很清楚,絕大多數鼠疫病患都是感染肺鼠疫,而且被解剖的老鼠身上都沒有發現鼠疫桿菌。即便如此,國際推崇的鼠疫權威北里柴三郎博士在 2 月底造訪奉天之時,仍然堅稱當務之急是滅鼠。他指出,等天氣變暖,老鼠從冬眠中甦醒並接觸病患後,就會產生新一波的疫情,將會使腺鼠疫與肺鼠疫聯手肆虐中國全境。另一方面,看到大連許多日本人戴著口罩,他斥之為「沒有必要,而且小題大作」。當北里向日本領事館全體人員發表演說時,更強調肺鼠疫其實比較容易控管,不至於傳播至海外,更值得擔心的問題是肺鼠疫有可能在不久之後轉變為腺鼠疫,而腺鼠疫卻可以經由船上的老鼠而散播至世界各地。簡言之,這場鼠疫的本質以及可能出現的轉變(這點在當時正是爭議焦點)會直接影響清廷當如何維護東北地區的主權。
4,000 年未經見之極殘忍政策
由於當時西醫也無法治癒肺鼠疫病患,伍連德的抗疫措施的核心是防止鼠疫擴散:辨識出鼠疫病例、把病患與疑似病患區分開來、設置隔離鼠疫接觸者的設施,並且教導大眾正確佩戴紗布口罩。為了「監管病患」,伍連德招募了 600 名警察接受抗疫訓練,取代先前沒有受過訓練的警察人員。鑒於鼠疫沿著鐵路往南傳播,伍連德建議嚴格控制西伯利亞邊界的滿洲里與哈爾濱之間的一切鐵路交通。更有甚者,清廷以軍隊控制火車交通,也阻止徒步旅行者穿越長城入關。
一旦抗疫措施聚焦於控制帶菌病患的移動,顯微鏡就變成一個不可或缺的工具,因為顯微鏡為鼠疫病患的診斷提供了最終的判準。首先,在檢診隊逐戶搜尋鼠疫病患時,「逐日報告必以醫官診斷書為憑,醫官之出診斷書,務以鏡驗成績為據。一病名之是否,必經數醫之手,多次之檢查,確有百斯脫菌之發現,而後敢決定。」逐日報告表中列有專門欄位,以供填寫檢驗結果以及檢驗日期。鼠疫個案的診斷由「百斯脫菌」(鼠疫桿菌)決定,因此與顯微鏡以及病菌理論密不可分。儘管如此,很難想像當時的診斷程序都確實使用了顯微鏡,因為不管是儀器還是受過訓練的人員,其數量都遠不足以進行如此全面性的檢驗。更何況就成本效益而言,顯微鏡檢驗絕不是診斷鼠疫病患的最佳方式。
滿洲鼠疫期間,確診的鼠疫病患被送進一家鼠疫醫院,而病患接觸者則被送往由俄國鐵路當局出借的 120 部鐵路貨車所改裝而成的緊急隔離營。病患接觸者每天早晚都必須量測脈搏與體溫,只要有人出現發燒症狀,就立刻隔離於獨立的車廂裡。如果細菌檢驗發現某人感染了鼠疫,那人立刻就會被轉送到鼠疫醫院,而且入院後幾天內就會死亡。由於鼠疫醫院裡的病患死亡率近乎百分之百,因此顯微鏡診斷個人染病狀態的功能,就等於賦予這種儀器判斷生死的權力。
清廷以顯微鏡作為抗疫措施的基礎,從而賦予顯微鏡莫大的權力;另一方面,顯微鏡也反向賦予抗疫措施高度的正當性──即便連錫良都承認那些措施是「4,000 年未經見之極殘忍政策」。至於抗疫措施為何會被視為殘忍的暴政,這一點並不難理解。史學家班凱樂(Carol Benedict)指出,在許多面向上,傳統中國因應瘟疫的做法與歐洲早年因應黑死病的做法十分類似:兩者都向神靈求助,都以為疫情源於大環境的因素,並且都努力避免接觸有毒的空氣。不過,「(歐洲)政府以隔離檢疫(quarantine)直接介入民眾的生活,而中國卻沒有施行強制性的公衛措施。」換句話說,中國與西方因應疫病的不同之處,就正是伍連德建議的那種策略:嚴格控制人民的移動與習慣。

無論是在香港鼠疫或是滿洲鼠疫期間,當局施行的抗疫措施都遭到華人強烈的抗拒。英國公衛當局在香港逐戶搜尋病患,並且將病患送上醫療船「海之家」(Hygeia)隔離時,當地的華人在憤怒與恐懼交相影響下數度暴動。當時的情勢極為緊繃,以致當外籍醫師前往東華醫院附近那個群情激憤的區域時,甚至覺得有必要隨身攜帶左輪槍。此外,為了逃避那些可怖的抗疫措施,大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港人離開香港湧入廣州,儘管疫情在廣州也同樣猖獗。由此看來,港人對於抗疫措施的恐懼,竟然比對鼠疫疫情的恐懼還要強烈。
相較於港府在香港鼠疫中的作法,伍連德在東北的抗疫措施更為嚴格也更具侵入性。哈爾濱城外駐紮了將近 1,200 名士兵,城內又有六百名警察值勤,所有市民皆不得進出自己被劃入的區域,更遑論進出城市。在控管活人移動以外,更棘手的問題是處理地面上堆積如山的死屍。由於攝氏零下 30 度的酷寒將土壤凍為堅冰,延伸超過一公里的 2,000 多具屍體無法安葬。深知中國人對祖先的崇敬,伍連德焦慮地等待皇帝特准大規模地火葬屍體的詔令。疫情平息後,他經常把皇帝核准火葬的詔令譽為西醫在華史的里程碑。
對於當時在東北的大多數華人而言,他們既不知道鼠疫桿菌,也不關心國家主權,他們只是驚恐於一個明顯的事實:所有被強制送入隔離醫院的病患,沒有一個人活著回來。在他們的眼中,伍連德憑著醫學而指示的警察行動和衛生措施顯得專斷、暴虐、又深具破壞性。為了對抗鼠疫,伍連德運用警力限制人民的行動、干預他們的日常生活、焚毀他們的住宅與財物、還帶走他們的親屬──卻沒有救回任何一名鼠疫患者的性命。許多鼠疫患者在半夜自行爬出屋外,橫屍街頭,只是為了避免連累家人遭到警察的侵擾。此外,疫情中謠言四起,有人説疫情源於日本人在井裡下毒;也有人説病患遭到當局活埋;更多的是宣稱傳統中醫成功治癒了某些鼠疫病患。防疫事務總處的權威與正當性遭到來自四面八方的挑戰。
由於伍連德與他的同事無法以療效即時贏得人民的信任,所以那些看似殘酷的抗疫措施如果有任何正當性的話,就是因為沒有任何更有效的辦法。由防疫人員的角度看來,既然確診鼠疫的病患必死無疑,那麼在抗疫上唯一可行的選項就是把染病的人和健康的人隔離開來,並且把前者送進鼠疫醫院去等待他們必然的最終命運。這些措施確實無法治癒任何一名病患,但治療本來就不是他們的目標。藉著把確診的肺鼠疫病患和一般大眾區隔開來,伍連德與他的同事便可阻止疫病進一步散播,從而拯救許多人的性命。雖然無人確知到底是什麼因素遏制了這場疫病,但施行抗疫措施之後才短短三十天,哈爾濱的每月染疫死亡人數就從 3,413 人遽減為零。由此看來,儘管無法治癒任何一名染疫的病患,這些嚴厲措施極可能是當時抗疫的最佳選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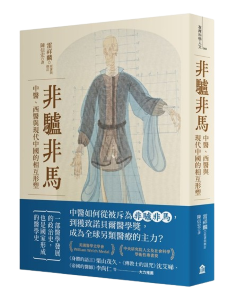
成為全球另類醫療的主力?◉
◉一部醫學發展的政治史,也是國家形成的醫學史◉
◉美國醫學史學會William Welch Medal◉
◉中央研究院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
國父孫中山先生臨終之時,是否接受中醫的治療,曾引起全國輿論的關注與爭議。當魯迅聽說孫拒服中藥後,激動不已地說:「他的決定不下於他一生革命事業地感動過我。」他認定身為現代性象徵的孫中山,認定身為現代性象徵的孫中山,絕對不應該服用中藥,因為中藥是現代性的死敵。半世紀後,當《紐約時報》記者伴隨尼克森總統訪問中國,在同一個醫院裡親身經歷針灸療效後,他所寫的報導卻引發了全球性的「針灸熱」,讓世人以為中國發展出了獨特的現代性。
中醫的華麗轉身是如何發生的呢?
其實在孫中山先生過世後的三年,西醫和中醫就經歷了一場重大的歷史鬥爭,中醫幾乎要被消滅。弔詭的是,西醫非但沒有成功把中醫打入歷史灰燼裡,還激發中醫界團結起來,追求「科學化」。過去,史學界並不認真看待中醫的「科學化」,要不是以為科學化後的中醫,不再是真中醫,要不就以爲一切都是政治力的干預,結果錯失這一段充滿創意和活力的歷史過程。
本書作者以突破性的研究架構,超越原本「西醫在華史」和「中醫現代史」的二元對立,描繪中醫、西醫和國家交鋒的歷史現場。中醫如何在被譏笑為「非驢非馬」「雜種醫」的噓聲中,仍堅苦卓絕地在知識論上、體制上、物質(指本草)上,既改造自我又維持自我,而後與西醫競奪,參與打造國家的過程。這是一部醫學發展的政治史,同時也是國家形成的醫學史。
作者考掘出巨量的史料,鳥瞰全局,編織出一幅跨國、跨地域、跨政權的東亞歷史圖像。從延燒輿論界的知識分子論戰,到本草物種的正名;從東三省到四川重慶;從歐美來華組織,到日本醫界的影響,甚至日本殖民台灣的公共衛生經驗,都曾經影響當時中國的國家治理。這不僅是現代中國的誕生,更是中國現代性的創生,也是東亞世界的交流與創造。
中醫從幾乎被西醫邊緣化的危險境地,到成為兩岸官方認可的醫學體系,甚至躍升為全球另類醫療的主力,我們絕對不能錯過這段中醫奮鬥的歷史經驗。綜觀世界,有哪一門傳統醫療在經歷了科學霸權年代,能夠存活下來,甚至貢獻自身回饋給主流醫學呢?放在全球史的脈絡下,這些經驗將迫使我們重新反省科學的普世性。這不僅是一部政治史,也是一部科學史。


,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5,頁146。.p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