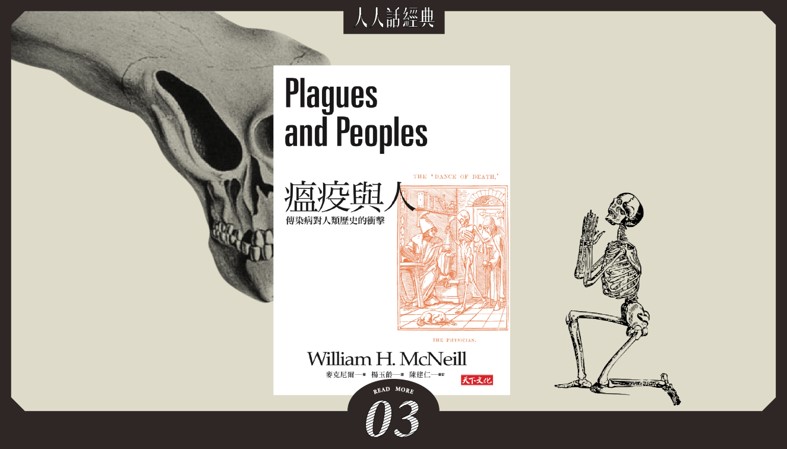卡法(現費奧多西亞)是義大利在黑海岸邊的一塊碎片,熱那亞商人乘著槳帆船來到此地,向駱駝商隊購買來自遙遠東方的絲綢與香料。
西元 1343 年,蒙古大汗看上貿易的果實,藉故驅逐義大利人,繁榮的貿易都市在圍城下支撐了三年。風雨垂零之際,蒙古鐵騎突然被疾病擊倒,每日都有數千人在惡臭與高燒中死去。
一開始,義大利人以為疫病是他們的救星,卻沒想到蒙古人竟在絕望中突發奇想,用投石機將死屍拋入城中。編年史家德謬西紀錄寫下「屍臭如泰山壓頂,幾千人裡大概只有一人能躲開韃靼軍的屍體。」這是史上最早的生物戰,也標誌了黑死病的開始。
惡夢的起點
早在西元前兩千年,蘇美人就記錄了最早的傳染病,《舊約》中也寫過上帝以瘟疫懲罰人群。然而,我們真正了解傳染病對歷史的影響,卻得等到二十世紀。
1955 年,歷史學者麥克尼爾審閱十六世紀「征服者」科爾特斯的事蹟,不禁懷疑區區 600 人的西班牙探險者,究竟是如何征服幾百萬人的阿茲特克帝國。直到他發現,阿茲提克的指揮官擊敗柯爾特斯四個月後死於天花,他才領悟,征服兇猛的阿茲特克戰士的並非火槍與馬匹,而是無形的病毒。
世界貿易未興前,文明各自與當地的傳染病達成平衡,形成由各自隔離的「疾病庫」。新大陸的居民從未接觸與舊大陸的居民「共存」數千年的傳染病,因而毫無抵抗力。當歐洲殖民者抵達新大陸時,就把福音連著死神一起傳到美洲。原本致死率約三成的天花,最終殺死了近九成的原住民。
來自鼠疫
在喜馬拉雅山腳住著許多大型囓齒動物,這些地松鼠與旱獺長約 60 公分,重更可達八公斤。但即使行動緩慢,大草原的居民從不獵殺這些過胖的松鼠,因為牠們承載著一種致命的細菌-鼠疫桿菌。鼠疫的原生宿主很少出現在亞洲大草原外,但鼠疫桿菌還能感染兩種動物-跳蚤與大黑鼠。當跳蚤咬了帶原的地松鼠,就成了疫病的橋樑,而大鼠就是跳蚤的公車。當身上滿是跳蚤的大黑鼠因鼠疫桿菌死亡,跳蚤們只能尋找下一個宿主,有時是馬匹與駱駝,有時是人類。
隨著貿易發展,大鼠跟著商隊、乘著帆船,逐漸從亞洲旅行到了古典世界邊緣。西元 541 年,黑死病在埃及第一次與西方文明接觸。瘟疫在拜占庭與波斯帝國間肆虐,重傷了纏鬥已久的宿敵,也中斷了查士丁尼中興羅馬帝國的偉業。居住在炎熱乾燥的阿拉伯沙漠的穆斯林,未受瘟疫打擊趁隙崛起。
之後數百年間,歐洲商人無法繞開伊斯蘭世界的阻隔,只能向穆斯林商人購買層層轉賣的東方商品。歐洲人因此對印度魂牽夢縈,連「地球是圓的」的奇想都想得出來,但「穆斯林隔絕」也讓歐陸免於亞洲疾病庫的荼毒,直到蒙古人一口氣打通了半個世界。
黑死病入侵下的歐洲
蒙古人在所到之處設下驛站,絲綢香料在駱駝商隊間輾轉,一路從中國北京走到黑海岸邊的卡法,跳蚤也跟著搭了便車。1331 年,中國收到第一批鼠疫的報告。 1346 年,惡臭的蒙古屍體循著拋物線掉到了熱那亞人頭上。
有些水手幸運地從已成死城的卡法逃出,搭著槳帆船回到西西里的墨西拿(Messina),他們帶回厄運的消息,也帶回了厄運本身。瘟疫在墨西拿爆發,逃離的倖存者又進一步擴散了疾病。一位教士記錄「墨西拿人如此受憎恨、畏懼,以致沒人願跟他們講話、與他們為伍,一見著他們就屏住呼吸,拔腳而逃。」
與查士丁尼時代不同的是,十四世紀時的地中海貿易網絡更加穩固綿密,通往大西洋的航路隨摩爾人的衰退開啟,大黑鼠也在新興的都市中亂竄,這些都讓瘟疫更加迅速的在人群間傳播。大鼠與瘟疫乘著商船,在港口間來來去去,從瑞典的斯德哥爾摩到西班牙的賽維利亞,黑色死神壟罩了全歐洲。

《十日談》的作者薄伽丘寫下了黑死病的症狀:「無論男女,它最先以腋窩與胯間的腫囊顯露自身,有些大如蘋果,有些小如雞蛋。致命的瘡痔蔓延至身體四處,症狀接著改變,黑斑在四肢出現,大者數塊,小者無數。瘡痔無疑標誌了死亡的到來,不論在誰身上都是。」
有些人相信黑死病是上帝對縱慾的神罰,控制欲望能阻止疾病,他們組成了封閉的小小社群,拒談死亡與疾病有關的一切。有些人則相信死亡無法避免,他們跳起「死亡之舞」,在無人的街道夜夜笙歌,縱酒狂歡。也有人拋棄了財產、家庭、國家,試圖在城牆外躲避上帝的怒火。
「恐懼與幻想攫取了所有活人的心智,幾乎所有人都採取了同樣的殘酷態度:徹底避開患者與他們的所有物。每個人都以為如此就能確保自身安全。」薄伽丘記下了人們的慘況,此時,不論是天堂與塵世的權威,在折磨與苦難中都不再有意義。然而,沒有任何方法能緩解瘟疫,大部分的患者都在三日內死去。
人群大批大批死去,甚至來不及幫死者舉辦葬禮。一位義大利市民寫道「所有人除了把死屍扛走,根本做不了其他事。每間教堂都挖了深及水面的大坑,在晚上死去的窮人裹一裹就這麼丟了進去。到了早上,屍體太多就鏟些土遮住,再繼續把屍體堆上去,就跟做千層麵一樣。」他倖存了下來,但也親手埋葬了自己的五個孩子。
瘟疫的替罪羔羊
在死亡的壟罩下,基督徒轉向了猶太人。猶太人被控在水井裡下毒,製造了黑死病。獵巫式的審判下,許多猶太人屈打成招,承認了他們的「罪行」。1348 年,普羅旺斯的猶太區被洗劫,49 位猶太人在家中被殺死。
起初,教宗克萊孟六世試圖制止,頒布詔令指相信猶太人是罪魁禍首的人是被「騙子魔鬼迷昏了頭」,神聖羅馬皇帝查理四世卻下令被殺死的猶太人財產充公,讓不少欠猶太人債的諸侯有充分的動機對暴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隔年,日耳曼爆發了反猶活動,少則數十,多以千計的猶太人在數百個城市中被屠殺。當年情人節,未受瘟疫侵襲的聖特拉斯堡「先發制人」,特別建了棟木屋,在裡頭活活燒死了八百位猶太人,大火熄滅後,居民在餘燼中爭奪財物。猶太人因此大舉東遷,投入波蘭國王的保護,之後數百年免受反閃主義荼毒。不過,殺死猶太人沒有讓任何城市免於黑死病的侵襲。事實上,後世認為猶太人受黑死病影響較小的原因是猶太社群不常與市鎮共用水井,且猶太清規中有許多有利防疫的傳統。

黑死病深遠影響
過了數代,歐洲才逐漸與黑死病達成「疾病平衡」,遠至四百年後英格蘭的人口才回到黑死病前的水準。黑死病奪去的五千萬條人命,在歐洲社會的文化、宗教、經濟等層面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黑死病的生命經驗啟發了《十日談》,使貴族開始及時行樂,贊助從天堂轉向人間的藝術家,開啟了義大利的文藝復興。許多有經驗的教士因疫病死去,為了填補空缺,教廷倉促地訓練任命新人,這些參差不齊的新教士加劇了教會的腐敗,隱隱預示未來的改革。貴族試圖以法律把日漸稀少的農民綁在農田上,東歐貴族成功的鞏固了農奴體制,西歐農民卻建立日漸市場化的契約,標誌了封建經濟的衰亡。
歷史作家唐·納爾多寫道「一旦人們在停滯秩序中窺見改變的可能,臣服時代的終結指日可待,個人意識的轉向就在前方。這麼說來,黑死病或許是現代心靈未為人知的開端。」黑死病奪去無數靈魂,但黎明前的夜晚總最為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