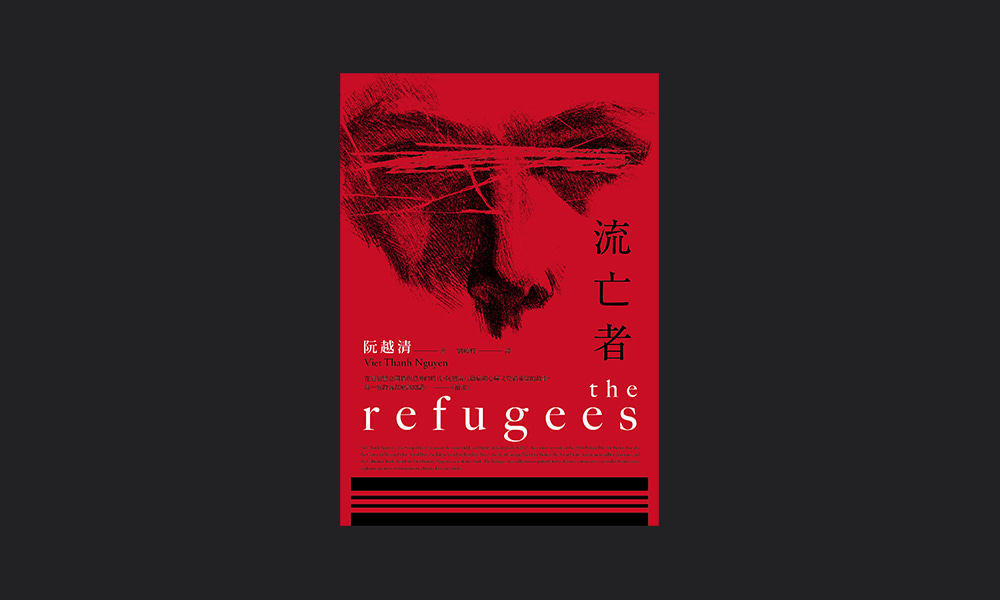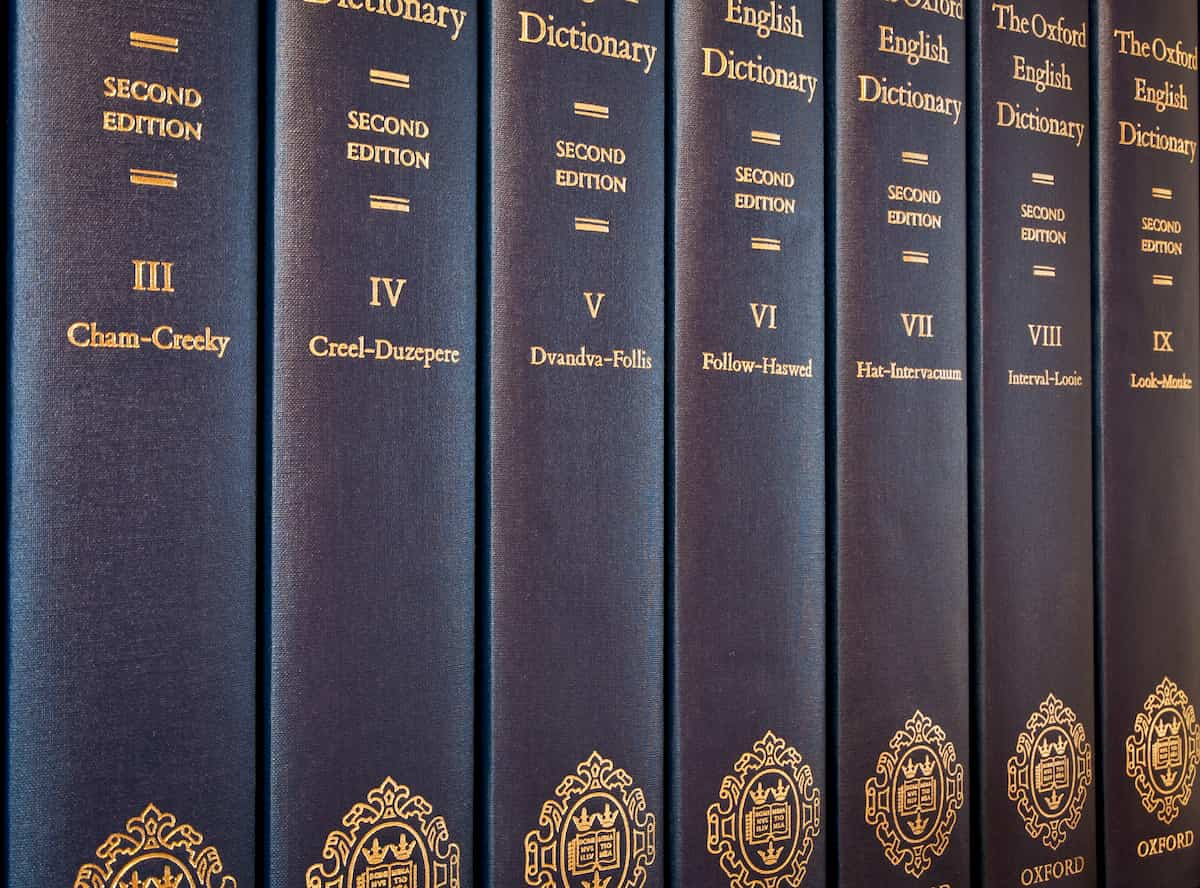世上有一群癡迷水果的人,他們遠離公眾視線,非常非主流,徹頭徹尾地將人生奉獻給探求水果的偉業。借助於「北美水果探索者協會」、「珍稀水果全球聯盟」這些民間組織,不為人知的地下水果世界就跟他們始終追隨的花果神一樣特立獨行。
「forest」(森林)這個詞來源於拉丁語中的 floris,意為「外界」,卻通常吸引著真正的外來者。自 1910 年始,「fruit」(水果)就被用來形容行為古怪、與眾不同的異類。寫這本書,也就意味著深入瞭解水果書呆子、水果走私販、發掘水果的探險者、膜拜水果的信徒、創新水果的發明家、水果員警、水果強盜、素果人,甚至包括一位水果按摩師。這些別具一格的人物,也在這個星球的多樣化中占有一席之地——無論從植物學還是人類學立場,都一樣精彩。
水果狂人羅伯特・帕特
水果對我們的誘引,能到何種程度?參見 2002 年羅伯特・帕特(Robert Palter)的《瑪菲公爵夫人的杏及其他文學作品中的水果》即可窺知。這本專著洋洋灑灑 872 頁,試圖對歷代小說、歌曲、電影、詩歌及其他文學樣式中出現的水果加以分類討論,其野心和癡狂都無法按捺,實有不吐不快之勢。甚至專門有一個章節,鉤沉出某些書中明顯漏掉或缺失了的水果。
帕特年屆八旬,是位退休的教授,曾參與研究原子彈的「曼哈頓計畫」。讓他最快樂的事,便是探討語義曖昧的斷章殘詩所影射的水果——理應被冠以「蘊涵宇宙奧義」的水果——譬如大詩人安東尼・赫克特(Anthony Hecht)的《葡萄》充滿了星球體和透明圓球的意象。

當他解讀威廉・迪基(William Dickey)的《李子》時,幾乎要把拳頭解剖開來看,引用的詩句中提到李子的生長:「艱澀地挺進,春天裡的一隻拳頭/薄膜瘀傷的緊握的拳頭/痙攣⋯⋯。」帕特得出的結論是,這首詩「始終意圖打破傳統田園詩格式緊握不放的精妙感」。
慾望、腐敗、諷刺,都是水果的滋味
我在黃頁電話本裡找到帕特的電話,打了過去。他對入嘴的水果倒不是特別感興趣。「到手的果子,我會為其哀嘆。」他嘆了一口氣,在康涅狄格州的寓所接聽我的電話。但過了一會兒,談到他直到最近才第一次嘗到新鮮的無花果,情緒才高漲起來:「我心想,『不可能有這樣的有機體啊——實在太過分了!』」他興奮的聲音傳過來,成了聽筒裡一連串短促而急切的短音。
我問他,何以對文學中的水果這麼感興趣。「水果和人類生活、愛、性和享受之間顯然有關聯。」他回答,「但水果會爛掉!所以,同時還有消極的潛台詞。水果可以暗喻政治腐敗。我可以給你找到很多文學中的實例,用水果來隱喻任何人類的情感,甚至是極其微妙難辨的情緒——無所不包」。
鮑勃・狄倫(Bob Dylan)在《重訪 61 號公路》的光碟封套裡寫過這麼一句話,諷刺某人「正在寫一本講述一顆梨的真實意義的書」。帕特的書裡沒有摘引狄倫這句話,而是提到梨子意蘊無窮,無論是作為性物、希望落空的形象,還是熵的隱喻物,都能說得通。要說帕特的研究精髓何在,便是指明了水果的真正力量在於足以誘惑我們。

(Source:Wikimedia)
最初,他研讀了一篇有關水果的散文,但一旦研究起來,資料迅速積累到令人瞠目結舌的數量。沒多久,他就被鋪天蓋地的實例淹沒了。「每一次我在某篇小說裡找到一則水果的新例,我都會說:『哇哦!真是難以置信!』」圖書館裡的員工也給他起了綽號,背地裡叫他「水果傢伙」。積累了汗牛充棟的水果逸事趣聞後,他聯繫了南卡羅來納州大學出版社,打算出一本三百頁的書。等他交初稿時,篇幅已比預期值翻倍,膨脹到六百頁。等到即將付梓印刷時,他仍在孜孜不倦地增添新內容,直到出版社下了「最後通牒」!
夠了,真的夠了!他在書的引言中寫道,這個項目注定沒有所謂的結局,毋寧說這本書只是「階段性報告」。他決意,不在書的末尾加上標點符號,以示其永無終結。書出版後很久,他依然停不下來,有關水果的段落篇章繼續累積。正如他在名為《我的水果巨作》的回憶錄中所寫:
不知不覺間,不管看到印刷品還是照片,我都會尋覓水果的蹤影,簡直欲罷不能。
掛上電話前,帕特說他正在考慮把手頭所有的水果相關書籍都捐獻給圖書館。「我得和水果一刀兩斷。」說著,他忍不住重嘆一聲。話是這麼說,在我們交談後數月間,他一直給我發電郵,全都是有關水果的奇聞逸事。其一便是他的「最新發現」:西班牙作家哈威爾・馬里亞斯(Javier Marias)的長篇小說《一切魂靈》中的一景。他標注了頁碼,解說上下文是「一場大學教員的晚宴」,吃甜品時,學監「執意用一條橘瓣串成的項鍊,裝點約克系主任太太的胸脯」。這封電郵最後寫道:「這場面多帶勁兒啊!祝福你,羅伯特。」
「每有水果入口,我們都在咀嚼被遺忘的歷史」
文學作品中的水果多姿多彩,可我還想知道水果背後的故事——能吃的、真實的水果。在超級市場裡,我們可以從貼在水果上的標籤追溯到特定的人或地。哈斯酪梨(Hass avocado),其名來源於郵遞員魯道夫・哈斯(Rudolph Hass),他住在美國德克薩斯州帕薩迪納市,孩子們央求他不要把一株怪異的秧苗砍掉,結果,他在 1935 年獲得了這種酪梨的專名權;時至今日,在全世界出售的所有酪梨中,絕大多數都是哈斯酪梨。

還有美國的檳櫻桃(Bing cherry),其名來源於十九世紀美國俄勒岡州的中國東北人阿檳(Ah Bing),另外,克萊門氏小柑橘(clementine),得名於克萊門・羅迪恩(Clément Rodier)神父,1902 年他在孤兒院為這種柑橘和酸柑的雜交品種施洗。柑橘變種之一坦吉爾柑橘(tangerine),來自摩洛哥城市坦吉爾。丁岡(Dingaan)蘋果得名於非洲酋長,他殺害親兄弟後被人殺死,而麥金托什(McIntosh)蘋果的起源則是一顆破碎的心。
約翰・麥金托什(John McIntosh)出生於 1777 年的紐約,年輕時深深愛上多莉・歐文(Dolly Irwin),她的父母都是反對美國革命的「聯合帝國忠臣」,同樣,也反對親生女兒的婚姻。歐文夫婦帶著女兒移居加拿大,十八歲的麥金托什也尾隨其後。不幸的是,等他趕到歐文家在康瓦耳的露營地時,多莉已經香消玉殞。悲慟至極的麥金托什怎麼也不相信這是真的,掘地三尺,挖出遺體,這才確定愛人真的不在人間了。屍體早沒了人樣,他伏在上頭久久痛哭,好不容易才起身離去。
最後,他在安大略省的易洛魁族人村落附近找到一片地,定居下來。地裡野草叢生,荊棘瘋長,灌木過盛。整頓田地時,他發現了二十棵矮小的蘋果樹,但沒多久幾乎都死了,只有一棵存活—還結了異常多的果子。他把這棵樹的枝條嫁接到別的樹上,到了二十世紀初期,麥金托什蘋果就隨處可見了。
「每有水果入口,我們都在咀嚼被遺忘的歷史。」不只是神奇的蘋果,綜觀歷史,帝王將相、皇后嬪妃都曾品讚奇果。十二世紀的詩人伊本・沙拉(Ibn Sara)把橘子比喻成處女的臉頰、熱火之炭、被愛情之苦催熱的淚花、黃晶枝條上的紅玉瑪瑙珠。水果令我們詩興大發、妙喻連連。鳳梨最初被引進英國時,在貴族階層引發了一陣瘋狂追捧。香蕉在美國曾經意義非凡,以至於在《獨立宣言》一百週年的慶典上被當作「抗爭的證據」供奉起來。香蕉象徵了自由,柏林牆倒下的時候,垃圾桶裡裡外外都是香蕉皮,好像那是東德人能買到的第一件寶物。
直到現在,不管在自家後院還是國外,我們探索水果時,也就是與大自然重新接軌的時刻,通往至高境界。要想體驗「生之愛」,就要盡力去愛多姿多態的生物,沒有界線,又很脆弱;多樣化的正反兩面既讓我們魂牽夢縈,也能讓我們滿懷希望。這本書,是有關水果,有關人類和水果之間的緊密聯繫。要預先提醒諸位的是:閱後可能魂不守舍,有口乾舌燥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