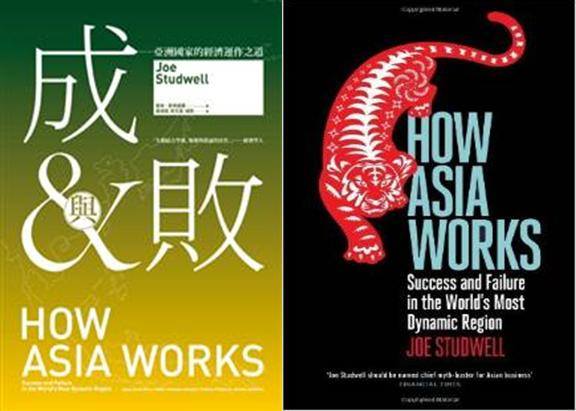在我人生的首二十多年,對臺灣的認識可謂相當皮毛,要數的話,僅限於一般旅遊地區,而且還是旅遊團安排的典型景點。但臺灣這島似乎就像命運一樣擺脫不掉。小時要跟父母去,接著是中學時期跟阿嬤一整家人去,然後是大學畢業後加入的首家公司為答謝員工的旅遊……臺灣之於香港,畢竟算是對男女老幼都很相宜的外遊選擇。
不但距離不遠,而且也用繁體漢字。料理方面更是可滿足不同年齡層的胃口:老人家可吃中華料理和各種臺式小炒;愛吃日本料理的港人,在這裡能輕易找到更實惠的選擇;而各式咖啡廳、甜點、火鍋等,給年青人的享受亦多不勝數。總言之,臺灣無疑是港人團體旅遊的輕鬆之選。
我曾以為,以這種吃喝玩樂的心態遊玩臺灣就足夠。要認識當地更深嗎?反正,以後國語[1]學好一點就是了。當然,這個「以後」遲遲沒有正式降臨。只是,誰也猜不到,後來讓我認真探問起臺灣生活的,是一些相遇和印象,絕沒有也不需一個所謂「正式」的原因或時點。初成為自由工作者時,恰巧認識了一些臺灣朋友,便開始去臺灣探索。每一次離開時,心裡想看、想體驗的名單總是又增長了一點,於是又趕快訂下下一次去的時間。我在當地遇見一幕又一幕深印在腦海的場景,無形中竟在心裡累積成越發深廣的湖,沉靜地躺著。
我期待這個湖得以日漸完整而昇華,但卻缺乏表達那些養分的語言。而每逢在臺灣過生活,就好像有更多礦物安分地累積,等待沉澱和表達。雖然可能會漸成一種鬱結,但亦暗藏待受語言解放的興奮。它好像正在形成一股我從未見過的東西,似乎只要有方法整理表達,湖面就會生起一條閃爍燦爛的橋,或通向星河的大道;好像只要取得動力,就可形成滋養萬物的有機環境,湖水可以揮發成雨點,積聚成雲,建立循環,成為一幅生機勃勃的圖畫。當初就是有這麼一段時間,我的心裡如此累積起一個寂靜的湖,待著,也彷彿在沉睡。
一年初夏,我從臺南北上,跟友人亦修相約吃午餐聚舊。當天是平日,午飯時間過後,餐廳就剩下我們,一個研究生、一個自由工作者,在餐後悠然聊天。我們兩個港人就像獨占了餐廳的舞臺,以廣東話暢所欲言,除了互相更新近況,更分享了不少生活小發現。亦修比我更早到臺灣來。他是留學生,而我不過是間中來臺的訪客,只是待久了,開始想擺脫「觀光客」的標籤罷了。
那次聚舊,我禁不住跟他坦白自己對於「發現臺灣」的一些小驚嘆。當時我猜想,本身研修臺語文化的他,可能會認為我的發現無足輕重,或甚至覺得我大驚小怪。但由於我覺得自己的驚嘆是出於我香港人的身分,所以可能只有同為香港人的亦修能聽明白。結果,他聽著聽著也很欣然,對比我們在香港的生活時,更是興高采烈。
那次,我到底跟亦修說起什麼驚嘆的事?首先要數我當時剛從臺南得到的體會。
追溯芭樂的語言身世
有一天,在陽光普照的南方下午,我跟當地友人走過一臺芭樂車。車子停靠在公園路邊,一位老伯正緩緩整理小貨車上堆得像山丘的芭樂。友人看我一直觀察這個場景,便說:「啊,伯伯在賣『拔啦』呢。」拔啦?真奇妙。莫非因為我的國語不好,一直把「芭樂」講錯了?正當我打算取笑自己怎麼連這種日常事物都仍然說不好的時候,友人卻解釋,「拔啦」不是國語,是臺語「菝仔」的意思,亦是臺灣人對「芭樂」的常用念法。那時,我才恍然大悟,原來臺灣在地使用的語言不是只有國語一種。
我想,雖然大多數港人都知道有臺語這種語言,可是臺語在臺灣有多常見?在哪裡比較普遍?這些都不是港人一般會關注的問題。我們看到「蚵仔煎」便用國語照著念,「芭樂」也一樣。只看見它們同是漢字,卻沒想過為何與香港人使用的名詞不同。這次芭樂之會,給了我一番震驚。友人並非在造作賣弄,不過是自然而然說出了「菝仔」。我開始想,這種水果到底是先叫「芭樂」,還是臺語所講的「菝仔」?為什麼說國語的臺灣人,有時卻不用國語講「芭樂」?

這個問題在心裡漸變得急切。我亟欲找到正當性來說服自己,或許「菝仔」是很偏門或過時的說法,自己確實沒必要去學臺語叫法。畢竟,學國語已經不容易了,難道還要學別的漢語語言嗎?
說來,其實心情也很糾結。首先,「芭樂」這名詞對香港人來說已經歷了一重翻譯。香港人一般稱這種水果為「番石榴」,意思大概就是外來(番)的石榴品種。中國大陸也叫「番石榴」。港人可能習以為常,也就少去想臺灣對這種水果為何另有專稱。如今,終於知道「芭樂」有與國語發音相近的臺語念法,是真的該趁機去查查看這個名字的來由。
可是,這種名字的來源找起來也不容易。我認為《蚵仔煎的身世:臺灣食物名小考》一書裡的解釋最為詳細。裡面提到「菝仔」這臺語名詞,特別是「菝」這個字,有可能是從歐洲語言而來。沒錯,是歐洲!這下子,可令謎題更添趣味了。書裡說,芭樂的名字在葡萄牙文「goiaba」和西班牙文「guayaba」都以「ba」音作尾,可能就是其臺語名字「菝」的由來。我們一般認為臺語就像廣東話一樣,是比較本土、非國際化的語言;可是,芭樂的背景,居然暗示臺語曾受西方影響?
事實上,別看臺灣今時今日盛產芭樂,就以為它是臺灣的原生植物。它的原產地為中南美洲。我為了尋找這個臺語名字的來源,特地去圖書館查了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的食物指南,裡面提到歐洲人最初在海地發現這水果,而當時其海地名字為「guayavu」,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航海員後來把這種水果帶到世界各地去。我記起大學上西班牙語課時,學到西班牙和葡萄牙語會把聲母「v」發成像英語聲母的「b」音。
如此一來,把水果傳開來的航海員很可能把海地名字尾音的「vu」發成「bu」,並因而演變出以「ba」作尾音的西班牙及葡萄牙名字。這只是我的推測。食物指南又記載道,芭樂在十七世紀便普及於東南亞地帶。當時正值大航海時代,歐洲多國透過航海接觸和占領東南亞各地,臺灣北部於十七世紀也曾被西班牙人占據。所以就像《蚵》書所分析一樣,追溯歷史,臺灣人首次為此外來水果命名時,真的可能受其西班牙名影響,造就了「菝仔」的臺語叫法。
除此以外,如果硬要把「芭」和「樂」用臺語念,發出的音並不是「菝仔」。根據種種線索,大致可推斷是先有「菝仔」的臺語講法,才有「芭樂」這個發音相近的國語名稱。「芭樂」這個名詞,應是根據臺語「菝仔」的念法音譯而成的國語名詞。
這就像香港以前會把日常用語寫成較正式的書面語,例如「的士」(Taxi)和「窩夫」(Waffle)。在臺灣也有相似的口語影響書寫的情況,「芭樂」就是一例。有了背景脈絡,便忽然覺得學臺語叫法也不是那麼艱深的一回事,還覺得「菝仔」好像比「芭樂」更順口了。同時,似乎也明白了為何不少臺灣人會講「菝仔」,而不一定用國語念「芭樂」。畢竟,後者是硬譯出來的書面語。某程度上,聽一個人怎樣叫這水果,就可得知對方是什麼樣背景的臺灣人。

一聲稱呼的背後故事
這件事,屬於我對臺灣的驚訝發現。單單嘗試理解一個當地名詞,就發掘到一點關於當地語言、生活以至社會歷史的故事,裡頭反映的多元世界,教人驚嘆。我想起香港的一些獨特名詞也能勾起當地的生活事跡,原來在臺灣也一樣有。而且,裡頭的多元與複雜細節,似乎比香港有過之而無不及。畢竟,臺灣比香港大得多。
以前糊裡糊塗的,只知道臺灣的臺語是國語以外的本土語,有點像是臺灣本地的「鄉下話」。曾聽說過臺語就等如中國福建的閩南語,但沒有詳細考究。現在才知道,原來一些臺語詞源可能跟廣東話一樣,受到過去殖民者帶來的文化影響。
以往臺灣的殖民者,除了日本人外,還有荷蘭人和西班牙人。語言與生活中可能還有更多外來影響,而我還未發現。而到底臺灣的「鄉下」指的是哪裡?是否即鄉郊或較為落後之地?還是純粹指本地人的「家鄉」?如果是後者的話,在今時今日的全球化和資本主義社會,「鄉」則不一定意味著落後,不過是客觀的地理文化根源而已。這些種種,我從前都沒想清楚。
除此之外,還要再多考究的,是臺灣的原住民也不止一個族群。臺灣漢人說的臺語在很早以前,就跟當地各種原住民語互相影響、共存,也即是說,有不同語源影響了臺語。同時,臺灣的國語跟臺語又一直微妙地互相影響。在今天的臺灣,臺語不只是特定地區的人所使用的語言,芭樂的案例反映,有些名詞在臺灣普遍都用臺語發音。
跟亦修談起,才驚覺原來這裡的日常潛藏了那麼多讓人了解當地的線索。過去二十多年來,我卻一直以香港主流的旅遊視角去看這地方,只懂得留意吃喝玩樂的地點,結果錯過了各種生活小線索。我發覺,臺灣與香港有些地方很相似,除官方語言外,還有(多於一種)本土語言環繞日常生活。
這兩個地方的在地經歷,例如官方語言的合理性、方言使用、公眾場所的多語制度等議題其實有所相似,也許值得互相參考。此外,臺港兩地非但只隔一個海岸,也同是島嶼之地,以航海貿易建立繁榮。兩地在地理上的優劣、維生方式、城市設計等等,皆有可互相取經的面向。雖然臺灣比香港大得多,但兩地人的生活小故事,應該可產生不少共鳴。
在兩地,用談生活的語言談心
發現到兩地有相似又彷彿相連的命運,就有種親切感,我亦找到更多角度去觀察和思考兩地生活。我甚至覺得心裡好像得了一股力量的泉源,發現臺灣的多元性,好像給了身為香港人的我一個自白的切入點。一直以來在心底累積的湖,好像有了溫度和生機,水點開始揮發成雲,建立起生態系統。活在香港的朋友,不都常常暗自憂愁,如何消除外界看我們那些種種過分簡化的誤解嗎?諸種大眾傳媒的論述,似乎還不足以形容我們實際的生活細節。
每每出現重大的基礎建設或政策爭議時,各種立場之爭所宣示的大標題和口號,都蓋過探討多元小故事的可能。此外,這個城市多年來取得的揚名海外的標籤,像「東方之珠」、「國際大都會」、「飲食之都」、「交通發達的彈丸之地」……這些大名好像在今時今日也流通處處,但真正生活在香港的我們,根本自知那些美譽已過時。今非昔比,我們已漸漸難以這些標籤自傲。
可惜,標籤的影響好像也感染了腦袋,限制了表達,導致我們有時想要解釋真正的生活體驗時,卻不知該從何說起了。日常的語言好像離實際生活越來越遠。社會上聽到和談到的,就像諸種口號和標籤一樣,跟我們實際所經歷的,有越來越大的鴻溝[2]。表達自己變得越來越困難。該怎麼說?踏實而貼切的字詞好像都從日常討論中消失了。
在發現臺灣的旅程裡,我無意中領會,其實日常的多元細節,統統都是認識自己、形容自己的關鍵。我心裡的湖,原來統統都是生活點滴,只因難以與日常的論述連接,欠缺呈現方法,便默默在心裡累積。與亦修談著談著,才發現我們最想討論的,都應該從最基本的日常體驗說起。既然沒有既有的解釋框架,也就直接由描述最平庸的生活開始,期望藉以分享種種似乎難以述說但真實的生活體驗。
畢竟,臺港兩地對某些事物就是有不同的說法,也因地域和生活方式演變出或近或遠的價值觀和文化。假若硬要忽視那些生活細節,並以單一的論述試圖蓋過多元的生活故事,那麼最終可能只會令主流語言無法表達生活的本質。我想,大概是這樣吧。我曾看臺灣作家吳億偉提到,他意外發現自己的著作《芭樂人生》在中國大陸譯作《番石榴人生》,認為「感覺整個故事也不同了」,「『芭樂』也脫胎換骨了」,幽默之餘,更令我覺得,探討日常真正使用的語言和面對的事物,也能發掘出豐富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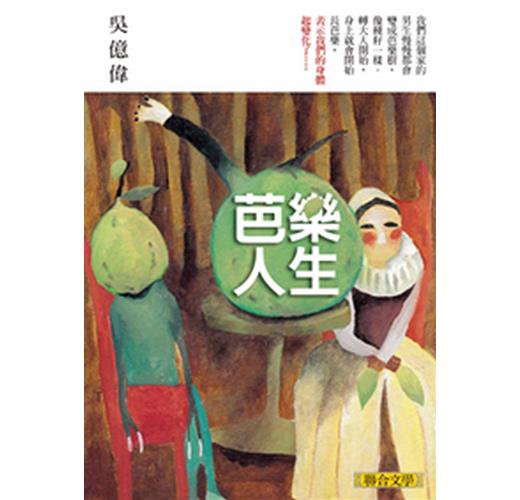
話說回來,看過一些關於芭樂的背景,才發現臺灣一年四季都生產,難怪日常可容易找到。這種果樹很好種,能適應多種土壤和氣候,但生長時會搶去土壤裡大量水分,容易排擠其他植物,有可能威脅到當地的生物多樣性。怎麼這種力量聽來,那麼像剛剛提到霸道的單一論述?芭樂可算是植物界的地霸,種植芭樂前的規劃應該不能馬虎。
單單因為遇到芭樂這件事,居然就把我從以前的井底拉出來,讓我突然看到許多一直存在的語言與生活脈絡。也許冥冥之中,我注定要遇上那臺芭樂車,並透過芭樂的暗示,終於啟程去認識臺灣,重新學習表達我一路走來的生活風景。

而當離鄉的兩個香港人,在異地臺灣再相會,有了長期旅居的時間醞釀,和文化觀察之眼的沉潛,一場從芭樂開始的閒聊,才終能拉出一連串從語言帶到生活的日常經驗比對,而體悟了種種:有從鴿子籠小套房到寬敞廁所的都市景況、有單人火鍋到中秋烤肉聚會的人際遠近,也有從漂泊到再紮根的身分認同。
[1] 「國語」表示在臺灣所說的標準漢語,亦可稱為「臺灣華語」,以便與北京官話、普通話作區分。臺灣於 2018 年通過了國家語言發展法,定義「國家語言」為臺灣各固有族群使用的自然語言及臺灣手語。雖然已有此廣泛定義,但臺灣大多仍以「國語」作華語俗稱。相比之下,香港學校所教的標準化北京官話一般稱作「普通話」。
[2] 這種被主流論述、標籤蒙蔽心眼的體會,可歸納為一種「視而不見」的現象。研究香港文化的學者 Ackbar Abbas 就以「逆向幻覺」(Reverse hallucination) 來形容香港的這種情況,那就如同幻覺的相反,不是看見不存在的東西,而是明明事物擺在眼前,但人們彷彿看不見,只繼續被陳腔濫調、主流大標籤等意識形態主導所思所行。詳情請見 Ackbar Abbas 的著作: Hong Kong: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