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回到刀光劍影的 1927 年。
南京政府的通緝令下達後,雖然不能直接到租界抓人,但當局若驅使黑幫動用綁架手段則防不勝防。工部局安排巡捕日夜保護榮宗敬。這一天,紗聯會副會長穆藕初[1]帶來好消息,紗聯會召集臨時會議作出決議:
會議提議,本會各廠派銷附稅庫券 50 萬元。除已由各廠認繳 1/4 外,其餘 3/4 計 37.5 萬元,當局仍在催繳,應如何籌措之處,敬希公議。
議決如下:第一,致電蔣總司令為會長[榮宗敬]解釋誤會;第二,庫券案,決由各廠勉力擔任,餘數如不足額,再設法籌措,但須由會長交付。

榮宗敬看過後,倔脾氣又上來了:「藕公,我謝謝你和各同仁的好意。但此次臨時會議並非由我主持,這決議是無效的。姓蔣的要通緝我,連他帶衛士出入租界還得工部局發給通行證,看他能把我怎麼樣!」
穆藕初勸導說:「宗公!你不要糊塗。現在是什麼人的天下?外面軍隊在殺人,警察在殺人,杜月笙手下的流氓幫會也在殺人。我有個族侄在報館工作,我敢擔保他不是共產黨,也被不明不白地被殺害啦!你能永遠不出租界嗎?就是在租界裡也不見得就安全呀!」
直到此時未發一言的榮德生,終於說話了:「宗敬,我們權當碰上一場火災。認了吧!」[2]
緊接著,榮氏兄弟求助於無錫老鄉、國民黨元老吳稚暉。吳稚暉約上蔡元培、張靜江一起去見蔣。三大元老聯袂登門,蔣介石不得不傾聽他們的意見。
吳對蔣説,從未聽說榮宗敬依附孫傳芳,也無為富不仁之事,何況他首倡實業救國、興辦工廠,歷盡艱辛,無錫人的很多優點集於一身。蔡元培也説:「無錫榮氏身為商界巨擎,非為個人謀財致富,而致力於社會公益,尤其是興辦教育,稱譽海內,堪稱張謇第二。榮氏是關心國事、熱心社會的實業家,政府理應大力保護,方能安定商界局面。」[3]

有多名元老出面,且榮家願意出錢消災,蔣介石樂於順水推舟。6 月 4 日,蔣下令對無錫榮家啓封。
榮宗敬事件顯示,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後,蔣介石與資產階級的合作關係,很快變成從屬和利用關係。南京政府與資產階級的蜜月還沒有開始就結束了。蔣介石政權所關心的只是「在政治上使城市菁英階層處於依附地位,在經濟上對他們加緊剝削。」[4]
蔣為了獲得資金,對資產階級多有承諾,但他的要求超過銀行家和工商界所樂意提供貸款的限度,當說服無效時,就用強迫手段去硬索。蔣把原來用於對付工會和共產黨的那股恐怖風浪轉而用來對付資本家,他將上海的幫會組織拉攏過去,讓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等幫會頭目組成「上海鋤奸熱血團」、「鐵血團」等秘密團體,專門以綁票等恐怖手段對付不聽話的商人。
蔣介石把資本家當作奶牛,他自己是擠牛奶的人。他不斷提出新的付款要求,加重對商人的敲詐和勒索。[5] 在上海的外國記者索科爾斯基寫道:「各種迫害的方式都在搜捕共產黨的藉口下使用出來。許多人被綁架並被迫獻出大量軍事貸款……這種反共的恐怖手段使上海和江蘇人民感到近代以來絕無僅有的恐懼。」[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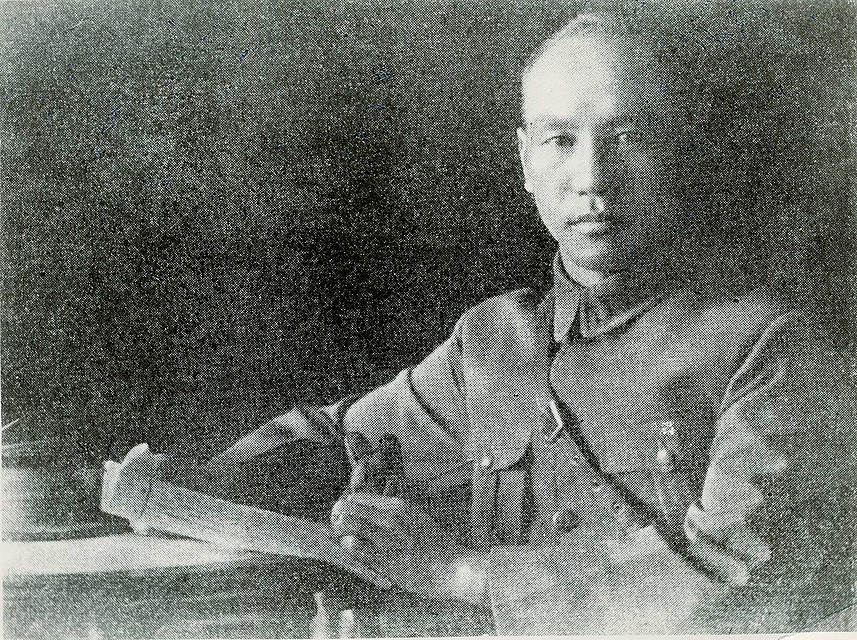
榮宗敬只是家產暫時被封,人身畢竟未受傷害。相比之下,其他上海灘富商的遭遇更慘:1927 年 5 月 14 日,住在租界的顔料富商石寶順的兒子以反革命的罪名被逮捕,在石答應向國家捐獻 20 萬元之後,5 月 19 日其兒子獲得釋放。
5 月 16 日,酒商趙志永被捕,捐了 20 萬後獲釋。先施公司經理歐炳光 3 歲的兒子也被綁架,被要求給黨國事業捐款 50 萬元。棉紡廠主徐寶真的一個兒子以共產黨員的罪名被逮捕,被勒索 67 萬元。採用逮捕和以逮捕進行威脅的手段向商人和官紳勒索錢財,根據美國領事的說法,是「在有錢階級中的一種確確實實的恐怖統治」。[7]
對上海資本家來說,國民黨統治的第一年是一個意想不到的災難。誠然,資本家透過和蔣的結合在上海挫敗了共產黨控制的工會。
但是,作為中國最強大的經濟財團,上海資本家卻未能把它的經濟勢力轉變為政治力量。他們在 1927 年以前十年中在上海所享有的不受政治控制的局面,因國民黨近似「恐怖的統治」而突然結束。當然,外國租界當局反對國民黨政權剝奪商人權利的做法,但它們所能做的,至多只能是為實業界人士提供一個愈來愈軟弱和虛幻的避難所——而且,租界當局面臨著國民黨挑動的越來越強大的民族主義壓力時,他們幾乎處於自身難保的境地。
此時,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成為國民政府理直氣壯地敲詐勒索商人的利器。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發出禁止購買日貨的布告,並在 1927 年 6 月 28 日組織「反對日貨大同盟」。
民眾關心日本出兵山東是完全正當的,上海市黨部卻把拒購日貨當作榨取上海商人更多捐款的方便手段。「反對日貨大同盟」利用這種檢查權在所有商人階級──從百萬富翁到小店主中,以「幫助日本帝國主義」的罪名,進行勒索罰金和敲詐。公共租界邊界設置了一些木籠,貼著「出租給洋奴的木籠」的條子,以恐嚇公共租界的商人。[8]

國民黨故意煽動民眾的反日情緒,是中日矛盾激化的原因之一。
1927 年之後,與其他商界人物一樣,榮宗敬被迫與國民政府合作,曾歷任南京國民政府工商部參議、中央銀行理事、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等職務,但這些職務都是象徵性的,無法影響政府的經濟政策。
南京畢竟不是上海,南京與上海的心理距離遠遠大於地理距離。美國學者卜睿哲(Richard Bush)指出,在南京,「掌權的並不是資產階級,因為商人基本上被排斥在政策制定的核心之外」。
美國學者傅士卓(Joseph Fewsmith)指出:「南京政府時期的商人組織(以及其他中間團體),其作用不是向政府上傳輿情,參與國是,而是政府控制社會的工具。」法國學者安克強(Christian Henriot)亦指出:「在國民黨以黨治國政策下,市黨部極力擴張黨權,一切納入黨的意識形態,運用軍事的﹑政治的和思想的手段干預經濟活動,這是工商界和市黨部頻起紛爭的根本原因。」[9]
總而言之,「四.一二」清共之後,中國的資產階級「既沒有控制,也沒有影響過南京政府」,南京政府代表著資產階級的利益是一個長期謬種流傳的神話,左派和共產黨是這一傳說的製造者,而蔣介石也故意營造此一假象。[10]

官僚資本主義陰影下的百年家族何去何從?
站在大政府主義的角度看,國民黨南京政府幾乎是成功的。他們採取的策略分成兩部分:對於銀行家,他們通常收買或委任官職,將其納入政府系統中;對於工業性企業家和流通領域的商業企業家,則以高稅收來層層剝削。
1928 年,南京政府推出生產整理稅;1929 年和 1933 年,又推出針對生產和貿易型企業的關稅修正案。[11]高額的稅負讓很多企業難以為繼,榮氏企業在 1934 年面臨擱淺的危機──被迫繳納的新稅收高達 1500 萬元,即便是經營之神也難以承擔。榮宗敬呼籲政府減免稅收,否則只能「停機歇業,坐以待斃」,但政府不做任何回應。
武漢紗廠向財政部長孔祥熙提出新稅讓企業陷入困境時,孔居然痛罵紗廠跟政府搗亂:「有困難,你們為什麼不想法子克服?成本高了,你們為什麼不讓它降低?」[12]

宋子文及南京政府多次試圖利用榮氏企業的困境而將其吞併。1934 年,南京政府實業部提出《申新紡織公司調查報告書》,認為「申新如今已資不抵債,榮宗敬信用已失,如果仍以他為中心,無法維持」。
實業部長陳公博盤算由財政部撥款 300 萬接管申新,變申新為國有企業。榮宗敬憤怒地反駁説,「實業部想拿 300 萬元來奪取我 8、9 千萬元的基業」,無異於蠶食鯨吞。
他給行政院長汪精衛寫信説,「平心而論,組織不健全,管理不妥善,無可諱言;但豈有無組織、無管理,而可創辦 21 廠,奮鬥 3、4 年者?」同情榮宗敬的實業部商業司司長張翼后感嘆説:「可憐大王幾被一班小鬼扛到麥田裡去。」[13]榮氏子弟對官商經濟一直非常警惕,千方百計地抵制「官商化」。[14]
抗戰爆發後,日本佔領上海,榮宗敬避居香港,憂憤過度,一病不起。抗戰勝利後,政府本該為民營企業的發展創造良好的制度條件,卻有帶頭發國難財,以民營企業為案板上的魚肉。
國共內戰期間,蔣介石派蔣經國到上海「打老虎」,以反貪汙為名,將很多代表性的民營企業收歸國有,榮家再度成為犧牲品。
1948 年 9 月 4 日,榮宗敬的兒子榮鴻元以「私套外匯、囤積居奇」的罪名被捕,在提籃橋的特種刑事法庭上當庭放聲大哭。榮家請章士釗等三位名律師承接此案,榮鴻元還是被關押了 77 天,11 月 18 日開庭,宣判六個月監禁、緩期兩年。獲釋後的榮鴻元元氣大傷,不久就攜大部分資金撤離中國,去了香港,後來又前往北美和南美定居。

1946 年,榮德生在上海遭遇一次離奇的綁架,拿出 50 萬美金才獲釋。這是一起警匪勾結的綁架案,綁匪的汽車是向淞滬警備司令部副官處借的,綁匪就是第三方面軍第二處處長毛森的手下。幕后策劃者為新任國防部保密局局長的特務頭子毛人鳳。[15]
破財消災,但人為的災難綿延不絕。1949 年 4 月,國民政府監察院以「侵佔公有財物」、「不計調換折扣的耗損,侵蝕利己」等罪名起訴榮德生的兒子榮毅仁,指責他將霉爛的大米賣給政府,導致東北戰場的失敗。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5 月 25 日,上海地方法院公開審理榮案,也就在這一天,解放軍攻進了上海城。
綁架案和莫須有的刑事案,讓榮德生父子對國民黨政權徹底絕望,他們選擇留在共產黨中國。當時的「十大資本家」,有九家舉家遷徙,有的赴美或赴歐,有的去香港,有的跟隨蔣介石去台灣,唯獨榮德生執意留下。
國民黨的失敗,治理經濟的失敗甚於戰場上的失敗。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沒有不失敗的。南京政府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型,表現在企業史上,是政府官僚和企業家階層的市場化結合,這可以稱之為官僚資本主義或者權貴市場經濟。
這種經濟局面,是晚清官商結合傳統的又一次歷史呈現,是中國這個強大的官僚集權國家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一次變相構建,表面是市場經濟,實質是官僚主義。
中國的經濟史和企業史一直深陷在這種官僚主義的窠臼之中,至今仍未走出來。這種經濟史的面相所帶來的最大弊端,其一是官僚的腐敗不可抑制,其二是企業家的創新活動受到抑制。因此,市場的發育緩慢,政治的新秩序不能出現,中國的現代化轉型不斷被拉長,直到二十一世紀,仍然不得要領。[16]
去國的人,未必能繼續過花團錦簇的生活;留下的人,則必定要遭遇千刀萬剮、乃至滅頂之災。當時,30 出頭的榮毅仁對共產黨的治理能力頗為懷疑,他曾說,「共產黨軍事 100 分,政治 80 分,經濟打 0 分」。此話一度流傳甚廣,後來也成為其「反黨」罪證。

1956 年,中共以公私合營為名消滅私有經濟。1 月 10 日,毛澤東南下到上海申新棉紡織印染廠視察,對榮毅仁說:「你是大資本家,要帶頭。現在工人階級當家作主了,老闆換了。」
榮毅仁當即代表上海工商界集體向毛保證,要在 6 天內實現上海全行業公私合營。他對一班老臣說:「社會主義是大勢所趨,不走也得走。只要接受改造,大家都會有飯吃有工作。」由此,榮家發展了半個世紀的產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變為國家所有。
對於榮毅仁的「識相」,新政權當時給予一定的回報:國務院副總理陳毅稱榮毅仁為「紅色資本家」,並以上海市前市長身份,安排他出任有名無實的上海副市長一職,以此籠絡資本家階層。
然而,既然有資本家之原罪,在此後中共的一系列政治運動中,榮毅仁根本不可能全身而退。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發,榮毅仁作為「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被徹底打倒。他被安排在全國工商聯機關食堂的鍋爐房運煤和打掃所有的廁所,他還經常遭批鬥,食指被紅衛兵打斷。其獨子榮智健則被下放到極其偏遠的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改造,每天和民工一起抬石頭,挖土方,搬機器設備,苦不堪言。[17]
毛澤東時代結束後,鄧小平上臺,倡導「改革開放」。許多資本家(或資本家子女)東山再起,榮毅仁也「出土」,「當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再度成為中國經濟界的重要人物。[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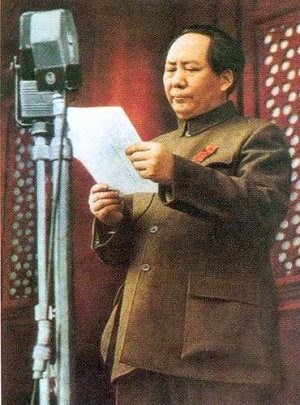
然後,「商而優則仕」,成為雖然無實權、但面子上極為風光的國家副主席──這是近代以來商人在中央政府擔任的最高職位。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中國經濟和政治制度的進步──中國今天的經濟體制與 1949 年之前何其相似:清末官督商辦企業,南京時期的半私營商社和鄧時代社會主義中國的企業,100 年來,並沒有什麽進步。
清末以來的商人家族,像榮氏家族這樣延續 4 代、長達百年之久的,屈指可數。1978 年,榮毅仁受國家之命,組建中信公司,意在向國際融資。幾乎就在同期,他的兒子榮智健放棄了清華大學的研究職位和家人,獨自去香港闖蕩。1986 年,榮智健加入香港中信,出任總經理。[19] 2002 年,榮智健登上中國首富的位置。
然而,與祖輩一樣,榮智健仍無法擺脫時代及環境的限制:2006 年,他因投資外匯巨虧而辭去中信泰富集團主席之職。2014 年 9 月,香港證監會起訴中信榮智健,為「炒匯案」4500 位股民討賠償,榮智健幾乎身敗名裂。

百年榮氏家族,跋涉於陰影與陽光中,至今仍未找到一條坦途──不是因為他們不努力,而是中國沒有西方的制度環境。
若無民主政治和自由經濟這兩翼,中國的前景必定不容樂觀。中國經濟表面上看欣欣向榮,實際上仍深陷於國家資本主義的泥沼中,稍有風吹草動,便人心惶惶,富豪們紛紛「用腳投票」。[20]
正如研究中國經濟史的學者蘇小和所論:「無論是洋務運動時代的國進民退, 1927 年民國南京時代的國進民退,還是 1949 年之後更大面積的國進民退,包括 2008 年的國進民退,幾乎都發生了大面積的企業家海外移民的現象。
一代代的政府重負已經把企業家們壓得透不氣來,政治制度和經濟史秩序已經完全無法給企業家們提供一種確定性的制度環境,企業家無法繼續經營,只有一種辦法,這就是放棄中國市場,移民海外,成為一代代海外華人企業家群體。
從經濟史和企業史雙向敘事的中期角度看,國進民退的模式是無以為繼的,當民間社會完全凋敝之後,當企業家的市場自治完全退出之後,整個國家終於失去了發展的動力。」[21]
未來的中國,如何才能出現 1927 年之前的榮宗敬那樣的白衣傲世卿相的商人?若當代榮宗敬浮出水面,就標誌著中國的經濟模式大致走上了正軌。
[1]穆藕初(1876 —1943):上海人,民國企業家、棉花專家。1909 年,赴美留學,獲農學碩士學位。回國後,在上海創辦德大紗廠、厚生紗廠,並在河南鄭州創辦豫豐紗廠。引進科學管理制度,創辦棉種試驗場。1927 年,當選上海總商會臨時委員會執行委員。1928 年後,任國民政府工商部常務次長和實業部中央農業實驗所籌備主任。
[2]楊旭:《榮氏兄弟:一代大實業家創業風雲錄》。
[3]傅國湧:《大商人:追尋企業家的本土傳統》,頁118。
[4]白吉爾:《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一九一一—一九三七)》,頁310。
[5]白吉爾:《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一九一一—一九三七)》,頁260。
[6]帕柯斯·M.小科布爾:《上海資本家與國民政府:一九二七—一九三七》。
[7]帕柯斯·M.小科布爾:《上海資本家與國民政府:一九二七—一九三七》。
[8]帕柯斯·M.小科布爾:《上海資本家與國民政府:一九二七—一九三七》。
[9]帕柯斯·M.小科布爾:《上海資本家與國民政府:一九二七—一九三七》。
[10]法國學者白吉爾敏銳地發現,關於國民黨政權是資產階級政權,或為資產階級服務的錯誤說法,是由中國本身引起的。對於那些希望將中國的發展與馬克思主義原理密切聯繫起來的共產主義理論家來說,他們很願意確定有一個買辦、官僚或封建地主的資產階級的存在;而對於蔣介石政權來說,則希翼提供一幅與其利益最相符合,並且對它恰如其分的圖景,以便獲得西方的同情和財政上的支援。毛澤東的中國通過宣揚建立一個純朴、節儉和友愛的理想社會而吸引了西方左派和激進派的注意。與此完全相同的是,蔣介石的中國也通過不恰當地賦予自己以資產階級的特徵,說服和吸引了歐美的民主人士。因此,在上述兩種情況裡,毛氏和蔣氏運用各自的手法,成功地造成了人們對中國現狀的無知。白吉爾:《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一九一一—一九三七)》,頁310-311。
[11]蘇小和:《倒退的民國》,未刊稿。
[12]傅國湧:《大商人:追尋企業家的本土傳統》,頁88。
[13]傅國湧:《大商人:追尋企業家的本土傳統》,頁94。
[14]早在 1934 年,榮德生的大兒子榮偉仁就在一封信中披露了家族擔憂:“政商合辦之事,在中國從未做好,且商人無政治能力策應,必至全功盡棄。” 1945 年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大興國營事業,將很多日商大紗廠合併為國有的中國紡織建設公司,榮德生以老資格實業家的身份向政府上書説:“日本紗廠接收後,全部改為國營,亦是與民爭利,以後民營紗廠恐更將不易為也。若論國家經濟,統治者富有四海,只須掌握政權,人民安居樂業,民生優裕,賦稅自足……若措施一差,誤入歧途,雖千方百計,終難平穩。因知富強非難事,只在用之當與不當耳。能用民力,不必國營,國用自足。不能使用民力,雖一切皆歸官辦,亦是無用。因官從民出,事不切己,徒然增加浪費而已。余近見政府措施孽謬,有失民心。”
[15]傅國湧:《大商人:追尋企業家的本土傳統》,頁158。
[16]蘇小和:《倒退的民國》,未刊稿。
[17]吳曉波《榮家百年》,經濟觀察网,http://www.eeo.com.cn/observer/special/2009/04/30/136463.shtml。
[18]法國學者瑪麗·白吉爾曾經回憶過一個細節:1979 年 9 月的一天,她坐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辦公大樓裡,等待一個重要官員的接見。她看到:“這位官員從門外進來,後面跟著五六個隨行人員,從他的外表看,似乎要比其六十三歲的實際年齡年輕一些。他身穿一件直領、貼袋的中山裝——這是中國官員慣常所穿的服裝,但他所顯露的那種靈活、步姿和舉止,卻使我驟然聯想到美國商人。他插在胸前口袋的鍍金鋼筆和戴在手腕上的百達翡麗手錶,以及腳上穿的義大利皮鞋,就足以使人意識到,這位官員非同尋常。”跟白吉爾見面的這位官員就是榮毅仁。
[19]作為一個大型國企集團中的核心人物,榮智健的個性張揚,作風西化,與李嘉誠等本地富豪的勤儉(或刻意假裝勤儉)形象大為不同,引來不少「揮金如土紈絝富豪」的議論。
[20] 2018 年 9 月,“資深金融人士”吳小平在社交媒體上發文稱:中國私營經濟已完成協助公有經濟發展的任務,應逐漸離場。很多人並不知道吳小平是誰,但此文在社交媒體引發恐慌。中共喉舌《人民日報》罕見發文安撫民營企業家:“國家支持民營經濟發展,是明確的、一貫的,而且是不斷深化的,不是一時的權宜之計,更不是過河拆橋式的策略性利用。……在當前的形勢下,企業家群體更應該不為流言所動,相信國家政策的穩定性,踏踏實實把民營經濟辦得更好。”此文反倒更讓人產生此地無銀三百兩之聯想。早在 2010 年,中國最大電商阿里巴巴老闆馬雲就表態稱“只要國家需要,隨時準備把支付寶獻給國家”;2017 年,中國第二大電商京東創始人劉強東也表示,“突然發現其實共產主義真的在我們這一代就可以實現”。他們並不是像榮宗敬那樣靠自己的努力在自由市場經濟環境中崛起的,他們自始至終都是太子黨的馬前卒,他們的言論比榮宗敬更“謙卑”。
[21]蘇小和:《倒退的民國》,未刊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