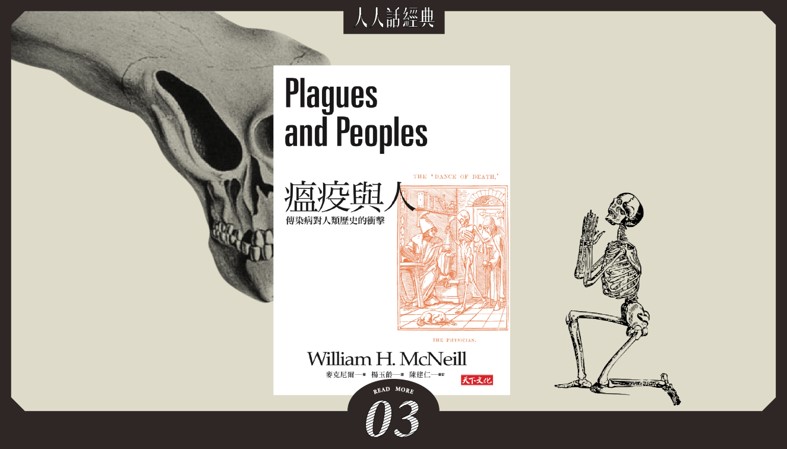西吉貝爾特與布倫希爾德的聯姻
西元 566 年春天,奧斯特拉西亞王國的法蘭克國王西吉貝爾特(Sigebert I)與西哥德人公主布倫希爾德(Brunhilda)結婚,並在梅斯的宮殿舉辦婚禮。從義大利趕來法蘭克王國的詩人萬南修福多諾(Venantius Fortunatus)為祝賀而寫的詩歌傳承至今,以下介紹開頭的部分:
接在這段詩之後的是一百一十九行的祝婚歌。維納斯與邱比特祝福兩人的婚姻,太陽神照耀婚禮舞台,妖精們紛紛獻上美麗的花朵。
就格式而言,這首充斥著羅馬多神教與基督教色彩的詩,算是古典文化的餘韻,也只會在古代過渡至中世紀的時期出現,後續的墨洛溫王朝再也沒有能寫出這類詩的詩人,萬南修福多諾也因這首詩得以活躍於墨洛溫王朝。

六世紀中期之後的法蘭克社會繼承了古典時代教養也接受了基督教倫理,在這層意義上,或許也是六世紀的墨洛溫社會被視為「過渡期」的原因吧。不過在此要特別注意的是這場聯姻本身,尤其是促成這場婚姻的因素,而不是過渡期這個特徵。
萬南修福多諾的詩雖然有提到布倫希爾德的「嫁妝」,但僅以「她領受了名為美麗的帝國做為嫁妝」稱讚嫁妝有多麼美侖美奐。不過就法國歷史學家布魯諾.杜梅吉爾(Bruno Dumézil)的調查,在都爾的額我略的《歷史十卷》與其他史料中都可以發現她帶著大筆嫁妝嫁給了西吉貝爾特。
從西吉貝爾特國王統治了長期隸屬於西哥德人的塞文地區阿利斯提烏姆這點來看,這塊地區應該是布倫希爾德從父親處繼承來的「嫁妝」(faderfio)。西哥德人原本就沿用羅馬法,女兒出嫁時父親必須給女兒嫁妝。西哥德國王讓公主出嫁時,通常都會附帶奴隸或僕人做為嫁妝;若辦得更奢華點,財產除了衣服、寶石飾品這類動產與奴隸,還包含土地。
此外,布倫希爾德與西吉貝爾特成婚之際,也從丈夫手上收到許多禮物。這些禮物的內容與分量目前沒留下直接記述,但間接的記述卻不少。在動產方面,王妃離開盧昂時,將五個包裏交給該處主教普里提克塔都斯(Prætextatus),據說其中有兩包裝滿了「貴重物與各類裝飾品」,總價值應超過三千索利都斯。另一包則裝有二千索利都斯的金幣。
目前已知的是,普里提克塔都斯從其中一個包裏取出金絲織帶後,將絲帶切成小段分送給想驅逐國王的人們。一般認為,布倫希爾德擁有非常龐大的財產,其中有許多是西吉貝爾特送的。除了這些動產,這位王妃也在漢斯與科隆擁有許多土地,我們可將這些土地視為王的賞賜。
若從日耳曼人的習俗來看,西吉貝爾特在成婚時送給布倫希爾德的禮物稱為「晨禮」(morgingab)。這是丈夫在成婚後第二天清晨送給妻子的禮物,後世將這個禮物解釋成「處女的對價交換」。可見這場西哥德公主與法蘭克國王的婚 姻同時遵守了羅馬法與日耳曼法。
一如羅馬帝國全盛時期史學家塔西佗所述,羅馬法與日耳曼法在結婚送禮的習俗完全相反,日耳曼人認為「嫁妝該由丈夫送給妻子,而不是由妻子帶給丈夫」(塔西陀,《日耳曼尼亞志》)。那麼到了中世紀, 法蘭克國王國的結婚贈禮又是如何處理呢?
「晨禮」與結婚贈禮
進入中世紀之後,不再採用羅馬式嫁妝,也就是父親直接送女兒禮物,而是由新郎/丈夫間接贈予新娘/妻子禮物,這樣的禮物稱為「聘禮」(meta/metfio)。不管是直接或間接贈予,這些財產都用於經營婚姻生活,鞏固兩國邦交,避免妻子被休或是被家暴。
當時可能適婚男性比適婚女性來得多,所以才形成這種由丈夫贈予妻子的社會習俗,但目前尚無足夠數據針對中世紀初期進行統計。放眼其他婚後住在夫家的例子,由新娘帶著嫁妝成婚的方式雖是主流,卻仍無法解釋上述的現象。
剛才已經提過,在羅馬帝國由新娘帶著嫁妝成婚是慣例,但在四、五世紀時,新郎通常會在婚前給新娘聘禮或聘金,而且從四世紀末開始,羅馬皇帝還要求聘禮與嫁妝必須「等值」。
由此可見,當時新郎免不了得提出聘禮。這類聘禮很容易與日耳曼的「晨禮」混為一談。但其實,是由於這種婚前贈送的聘禮被君士坦丁大帝定為「新娘禁欲的對價交換」,才因此與象徵「處女的對價交換」的晨禮畫上等號。
當丈夫贈予妻子禮物的方式在法蘭克時代普及後,就很難追溯這項傳統究竟屬於羅馬社會還是日耳曼社會,也很難釐清羅馬式嫁妝習俗到底被保留多少,因為記錄結婚禮品的證書通常都是由丈夫寫給妻子的。結婚時的贈予在中世紀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教會行規也多次提到「沒有聘禮就不可結婚」。
既然有這類贈予,婚姻才得以正常化,那麼當然就有不正常的婚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近親婚與綁架婚,兩者都是源自日耳曼人的習俗。不過隨著研究發現,這類婚姻也是羅馬社會的傳統之一。
禁忌的婚姻(一)近親婚
本段引自《歷史十卷》七卷三章。安布羅修斯與盧普斯這對兄弟是都爾市民,維達斯提斯是住在同一區或在普瓦捷壞事做盡的居民。都爾的額我略之所以將這段歷史視為「傳言」,一來是因為無法確定這是事實,再者是維達斯提斯娶了自己的堂姐妹,同時也是安布羅修斯妻子的女人。額我略的字裡行間充滿了批判,因為在當時,這種堂兄妹結婚是教會法判定違法的近親婚,而維達斯提斯是個羅馬人。
近親結婚在羅馬人社會不算新鮮事,所以從羅馬時代就以法令禁止,不過最近的研究卻發現,墨洛溫時代的近親婚也被視為是日耳曼社會的傳統。六世紀拜占庭史學家普羅科匹厄斯的《戰史》(De Bellis)提到,在圖林根地區,兒子與繼母結婚是「代代傳承的習俗」;教宗額我略一世(Pope Gregory I,590~604 年在位)也禁止盎格魯人與堂姐妹、繼母與結拜姐妹結婚;法蘭克人社會也能看到與繼母或嫂子結婚的例子。

因此在墨洛溫時代,主教們透過主教會議履履禁止近親婚姻,即是想讓日耳曼人停止具有異端色彩的家族祖先祭祀,改以基督教的方式祭祀。
不過先前提到的學者查理.烏布爾認為,這種理解必須從根本重新檢視,因為在墨洛溫社會的日耳曼人之間幾乎看不到堂兄妹結婚的例子,通常是羅馬人才會如此。此外,從古典時代晚期的證據也發現,這種堂兄妹結婚的情況在羅馬人社會相當普及,被視為是強化菁英家族勢力或避免財產外流的手段。
若將範圍限縮至墨洛溫王室的婚姻,最常見的就是兄弟死亡、未亡人由其他兄弟迎娶的例子,這也是最能與禁忌的近親婚比擬的情況。舉例來說,克洛維之子克洛泰爾一世(Chlothar I)在哥哥克洛多米爾(Chlodomer)去世後,娶了嫂子貢迪奧克(Guntheuc),但這是為了接收克洛多米爾的王國。
王室的近親結婚通常帶有政治目的,也是為了避免王室財產外流。財產就是結婚的籌碼,與多神教的習俗或信仰無關。
不管是羅馬人還是日耳曼人,親屬間的近親結婚情形尤其嚴重。過去的人類學者不斷討論這種亂倫禁忌的問題,卻一直沒有釐清禁止的理由與目的,此時期的史料也沒有任何與遺傳學有關的敘述。
從墨洛溫時期的史料來看,近親婚被禁止的原因在於「保持血統純淨」,但這是否與血統具有某種神聖性質有關,目前尚無定論,但一般認為,禁止近親婚是為了促進各家族或各地區能進一步交流。由此可見,羅馬人與日耳曼人對於近親婚的態度沒有明顯差異。漸漸地,與外族通婚就在西歐成為主流。
禁忌的婚姻(二)綁架婚
所謂的綁架婚,是未經女方雙親同意就與之結婚。雖然也有失敗的例子,但到底是怎麼綁架的,《歷史十卷》記載了相關的小故事:
由於《薩克利法典》將綁架婚定為違法行為,因此要綁架新娘得盡可能掩人耳目,通常選在晚上。此外,考量到新娘的家族會抵抗,所以夥同幫手闖入新娘家中的例子並不罕見,新娘的家族也會動用武力抵抗並保護自家女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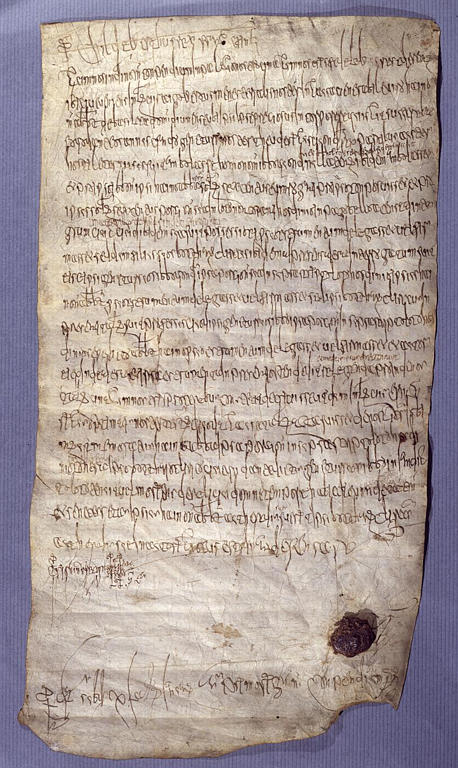
綁架的結果非常多種,其中之一就是上面這種遭到新娘家族抵抗而失敗的例子。另外當然也有成功的例子,此時就可能比照羅馬皇帝的做法,由國王允許這場綁架婚。此外,新娘本人同意結婚、但父母親不同意的情況下,也常導致這種綁架婚發生,此時犯人通常會支付新娘家人賠償金,事後也得以與新娘結婚。
日耳曼法典通常是以賠償金解決紛爭為前提,但也有將犯人打入奴隸階級的案例,每個王權做出的判決都不一致,墨洛溫國王甚至下過執行死刑的命令。
綁架婚之所以被歸類為「日耳曼習俗」,是因為羅馬法律禁止這樣的行為,但日耳曼人認為這是一種私奔,有時甚至將這種綁架婚視為合法。羅馬法律規定,就算新娘本人同意,也必須與犯人同處死刑;日耳曼法律則不同,只要犯人能於事後得到女方親屬同意,就能合法結婚。
換言之,綁架婚是否成立,端看事後有無得到女方親屬同意,所以綁架婚才被歸類為「日耳曼習俗」,而非「羅馬習俗」。
由此衍生的其他解釋,例如綁架的「幫手」被解釋成隨從,也就是跟在主人身邊、擁有自由身分的日耳曼戰士團。不過在其他例子裡也發現,這些戰士會幫忙綁架奴隸,譬如巴德基希魯的妻子之所以斥退庫帕那群人,全拜自己的隨從頑強抵抗所賜。
這不禁讓人想起過去君士坦丁大帝規定只要發生綁架婚,新娘的乳母以及與綁架有關的奴隸全都要處以極刑。《西哥德法典》(Lex Visigothorum)也有為了綁架新娘而出借奴隸的紀錄,甚至有時候,新娘家裡的奴隸也會幫忙犯人綁架新娘。
日耳曼人當然是利用隨從綁架新娘,但就綁架的方法而言,日耳曼人與羅馬人應該大同小異。

這套書,讓你完全扭轉世界史的理解方式
創新橫切式敘事 多空間的比較視野 著眼關鍵年分的全球史通述 打破單一國族語言,展現跨地域的相遇和連結
西元378年,人類歷史的轉捩點────────
西方:日耳曼民族大遷徙,西羅馬帝國步向滅亡,古典時代晚期開啟,拜占庭世界的建立
東方:西晉滅亡漢人南遷,北方游牧民族進駐,多元混雜的南北對立之勢
這一年,由西羅馬皇帝親自率軍出征日耳曼民族的亞德里安堡戰役,最後以大敗收場。至此,羅馬再無力抵擋北方「蠻族」進入帝國,過往的榮光也一去不返。差不多同一時代,由「五胡」之一的氐族人苻堅率軍攻打東晉的淝水之戰,最後也無功而返。至此,分裂成南北兩塊的對立局面逐漸定型,中國同樣無法重現大一統盛世。兩場戰役都宣告了帝國秩序的崩解,各地呈現分裂之勢。
這是一個時代的結束,也是一個時代的開始。在亂局之中,各地人們共同面對這個新的世界,從掙扎中求生、摸索,並逐漸萌生出新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