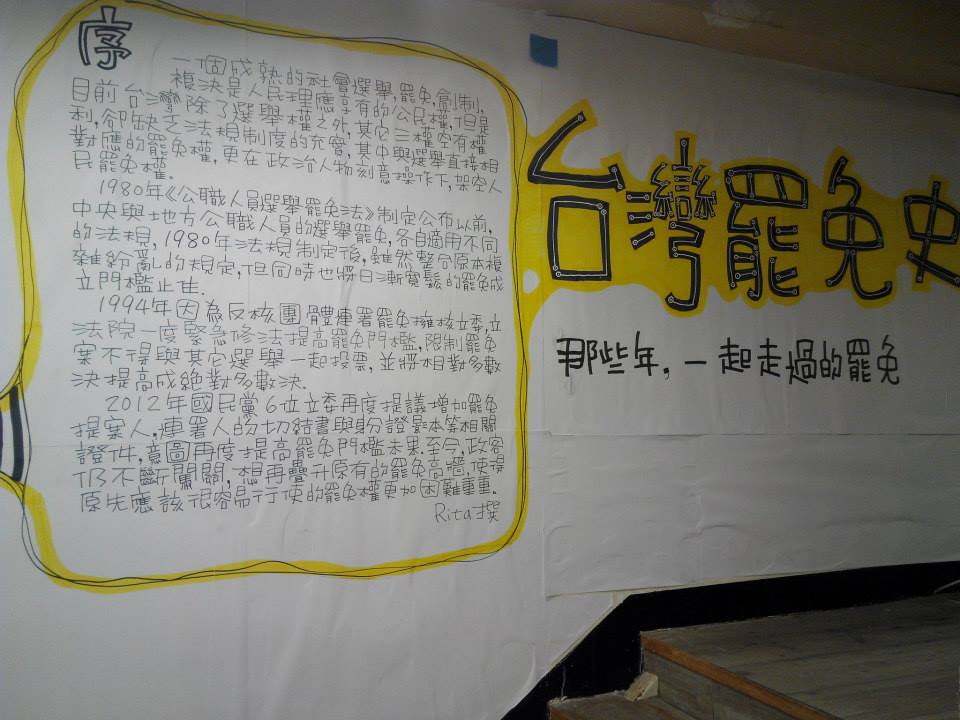走不出的刑求室惡夢
蘇建和艱難地大口喘息,在嗆咳的隙縫間嘗試吸入一點空氣。他的手被綑綁著,臉上覆著警察強蒙上的濕毛巾。因為缺氧,他的眼前逐漸暗了下去,卻又突然因下體激烈的疼痛驚醒過來。是電擊棒,他太熟悉這樣的痛楚,因為他們已反覆電擊過他許多回,他甚至可以聞到自己胯下燒焦的氣味。他不知道,如果自己再不認罪,接下來等著他的,會是何等酷刑…………。
他再度驚醒,這次是真的醒了過來,一身汗濕。
這麼多年過去了,蘇建和還是反覆在夢中回到那個冰冷的刑求室。
在一個平凡無奇的夏日午後,警察找上了門,強行將蘇建和帶走。他們說他是殺人犯,媒體跟著說他是殺人犯,最後連法官也說他是殺人犯,於是他便是殺人犯了,那年他只有 19 歲,一夜之間成了階下死囚。
一開始,蘇建和不懂為什麼他的朋友王文忠會對檢警說自己參與了殺人案,但後來他學到,嚴刑拷打能讓人說出任何施暴者想聽的話。警察不相信一樁殘忍的犯行是一人所為,用刑求逼得嫌犯供出了不存在的同夥。連蘇建和自己,也從一次次痛苦的否認犯行,到最後被折磨得只能在檢察官所寫的認罪自白書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
蘇建和逐漸明白,自 1991 年夏天起,不論他是否願意,這個惡夢將注定如影隨形,日日夜夜,長成他肉體與靈魂的一部份。
不在場卻被指證的「共犯」
1991 年 3 月 24 日的凌晨,新北市汐止區一對夫婦吳銘漢、葉盈蘭在家中遇害。他們年幼的兒女晨間不見父母起床,便到父母的房間找人,竟然發現房門反鎖,門縫下流淌出腥紅的鮮血。這對夫妻在睡夢間遭到砍殺,一共身中 79 刀,屋內錢財則不翼而飛。警方在現場找一把菜刀、少許毛髮,以及三枚血指印,其中兩枚指印模糊難辨。
循著吳銘漢薪水袋上唯一一枚可辨認的血指紋,警方在 8 月 13 日找到了正於海軍陸戰隊服役的王文孝。王文孝很快坦承了自己的犯行,他因為積欠電玩賭債,夜半潛入鄰居家中盜財,不料吳銘漢與葉盈蘭先後驚醒,慌亂之下他揮刀將二人滅口。
他說,是他一人所為,但是檢警不罷休。
他們不相信兇殘砍殺 79 刀的命案,竟沒有共犯。經過漏夜的偵訊與審問後,王文孝改口了,供稱弟弟王文忠、謝廣惠、「黑點」與「黑仔」也參與犯案。後來,他又推翻前面說法,表示沒有謝廣惠,但「長腳」也在。於是「長腳」蘇建和以及劉秉郎、莊林勳接二連三被逮捕。
沒有人能確切知道,偵訊王文孝的過程究竟發生了什麼,筆錄又經歷過何等刪改,只知道在蘇建和被逮捕的當下,官方的筆錄中甚至還沒有出現他的名字。
在王文孝坦承犯行的五個月後,便迅速地執行死刑。自始至終,蘇建和與其他兩個被捲入的「共犯」,都沒能得到與王文孝正面對質的機會。
除了王文孝幾度反覆的供述與自白,兇案現場找不到蘇建和三人的鞋印、指紋或其他痕跡,法律上卻已認定他們的殺人與強姦罪行。一審、二審、最高法院撤銷原判發回更審、更一審、更二審,四年過去了,司法一次又一次採信屈打成招的自白,他們獲判一個又一個死刑。1995 年 2 月 9 日,最高法院駁回更二審後的再一次上訴,判決定讞,蘇建和等三人各判二個死刑,褫奪公權終身。
在水泥與鐵柱層層堆疊的死牢裡,蘇建和試著伸手,卻搆不到一點窗外的陽光。他提起筆,寫下了一封封遺書,給律師、給父母,還有因他飽受異樣眼光的弟弟。他甚至在給父親的遺書中說,他要到閻羅王那裡告狀去,因為在人間,他已別無他法。
歷經二十餘年終於沉冤昭雪
1995 年 2 月 10 日,蘇建和死刑定讞的消息已經見報。蘇建和、劉秉郎與莊林勳的母親淚眼婆娑,她們都穿了一身墨黑,做好身為母親能有的最壞打算,但她們還是盼望著:「律師,還能有什麼最後的辦法嗎?」
母親們焦急的眼淚,觸動了許文彬律師心中的一個念頭:非常上訴,或許會是最後的一線希望。許文彬撥了通電話給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陳涵,希望與陳涵會面,陳涵同意後,他便與蘇案的主要辯護律師蘇友辰一同前往造訪。
已經判決確定的刑事案件,除了可以透過再審程序外,如果審判有違背法令之處,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能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上訴。檢視過蘇建和案的卷宗之後, 2 月 20 日,陳涵向最高法院提起第一次非常上訴,卻遭到了駁回,陳涵又陸續提了第二次、第三次。後來陳涵說,他當時無從得知蘇建和等人是否絕對蒙受冤枉,但身為司法的重要守門人,他確知蘇案的法院審判程序有多處違反法律規定。每一個站在被告席的人,都應該有權利接受不偏不倚的調查與審判。
後來的纏訟過程,繁複得超過想像。三次非常上訴都遭到駁回,蘇友辰律師不屈不撓,一再提起再審、抗告,每次都遭到最高法院的駁回。直到 1998 年,王文忠出面指控警方刑求,坦承自己是在逼迫下編出其他共犯,並指證目睹蘇建和三人也都是因酷刑簽下了不實的犯罪自白。
.jpg)
全案於 2000 年開啟再審後,又經歷了改判無罪(2003 年),檢察官上訴、再更一審死刑(2007 年),鑑識專家李昌鈺返臺作證表述案件應是一人所為,再更二審無罪(2010 年)、檢察官再度上訴、2011 年再發更審,最後在 2012 年,再更三審宣判無罪,依《刑事妥速審判法》規定,檢察官不能再上訴,全案才終於真正了結。

歷經 21 年,蘇建和終於在法庭上洗刷了自己的冤屈,但是一晃眼,來到了不惑之年,逝去的青春,永遠留在那方小小的牢房,不會再重來。
共犯自白的角色
若非因為舊有的刑事訴訟法對「共犯自白」於刑事證據法中的角色定位不明,蘇建和案,或許不會痛苦纏訟多年。
過去法院認為,共犯的自白內容只要不是對自己有利的陳述,當中如果涉及指控別人(其他共犯)犯罪,這種指控不需要具結(發誓沒有說謊,否則願意接受偽證罪處罰)、也不需要像普通證人一樣需經過檢、辯雙方的交互詰問釐清事實等的調查程序,只要共犯是出於自願的陳述,且也有其他補強證據證明真實性的話,就可以當作是證明其他共犯犯罪的證據。
而在蘇建和案中,定罪三人的關鍵證據,就是共犯王文孝的自白陳述,曾指控蘇建和三人共同犯案,但這樣的指控,卻沒有給蘇建和三人對質詰問的機會,就成為了證明被告犯罪的證據。
因此,雖然過去刑事訴訟法第 156 條第 2 項已規定:「被告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是否與事實相符。」但共犯王文孝的自白陳述,既然被法院承認為證據,自然就可以作為與蘇建和三人的自白互相補強的關鍵證據,換言之,雖然法院不能僅憑蘇建和三人的陳述就認定三人有罪,但若王文孝自白中,也指證蘇建和三人參與犯罪,且也有其他補強證據證明王文孝說法真實性時,法院就可以憑著蘇建和三人與王文孝的自白,判決蘇建和三人有罪。
但是,共犯的自白因為不用具結、不負擔偽證罪責任,被告也無法直接與咬出他的共犯對質詰問,以辨明證詞真偽,就可以做為被告犯罪的證明,這實在是不太合理。因此,在 2003 年 2 月,刑事訴訟法第 156 條第 2 項修改為:「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是否與事實相符。」特別明訂共犯的自白,也不能作為判決被告有罪之唯一證據、也刪除了刑事訴訟法第 186 條第 3 款共犯不用具結的規定。
2004 年 7 月,大法官針對另外一件聲請案作成釋字第 582 號解釋在該解釋中,大法官認為刑事被告詰問證人的權利,受憲法第 16 條訴訟權及憲法第 8 條正當法律程序所保障,因此共犯陳述應該要進行「人證」的調查程序,也就是說,共犯指證被告也參與犯罪的話,這樣的指證也需要經過具結與被告的交互詰問等調查程序後,才能作為證明被告犯罪的證據。
對蘇建和等人來說,法院對共犯自白的證據評價演變,不只是紙上的法理進步而已,已幾乎是生與死的距離。
蘇建和的重生之路
那天步出法庭以後,歲月逐漸安靜了下來,但是蘇建和不確定,有生之年自己是否還能找回真正的自由。現在的他不喜歡拍照,習慣在搭火車的時候低下頭,有好一陣子,他不知道怎麼用「正常」的表情與人應對。
有時候他會想像,沒有發生這件事的另一種人生會是什麼模樣,或許他會有一個妻子、有兒女圍繞,甚至或許,父親還能在他的身旁。
蘇建和的父親為了他奔走多年,時常發送文宣陳情至深夜,同時還得在夜半晨起經營自助餐店,累壞了身體。可惜父親來不及看到蘇建和無罪釋放,便先一步離開了。有一回父親到獄中來看他,當時的蘇建和滿心怨忿,日日詛咒刑求他的警察,父親問他,如果有天在路上踢到一顆大石頭,心裡會怎樣想。
「罵他啊!這麼缺德,在路邊放石頭。」蘇建和回答。
父親說自己過去也是這樣的,但在救援他的過程中,遇見了全力相助的人權團體,看見了其他也在司法中被錯待的人們,現在的他若有餘裕,會想辦法移開路上的石頭,避免下一次磕碰、下一個人再受傷。
父親離世後,蘇建和才漸漸明白他說的話。出獄後,他走進當年救援他的台灣人權促進會、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與人本教育基金會,從志工做起,而後先後全職在台權會與司改會工作。蘇建和曾經對生命絕望,但是在漫長的歲月裡,紛沓湧至的救援與關懷,像暖風徐徐吹進冰封之地,讓他願意重新相信人。因為司法始終是為人而生,只要有人願意改變,就能越來越好。
這一路,絆腳的石子太多,過去有人為他搬開了許多,今後,他願意繼續為後人清道。
(本文為司法院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