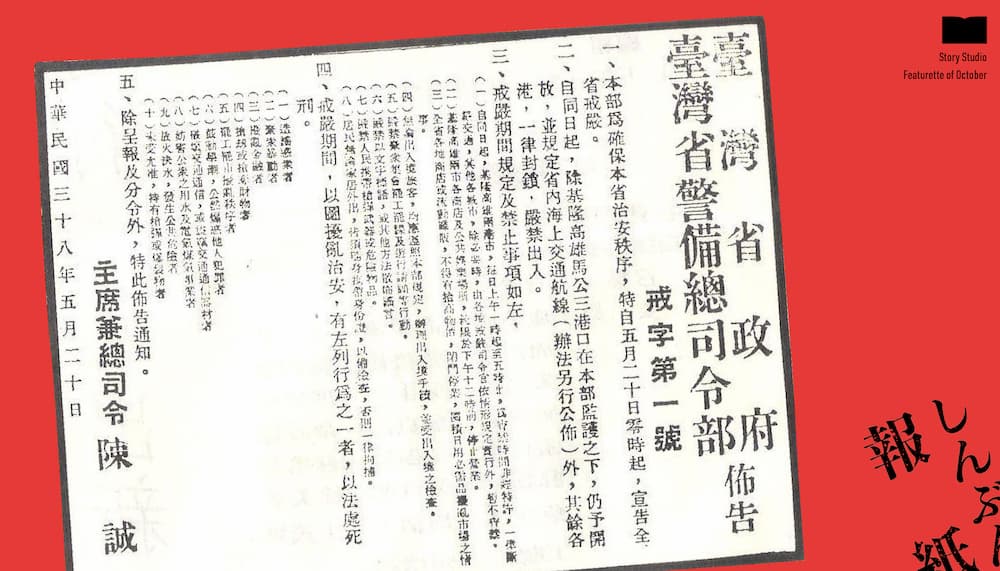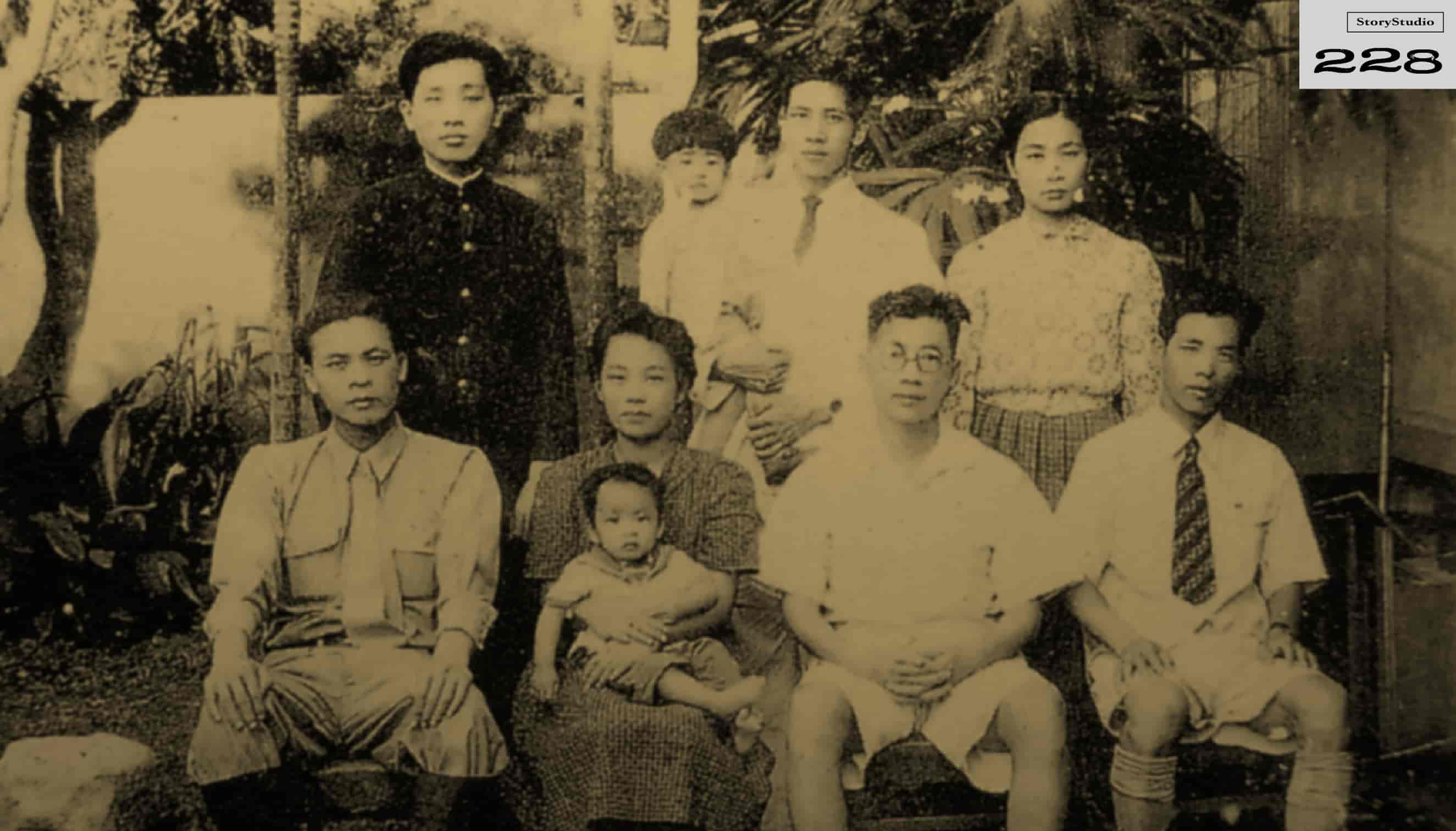一、李永得:絕不妥協的硬骨記者
我是在高雄事件發生之後才進入自立晚報。我第一次感受到戒嚴肅殺的氣氛,是美麗島事件之後的第一次選舉。當時美麗島軍法大審的辯護律師張俊雄宣布參選高雄立法委員,我去專訪他。那是他的第一次選舉,也是我第一次訪問政治人物。
我寫了一千五百字的報導。刊出後,第二天警總就來找我了。我那時候涉世未深,不知道害怕。我只覺得奇怪,這些東西有什麼好問的,這跟警總有什麼關係。
自稱警總的人約我喝咖啡,一直問我為何要訪問張俊雄?有哪些訪談內容沒寫出來?我後來才知道,這些人只是探聽情報,警總必須有報紙沒有登出來、但對他們是有價值的情報。也就是說,警總也要有自己的「獨家」,也要交差。
我另一次感受到肅殺氣氛,已經是當自晚總編輯的時候了。那時我寫了一篇社論,標題是:「軍人氣慨?」我批評參謀總長郝柏村兩件事情:第一個是郝柏村參謀總長任期過長破壞制度,培養郝家軍;另一個是,他常常說要憲兵介入社會治安的事務。我認為這是軍事統治的前兆,跟民主發展不相容,所以我就寫了六百字的社論。
當天晚上,國防部長鄭為元在新聞局裡開記者會,那也是我印象中有史以來,國防部長第一次開記者會。國防部大肆抨擊自立晚報這篇社論,說六十萬官兵絕對無法接受,說自立晚報污衊國軍。
我記得非常清楚,那天晚上吳樹民(前自立報系發行人)剛從美國回來,準備接任自立晚報發行人。我跟吳豐山(時任社長)在兄弟飯店幫他接風。吃到一半知道國防部在開記者會,我們當場就討論該如何回應。當時吳樹民說:「幹回去啊!」我們當場就擬了三點聲明,反擊國防部。
之後自晚連續兩個禮拜,每天都接到兩個麻袋的明信片,如雪片般飛來,全是國防部發動國軍官兵寄的。每張明信片內容都差不多,說我們是「匪報」,說我們污衊國軍官兵,六十萬大軍絕對不能接受,一麻袋一麻袋地寄過來。對此,我印象深刻。我才寫了六百字,就引起國防部這麼大的反應。
跟蹤監控無所不在
戒嚴時期跑新聞的最大收獲,就是學會擺脫竊聽和跟蹤。
當時和情治人員玩的遊戲是:用盡方法讓情治人員無功而返。我們都打公共電話,因為報社電話一定有人監聽;甚至在國民黨中央黨部採訪,被採訪對象也不許我打他桌上電話,因為他的電話一定也被監控了。
大陸六四事件之後,黃德北(曾任自立晚報政經研究室研究員,現為世新大學社發所所長)為什麼在大陸被抓?因為他沒有當過戒嚴時期的記者。他用旅館的電話跟民運領袖王丹通電話,這一定會被監控的。
後來我和徐璐大陸行的時候,我用飯店電話跟香港記者通電話。我一聽就知道有人在錄音,錄音有時候是沙沙聲,有時候是喀擦一聲。當時我聽到喀擦一聲,就開玩笑跟那個記者說:「我們暫停一下,因為他們正在換錄音帶。」我故意讓他知道,我知道有人在錄音。結果電話立刻恢復清晰,直到訪談結束。
當時情治單位甚至直接安排人在報社裡監控新聞。每家報紙都知道,有些是「明樁」,有些是「暗樁」。各報國際組會有一位新聞編譯當明樁,代替警總監控國際新聞。早期,這個編譯拿的薪水還是警總付的。
警總為什麼最擔心國際新聞?因為所有國內資訊都被控制,國際資訊則無法控制,所以外電進來時要經過這些人把關。報社堅持要登什麼外電,他們就會通報警總。直到解嚴之後,國際新聞的監控才解除。
暗樁則會在印刷廠或排字房。很多稿子落版之後,我們都要仔細去盯,因為稿子可能會在最後關頭被換掉。我們常常發現,怎麼報紙還沒印出來,警總的電話就來了。雖然不知道是什麼人,但是知道一定有人通報。
有時候還會被搞鬼。比如「中央」政府變成「中共」政府。有可能是排版工人失誤,因為撿字時「央」、「共」這兩字很接近;也有可能是暗樁故意整我們,偷偷搞的鬼,給我們搞麻煩。雖然不能確定,但是有可能。雖然警總盯得很厲害,不過我們也有一套防衛機制。例如敏感的文章都要再看一次,確認有沒有文章被搞鬼,再送上印刷機。
「機場事件」難忘經驗
一九八六年發生機場事件。當時我是自晚政治組記者,總編輯是顏文閂。許多人事前就知道許信良要闖關回臺,大家都在現場等待。當時中正機場的外圍群眾聚集,也有很多警備跟鎮暴車。
碰到這種大事的時候,自晚幾乎所有記者,不要人指派,都會到現場。現場範圍很廣,資訊不流通。所以我們都會分工,人員不能太集中;有人負責在車上互相聯繫。到了傍晚就出事了,很多警方噴水車朝群眾噴有顏色的水,讓群眾誤以為是刺激性的東西,引起一陣騷動。
記者最有力量的是客觀的報導,而不是評論。當時一篇「現場目擊」,冷靜客觀地描述現場畫面:是鎮暴部隊先激怒群眾,才暴發機場事件衝突。這跟所有其他報紙報導「暴民攻擊警察」的角度是不同。
那天傍晚的機場,風很大,海風冷冷地吹,有秋天的肅殺之氣。很多群眾走來走去,有的坐著,有的等著。警察來回穿梭,鎮暴部隊停在某個角落。那種畫面讓我印象非常深刻。對一個記者來說,能夠看到這些畫面,真的很難得,也覺得有一點點幸運。
機場事件確立了自立晚報客觀公正的地位,不只在晚報領域,也有政治上的影響力。因為所有報紙中,只有自晚敢報導警察先激怒群眾。報紙出來後,我們有很大壓力,但是自晚影響了那一次立委選舉的結果。
當時所有黨外候選人大量複印自晚發送。原本自晚的發行量只有十三萬份,但是因為機場事件,加上複印的發行量達到一百多萬份,有非常關鍵的影響力,讓選舉結果和預期的不同。那年黨外大勝,很多人都是第一次選上立委。
歷史性大陸行的偶然

在自晚政治組待了四、五年後,我擔任政治組召集人;後來顏文閂離職到《自由時報》,陳國祥接任自晚總編輯,我則接任陳國祥的政經研究室主任。
到了一九八七年七月解嚴,政府準備開放大陸探親。我們認同這樣的政策,也認為這是突破性的報導題材。當時所有報紙都蓄勢待發,想拔得頭籌進入大陸採訪。在報業競爭和政策趨勢下,我們以最快的速度決定派記者到大陸採訪。不過,當時報社只有我和徐璐剛好有簽證,可以隨時出境,所以吳豐山就派我們去。有人說,自晚怎麼選了一對金童玉女去大陸,其實只是歷史的偶然。
當年九月九日,我接到報社指示到大陸採訪,十一日就搭飛機前往日本轉機。怕走漏消息、官方阻撓,所以整個過程完全保密。直到我們上飛機,報社才發布消息。國民黨立即發布通緝令,要在日本攔截我們,把我們抓回來。瞬間,震驚全世界媒體。
我們先到日本,向中國大使館申請中國大陸簽證。中國大使館的人也不敢立即給我們簽證。後來我聽中國方面知情人士說,當時東京大使館與北京總共來回打了十七通電報請示後,北京才拍板定案,同意我們的採訪簽證。
我們瞭解,這趟歷史性的大陸採訪,步步危機,必須小心謹慎,包括退路,也就是進入中國之後,要從那裡回到「自由世界」的路徑,也必須預作安排。否則,一旦發生危險,又無退路,將會任人宰割;若被抓、被關,全世界將沒有人知道我們的下落。
從中國出來有日本、新加坡、香港三條路徑。我們分析評估最安全的路,是從日本原路回來,因此要離開日本之前,要向日本申請「再入國」簽證。沒想到,日本政府不知是受到中國還是臺灣的壓力,竟然對我們的申請再三刁難,一副不想給的樣子,氣得我們撤回申請。換言之,我們沒有退路,就要進入中國採訪了,一切就阿彌陀佛保平安了。
飛往大陸時,心情有點矛盾。小時候,我們被教育成大陸是神州,是故鄉,我覺得好像要回到非常熟悉的地方。可是再認真想想,大陸其實是很陌生的。我驚覺教育的可怕就在這裡。到了北京,現場大概有一百位記者,全世界的媒體,臺灣的、香港的、日本的、歐洲的,所有駐北京記者都在。我第一次見過這麼大陣仗的記者會。當時嚇死了,我才三十幾歲,而且我本來就內向害羞,不擅於面對那種公共場合。

大陸採訪三不原則
進大陸採訪時,我和徐璐思考:我們代表在臺灣成長的一代,要展現出什麼姿態來表現臺灣和中國的不同。
我們的採訪原則就是三不。第一,不接受招待。如果非不得已要接受,一定要接受我們回請。第二,不採訪官方。因為我們定位非常清楚,就是要讓臺灣讀者瞭解大陸社會的狀況。最好的採訪地方就是馬路、市集、人民大食堂,所以我們絕不採訪官方。第三,官方不得干涉我們的採訪對象。
另一個很重要的原則是,為了表現在自由環境下長大的骨氣,在中國,我絕對不批評臺灣,也不批評國民黨。如果要批評,一定是批評共產黨,這才能顯示臺灣人不一樣的地方,這就是骨氣。
在大陸採訪,隨時要提防中共官方的跟蹤和監視。我們在國民黨時代跑新聞已練就了這一套。第一,我絕對不搭在門口排隊的計程車,一定到一百公尺以外的路上攔計程車。第二,到了旅館大廳要特別警覺。
有一天我們去採訪方勵之(當時中國民主運動領袖)。當天早上我一到大廳就感覺有問題。大廳上有些人站著,有些人坐著,有個共通點就是,很多人都在看報紙、看雜誌。當時我只感覺有點問題,但也不確定,所以就興起好玩之心來測試看看。
我們走到另外一條街攔計程車。我們很警覺,一直注意後面有沒有人跟。後來司機跟我說:「方勵之的家在前面十字路口右轉就到了。」我一聽就說:「司機你先不要彎,你直走,然後煞車。」結果後頭的車子果然一直跟著我們往前走,後來我們一煞車它就衝過去了。然後我們回頭,看到那輛車子緊急煞車又回頭,我們百分之百確定那臺車是跟監著我們的。可是他們比我們更強的是,我們一到方勵之家門口,那臺車子早已經在門口等著了。
在大陸採訪時,我已經不怕被抓了,因為全世界媒體都在看著我們。我們在東京開記者會就是要吸引更多注意,我如果被抓,全世界會來找我們。
其實國民黨幫了大忙,因為我們一出發,國民黨就發出通緝令,全世界媒體興趣就大了,都派記者過來了。當自晚發布新聞、各國媒體都在找我們的時候,我們還故意躲在東京不露面,讓大家以為我們兩個人不敢出來。等到突然露面的時候,全世界的媒體都來了。有了全世界的關注,我就不怕到大陸去會忽然消失了。

二、李旺台──對抗威權體制的南部記者
記得一開始當地方記者,我最大的夢想是:「希望有一天稿子可以在二版、三版被登出來。」現在看起來很好笑,但是當時我就是以這個夢想為目標,逼自己不斷努力。後來,我到臺北當特派員,稿子被放在二、三版已經是稀鬆平常的事了。
地方記者做久了很容易習慣環境,變成記者公務員。二、三十年過去了,記者與地方各派人馬的關係愈來愈好。這種關係會讓記者習慣享受各種方便,日久成為「地方有力人士」,卻因此失去了動力。
在臺北當特派員的時候,我必須不斷與國民黨文工會主任聯繫。有時是透過黨政記者,有時是親自出馬。當時很重要的任務就是瞭解哪些是敏感的新聞?國民黨中央黨部的態度為何?然後回報南部的總編輯:文工會告知我們什麼可以登、什麼不能登。
此外,在臺北那段期間,當時黨外領袖黃信介、康寧祥都在臺北,有很多東西可以報導。我們那時候與中國時報或聯合報也沒什麼兩樣,只是比臺北的兩報三臺多寫了一些黨外人士的活動和談話而已。不過如此,卻成為英雄。每回我們的記者出去採訪,對方都會說:「這個是尚勇的記者。」
有次康寧祥在桃園演講,約兩、三萬人包遊覽車去聽,現場如痴如醉。我回來後寫兩、三百字,再加上一張小小的圖片。這在現在是司空見慣,但是在當時是不得了的大事。不過也因為這樣,最後我被貼標籤:「寫黨外新聞的記者。」最後連國民黨中央黨部都跑不進去,只好改派其他同事去跑。我因為這樣就被「封殺」,可見當時臺北新聞圈是一個很閉塞的環境。
親身見證美麗島事件
我擔任採訪組副主任時,發生了「美麗島事件」。原本是社會線負責跑這條新聞。當時在高雄的新聞圈裡,美麗島事件並不算政治新聞,所謂的「政治新聞」就是國民黨的新聞。當天,我不是為了採訪新聞,而是因為與黨外人士陳菊、周平德等熟識,聽說他們會來參加遊行,就決定去與他們碰個面、打個招呼。這是出門前的想法。
我和立法委員李慶雄、周平德一開始在旁邊聊天,聊著聊著不知不覺跟著他們走進遊行隊伍中。在隊伍裡固然聽到看到的都是和自己相同的理念,但偶爾心中會浮現這個問句:「記者可以參加政治活動嗎?」這是我記者生涯裡第一次面對這種掙扎,第二次是後來與司馬文武一起編黨外雜誌《八十年代》的時候。
那天原本是世界人權日的遊行活動,沿途不斷喊著口號,每個人手牽著手、情緒高昂。每次大家熱烈喊口號時,我總是在心中有點遲疑。我吃了幾年新聞飯,把記者這一行看得太認真。那時候一邊是李慶雄抓著我,另一邊是周平德,我們手拉著手。我心裡卻不斷自問:「我的身份可以這樣做嗎?」後來我告訴自己:「我今天不是來跑新聞的,是來看朋友的。報社有派攝影記者和文字記者來。」我當時是用這個理由合理化自己的行為。
遊行隊伍一直走,沿途繞成一個四方形,最後又走回警察局分局前,事情就是在那裡發生。當場的確有衝突,但當時遊行的民眾都很驚訝:「為什麼會打起來?」我當時身在遊行隊伍中,很明顯看到有一群圍事的黑衣份子,他們都不是遊行的人。
那些黑衣人突然冒出來,手上拿著鐵槌、木棍,二話不說就開始毆打憲警。那是在憲警開始整隊向群眾進逼之後發生的。一整排的憲兵踢正步「趴趴趴趴」,威嚇效果很大,之後就噴催淚瓦斯,噴得到處都是,我們退都來不及,瞬間怎麼突然有一群人衝上去!這些人都不是我們遊行的人,當時我看見的問題就在這裡。這就是美麗島事件的真相。
臺時換稿報導真相
遊行結束後,眼睛仍有催淚瓦斯留下的酸澀感,我大約九點才回到報社。跑警政線的記者已經將稿子寫好放在我桌上了,要等我看過後再交給採訪主任。
看完這篇稿子,我認為不是這樣的。這篇稿子就像一個凶殺或群毆案現場的寫法,而且是從警方的角度去寫。與當晚發生的事件,本質上完全不同。我瞭解這是政治事件,就向主任說:「這篇稿子不能用,我要自己重寫。」我飛快地寫完稿子,寫稿時不斷壓抑自己內心激動的情緒。
採訪主任看完我的稿子,馬上交給總編輯。沒一會功夫,總編輯便跑去社長室,可見當時他們看見我的稿子是驚訝的。其實我寫得非常克制,是平鋪直述的。過了好一會,社長跑到我的位子,看著我的眼睛說:「你的眼睛怎麼紅成這樣?是瓦斯噴的嗎?」「要不要先去吳老闆的診所洗眼睛?」我那時候只掛心這篇稿子,倒是沒有太在乎眼睛的不適。
最後社長決定暫時將我的稿子擱在一旁,等候黨中央指示。過了一個鐘頭,文工會居然沒有來電,大家都感到奇怪了:平時小至工廠廢氣外洩都會來電,這件天大的事件卻沒有半通電話?
為了確認「上面」的意思,報社方面決定繼續等下去,並先將那則警政記者寫的新聞排在三版(三版可以晚一點截稿)。過了午夜十二點,「上面」仍然沒有電話打來。最後一刻,報社決定換成我的稿子,並且加上當時對峙的照片。
隔天見報標題是「鎮暴部隊發射催淚瓦斯驅散人群」,這在當時是很不容易的事,因為其他報紙不敢這麼寫。要送印刷廠之前,大家還在掙扎:「這樣的新聞處理真的可以嗎?」這則新聞雖然在三版下方,但位置很明顯。標題不僅大又反白,還附上兩張照片。副總編輯開玩笑地說:「大概沒關係,三版最上方有蔣總統發表的談話全文,算是平衡,所以應該沒事吧。」這才稍微化解了眾人的焦慮。
當天回家後,我其實很害怕,我太太也很擔心。不過第二天報社一切如常,我照樣上班。這時才比較篤定「沒事了」。
國民黨的真正盤算
後來回想起這件事才瞭解到,這是一條可以大做特做的大新聞。因為國民黨中央打算利用輿論的力量,將所有的黨外精英一網打盡,並且藉此加以醜化。當時卻沒有人猜到國民黨中央的心意,只有我在無意間抓對了它的脾胃。
當我對美麗島事件的報導率先登報後,其他媒體才在國民黨動員下,從第三天開始用極大的篇幅報導美麗島事件與大審。像是中國時報、聯合報、中央日報等全國性的報紙,內容全都引導至「暴徒打人」、「非法集會」的概念上。像是施明德被追緝,報紙標題都是「暴徒施明德」。目的就是為了將他們抹黑成違法與襲警的暴民。
美麗島事件的爭執點在於,到底是「先鎮後暴」還是「先暴後鎮」?除了我,所有的媒體都傾向「先暴後鎮」。接下來的幾天,臺北很多黨外雜誌,像是《美麗島》、《大時代》均打電話來問:「那篇是不是李旺台寫的?」最後大時代全文照登,並且加上對我的訪談。
美麗島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天下午,陳菊打電話找我去周平德家吃晚餐。席間,我們看到當天晚間新聞的方向是臺北市長李登輝、省主席、各縣市議長與議員,輪流在媒體上批判這些暴徒。電視畫面盡是警總安排的橋段:新聞局率領很多美麗的歌星、明星,去醫院慰勞那些被打傷的憲警。一面倒的氣氛已經出現了!
陳菊對我說:「你看會抓人嗎?」我當時心底很篤定地認為一定會,並且跟她說當天晚上報社處理這條新聞的經過。我說:「發生這麼大的事,文工會卻沒有任何指示,這應該代表會有大動作。」
陳菊聽完一發不語、臉色凝重,粗線條的周平德則大聲說:「安啦!沒事啦!」但是客廳裡籠罩著一股無力且憤怒的沉重感。
迷失在輿論迷霧中
當時主流媒體誤導美麗島事件,把所有黨外人士都醜化為暴徒。最不可思議的是,當時的新聞局長宋楚瑜特地邀請國外記者採訪美麗島大審。顯然國民黨中央不僅扭曲事實,還準備在輿論上用力。
在全國媒體都排山倒海地報導美麗島事件時,國民黨政府也將新聞操作成「暴民先暴」,官方不得不「鎮」。每天電視上都是流眼淚、被打的憲兵,他們的母親傷心欲絕,淚訴著兒子被打得不成人形、新聞局發動影歌星去獻花給受傷軍警等等。電視不斷播報「美麗島暴徒」的相關新聞。塑造出來的氛圍,就像真的一樣。
在這種大氣氛的籠罩下,我偶爾會被帶進強大的輿論氣氛裡。那兩、三個月期間,我也感覺好像要被輿論的大潮流所淹沒,一度迷失甚至懷疑自己。遊行當晚,我並沒有使用「先鎮後暴」的字眼,只是寫下所目擊的景況。這段期間,被兩報三臺的扭曲言論與畫面衝擊後,我時常在深夜時分反問自己:「他們真的是暴民嗎?」「我之前有沒有支持錯人呢?」這種身在新聞界卻被另一股強大的輿論力量不斷撞擊的經驗,是現在許多人難以體會的。
直到名作家陳若曦在美國引用我的報導,譴責國民黨對於美麗島事件的態度,並且在事後到南部找我,對我說:「你那篇寫得很好,我有跟蔣經國說那是先鎮後暴。」這時候我才真正體會到自己那時候所做的事情是有力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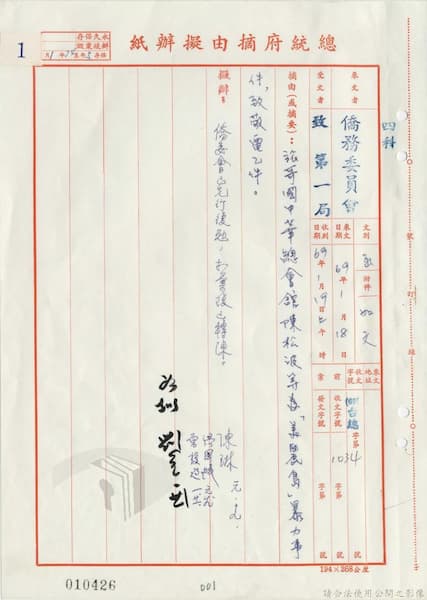
美麗島事件前後,國民黨欲強壓黨外力量的氣氛已經明顯出現。一方面培養「疾風集團」與黨外對抗,另一方面利用美麗島事件,將黨外菁英抓起來。其中大規模的媒體操作,是當時最成功的策略。
回想起來,這似乎是國民黨政府第一次如此大膽地操作。以前都是暗中抓人,抓了就送審。國民黨大規模地利用媒體作為政治整肅工具,並邀請外國記者來採訪司法大審與軍法大審。不配合的外國記者,新聞局也毫不留情地驅逐出境。但後來政局發展並不容易控制,包括海外臺灣人社團的覺醒與團結、國際社會的關切與同情,使得臺灣的政局產生了一連串的化學變化。

這群人散佈在最保守到最激進的媒體。他們在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高壓氣氛中匍匐前進,姿態多半扭曲變形,很難保持優雅好看。有的人在主流媒體內兢兢業業,有的人想盡辦法在文章中「埋地雷」鼓吹民主,有的人努力從中南部發聲,有的人深入觀察民間社會,有的人則與情治單位大玩「捉迷藏」遊戲;後人想像他們堅定勇敢,他們身處其中卻可能狼狽不堪。
他們像是在無盡的黑夜中尋找星星,對外迎向忽明忽暗的民主亮光,對內追尋若有似無的記者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