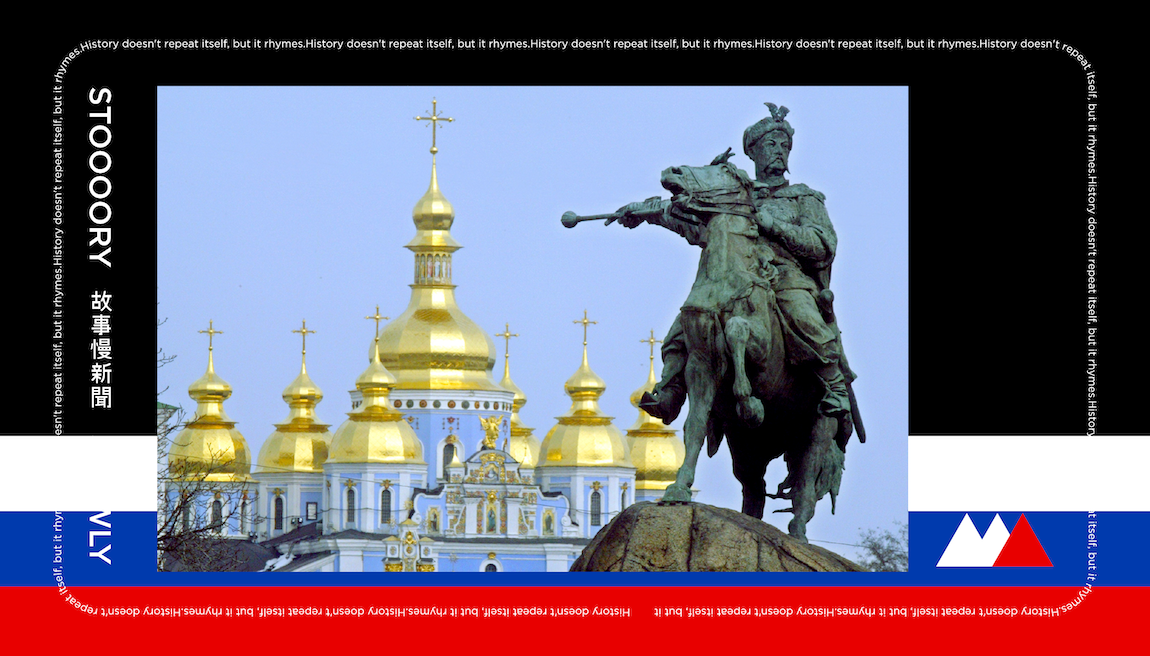他們來到獨立廣場,不再離開。而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創造一項新事物:一個民族。
無論烏克蘭政治制度有多少缺陷,在一九九一年後,烏克蘭人都覺得應該無須使用暴力就能解決政治上的爭端。若有例外,例如高人氣的調查記者格奧爾基.貢加澤(Georgiy Gongadze)在二○○○年遭到謀殺,則會引發抗議活動。烏克蘭在二十世紀見證的暴力事件不在任何其他國家之下,但在二十一世紀民間能如此和平,是一項值得自豪的成就。烏克蘭與俄羅斯不同的地方,除了能夠定期選舉、沒有戰爭,也包括有和平集會的權利。因此在十一月三十日鎮暴警察攻擊位於獨立廣場的抗議人士時,人民大為震驚。「我們的孩子」遭到毆打的消息傳遍基輔,在流下「第一滴血」之後,人民開始行動。
烏克蘭公民出於對暴力的不滿,來到基輔幫助學生。其中有一位謝爾蓋.尼霍揚(Sergei Nihoyan),是一位講著俄語的亞美尼亞人,來自烏克蘭東南部的頓巴次(Donbas)地區。這位工人表達自己對「學生、烏克蘭公民」的支持。這些人都是下意識希望保護未來,對學生來說,是因為他們害怕失去歐洲;而對其他人來說,是因為他們害怕失去這些由獨立的烏克蘭所培養的下一代。也有一些老一輩人士來到獨立廣場保護學生,其中就有「阿富汗人」,是在紅軍入侵阿富汗後留下的老兵。二○一三年十二月的抗議示威活動,與其說是為了歐洲,不如說是為了維護烏克蘭政治的正確形式,是為了「正派」或「尊嚴」。
二○一三年十二月十日,鎮暴警察第二次出動,驅趕獨立廣場上的示威民眾。消息再次傳出,這次是基輔不分各行各業的民眾,決定用自己的身體阻擋警棍。一位年輕的女商人回憶道,自己的朋友「刮了鬍子、穿上乾淨的衣服,做好在當晚喪命的準備」。

一位中年文學史家也挺身犯險,同伴有一對老夫妻、一位出版商和一位醫生,她說:「我的朋友有一位是超過六十歲的病人,而他的太太年齡也相近,站在他們旁邊,我算是相當年輕、強壯而健康(我是一個五十三歲的女人,到了這個年紀,當然很難想像該怎樣用體力打敗有武裝的男性)。我的兩位朋友都是猶太人,而我是波蘭公民,但我們攜手同行,都是愛烏克蘭的人,我們都相信,如果這些示威抗議活動現在遭到鎮壓平息,我們的生命也將失去價值。我們確實到了獨立廣場,過程不能說沒有凶險。我的朋友莉娜是醫生,她是全世界最溫柔的人,身高只有一百五十公分;我得讓她跟鎮暴警察保持距離,因為我知道她會直言不諱地告訴那些警察,她對他們和這整個情形的看法。」十二月十日,鎮暴警察無法驅離民眾。
捍衛烏克蘭的民主成就
二○一四年一月十六日,總統亞努科維奇(Viktor Fedorovych Yanukovych)溯及既往,一方面判定抗議違法,一方面也將自己使用武力合法化。官方國會紀錄有著被抗議者稱為「獨裁法」的一系列立法。這些措施嚴重限縮言論自由與集會自由,禁止根本未明確定義的「極端主義」,並要求非政府組織若取得外國資金,必須登記為「外國代理人」。引進這些法條的是一群與俄羅斯有聯繫的議員,而且就是取材自俄羅斯的法律。過程中,沒有公聽會、沒有國會辯論,甚至沒有實際投票:用的是舉手表決而非電子投票表決,而且舉起的手其實不到半數。但不論如何,這些法條都列入法典。示威抗議者瞭解到,如果被捕,將被視為罪犯。
六天後,兩名抗議者遭到槍殺。這兩起死亡案件,在美國或俄羅斯這兩個遠遠更為暴力的社會看來,或許很難理解在烏克蘭人心中有多大的重量。四週後,狙擊手又展開大規模屠殺,也就讓這兩起死亡個案變得小巫見大巫。而在五週後,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造成更多的流血事件,幾乎已經讓人無法再想起這些殺戮究竟是怎麼開始。但對於真正身處其中的社會而言,仍然會記得是在某些特定的時刻,犯下那些打破正派的行為。在一月的最後一週,開始有許多過去未曾支持獨立廣場抗議活動的烏克蘭公民,從全國各地大批前來。亞努科維奇手上似乎已經沾染血跡,讓許多烏克蘭人無法再接受未來由他繼續統治。

對抗議者來說,他們在這一刻體驗到自己政治社會的扭曲。這場抗議示威活動原本是為了捍衛成為歐洲的未來,但現在已經成為要保護少數烏克蘭現今的成果。而到了二月分,獨立廣場已經成為抵抗歐亞一體主義的絕望堡壘。在那之前,很少有烏克蘭人思考過俄羅斯的迴圈政治。但抗議民眾並不喜歡眼前看到的情形:各種可能性煙消雲散,而由暴力導向一個沒有未來的生活。
二月初,亞努科維奇仍是總統,而華盛頓和莫斯科對他該如何繼續掌權各有想法。有一通電話,顯然是由俄羅斯特勤局盜錄,並於二月四日洩露內容,是美國助理國務卿和美國駐基輔大使之間的通話,內容指出美國的政策支持亞努科維奇成立新的政府。這項提議並不符合獨立廣場民眾的要求,甚至可說是完全搞不清楚狀況。至少對於那些在二○一四年一月二十二日的兩起殺戮事件後,還選擇冒著生命危險待在獨立廣場的人來說,亞努科維奇的執政已經畫下句點。一項調查顯示,只有 1% 的抗議者願意接受讓亞努科維奇繼續執政。二月十八日,國會開始討論,希望找出妥協方案。但在隔天就發生血腥衝突,亞努科維奇政權也更無延續的可能。
從二○一三年十一月至二○一四年二月,獨立廣場有超過一百萬人獻身在那冰冷的石板地上,這段歷史與那些失敗的鎮壓企圖歷史,絕無法相提並論。在過去,烏克蘭境內的示威者難以想像會發生流血事件;只有在流血事件後,才讓美國和歐洲注意到這個國家;而流血事件也成為莫斯科的藉口,派出俄羅斯軍隊,造成更多流血事件。於是,有一股強大的誘惑,要恢復烏克蘭過去在外界看來的形象,敘事的軌跡就跟隨著子彈的軌跡。

對於那些前往獨立廣場的人來說,示威抗議是為了捍衛那些他們認為仍然可能的事物:自己國家的美好未來。他們之所以在意暴力,是因為那代表他們難以容忍的事物。暴力總是短暫爆發,可能只有幾個片刻或是維持數小時。然而,民眾來到獨立廣場的時間不是只有幾個片刻或數小時,而是幾天、幾週、幾個月,他們的堅忍剛毅可以看出一種新的時間感、新的政治形式。那些人之所以能在獨立廣場留這麼久,唯一的理由就是找到新的組織方式。
在廣場上打造新政治
獨立廣場的事件帶來四種政治形式:公民社會、禮物經濟、志願福利國家,以及獨立廣場友誼。
基輔是一個雙語首都,這在歐洲並不常見,而在俄國與美國更是難以想像。對歐洲、俄國與美國人來說,很少認為日常使用雙語是政治成熟的表現,而會想像烏克蘭既然會說兩種語言,必定是分成兩群、分成兩半,「烏克蘭裔」和「俄羅斯裔」的行為各有不同。而這就好像在說「美裔美國人」就該投票給共和黨一樣,比較像是摘要呈現某種政治,這種政治以種族來為人定義,讓人感受到的是永恆的哀苦,而不是未來的政治。在烏克蘭,語言是一種光譜,而不是一條一分為二的線。就算是一條線,也是在人的心中、體內穿梭來去,而不是將人群之間畫出區分。
在獨立廣場上的烏克蘭公民,他們口語用的語言就像日常生活的作為一樣,會視需要切換烏克蘭語與俄語。這場革命的起點是一名記者,他會用俄語指示其他人鏡頭擺放的位置,接著在鏡頭前用烏克蘭語發言。他著名的臉書發文(「光按讚沒有用」)用的是俄文。在獨立廣場上,使用哪種語言並不是什麼重要的問題。正如抗議者艾文.蘇仁科(Ivan Surenko)記得的,他以俄文寫道:「獨立廣場的群眾對語言問題很寬容。我從來沒聽到有人爭議這件事。」在一項調查中,獨立廣場的群眾有 59% 認為自己的母語是烏克蘭語、16% 認為自己的母語是俄語,以及 25%則認為兩者都是自己的母語。這些人會依據情境的需求,切換不同語言。在獨立廣場設立的舞台上,發言的民眾講的是烏克蘭語,因為那是政治的語言。但接著,等到這位發言民眾回到人群中,可能就是以俄語和朋友交談,這正是一個新政治民族的日常。

這個民族的政治重點在於法治:首先希望與歐盟簽署聯盟協定之後可以減少貪腐,接著希望避免法治在國家暴力浪潮下徹底消失。在調查中,抗議者多半表示「捍衛法治」是他們主要的目標。這裡的政治理論很簡單:國家需要公民社會引導它走向歐洲,也需要歐洲引導它遠離貪腐。而等到暴力開始,這種政治理論就會以更詩意的形式表現出來。哲學家莫洛狄米爾.雅莫蘭柯(Volodymyr Yermolenko)寫道:「歐洲也是隧道盡頭的一盞燈。你什麼時候才需要這樣的燈?當周遭都一片漆黑的時候。」
與此同時,公民社會就是處在一片黑暗當中。烏克蘭人的應對方式,是開始成立各種無關政黨的橫向網絡,正如抗議者伊霍.比洪(Ihor Bihun)所說:「沒有固定的成員資格,也沒有階級高低。」從二○一三年十二月到二○一四年二月,獨立廣場的政治及社會運動都只是由各種臨時的組織領導,完全出於個人的意願及技能。這裡的基本概念認為自由也是一種責任,因此廣場上的活動組織包括有教育組織(圖書館與學校)、安全組織(自衛隊〔Samoobrona〕)、外交事務組織(獨立廣場理事會)、暴力受害者援助與尋找失蹤親人組織(Euromaidan SOS)和反宣傳組織(InfoResist)。
抗議者安德烈.邦達(Andrij Bondar)回憶道,自我組織等於是挑戰烏克蘭這個功能失靈的國家:「獨立廣場上出現一個烏克蘭公民社會,具備令人難以置信的自我組織及團結,發展一片蓬勃。一方面看來,這個社會的內部是分化的:意識形態、語言、文化、宗教和階級都有不同;但另一方面,有某些基本的情感因素把大家聯合起來。我們不需要你的許可!我們也不打算向你要什麼!我們不怕你!一切就由我們自己來。」
獨立廣場的經濟是一種「禮物經濟」。如娜塔利亞.史特瑪赫(Natalya Stelmakh)的記憶,一開始幾天,基輔人民展現無比的慷慨:「短短兩天,其他志願者和我從基輔一般民眾手中收到的烏克蘭幣,已經高達相當於四萬美元。」她還記得,有一位老人家堅持把自己每月領的養老金支票捐出半數,她試著婉拒,但未能成功。除了現金捐贈外,民眾還提供食物、衣服、木材、藥物、有刺鐵絲網和頭盔。如果在當時到訪,會很驚訝地發現在表面的混亂當中其實有著深刻的秩序,乍看之下是無比的熱情好客,但骨子裡則是完全出於自發的福利國家。波蘭政治活動人士斯瓦沃米爾.謝拉科夫斯基(Sławomir Sierakowski)感到印象深刻:「走過獨立廣場,會有人提供你食物、衣服、睡覺的地方,以及醫療服務。」
二○一四年初,在高達數十萬人的示威抗議者中,絕大多數(88%)是來自基輔以外。只有 3% 的人是政黨代表,只有一三%是非政府組織成員。根據當時的調查,幾乎所有的示威者(大約86%)都是自行決定參加,以個人、家庭或是一群朋友的形式到場。他們參與的是藝術策展人瓦西爾.契瑞潘(Vasyl Cherepanyn)所謂的「肉身政治」(corporeal politics):不再只是緊盯著螢幕,而是讓自己身處於其他人之中。
像這樣在日益增加的風險中耐心抗議著,產生「獨立廣場朋友」(Maidan friend)這種概念,指的是因為同甘共苦而讓你產生信任的人。歷史學家雅羅斯拉夫.赫爾扎克(Yaroslav Hrytsak)就談到一種結交新朋友的方式:「在獨立廣場上,你就像是一個像素,而像素總是要成群結隊才能有作用。群體多半是自發組成:你或你的朋友碰到某個你或你的朋友認識的人;而你遇到的那個人也不會只有自己一個人,他或她身邊也會有他或她的朋友。於是,你們就開始走在一起。有一天晚上,和我同行的是一群貌似八竿子打不著的『佣兵』:我的哲學家朋友,以及一位我認識的商人。他身邊還有一個眼神哀傷、身材瘦小的男人,看起來像悲傷的小丑,而我後來才知道他還真是專業的小丑,組織一個慈善組織,服務癌症病童。」
烏克蘭的公民以個人身分來到獨立廣場,加入各種新的機構組織。一方面實踐著肉身政治,一方面也是讓自己身陷險境。正如哲學家雅莫蘭柯所言:「我們面對的這項革命,是人們把自己當作禮物。」人們常常把這視為一種個人的轉變,是一種非比尋常的選擇。赫爾扎克和其他人回憶法國哲學家阿貝爾.卡繆(Albert Camus),想起卡繆所言,反抗就是選擇寧死不從的那個時刻。獨立廣場的海報上,引用美國國父班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在一七五五年的一封信:「若為了一時的安全,就放棄最基本的自由,這種人既不配得到自由,也不配得到安全。」
有一群烏克蘭律師就這樣日復一日在獨立廣場上待命,有個標示寫著「獨立廣場律師」。如果民眾遭到國家的毆打或其他虐待,就能向他們提報不當行為,開始訴訟程序。俄羅斯政治哲學一直有一項問題,連伊林也無法解決,就是「怎樣才能在專制中製造出法律精神?」;而獨立廣場上的律師或其他人,雖然並非刻意,但靠著他們這種代表法治看法的行動,就為這項問題找出解答。

一百年前,在俄羅斯帝國日薄西山的歲月裡,伊林曾希望有個法治的俄羅斯,卻無法想出這種精神要怎樣傳達給人民。他在十月革命之後妥協,認定極左翼的目無法紀只能以極右翼的目無法紀來應對。而在普丁將伊林的法律概念應用於俄羅斯的那一刻,烏克蘭人正在證明確實能夠抵抗這種專制的捷徑,烏克蘭人展現他們深愛法治的方式,就是與他人共同合作,並且願意身陷風險。
如果烏克蘭人可以透過歐洲與團結,來解決伊林所困惑的法治問題,俄羅斯人不也可以嗎?這正是俄羅斯領導者絕不允許公民發現的想法。

繼《暴政》、《黑土》、《重病的美國》之後,著名歷史學家提摩希.史奈德又一警世巨作!
當上個世紀冷戰結束之際,人們一度歡欣鼓舞迎接「歷史的終結」,相信資本主義與自由民主的全面勝利,相信未來必然會往光明的方向前進。如此天真樂觀的態度,將各種事實編織成一張幸福之網,創造出史奈德所謂的「線性必然政治」:市場會帶來民主,民主會帶來幸福,進步的法則都在掌握之中。
然而,線性政治令人懈怠,它腐蝕公民責任,培養出沒有歷史的千禧世代,讓人遺忘自由與民主曾是如此得來不易。而今二十世紀腳步已遠,但人們並沒有從殘酷歷史中學到教訓。
大謊言時代的降臨
歷史從未終結,線性政治尚未走到那美好的未來,便開始瓦解崩潰。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種「迴圈永恆政治」:國家落入被害者的循環,時間不再是走向未來的一條線,而是無止境地重複過去的威脅。在線性政治裡,人人都知道一切終將進步,所以沒有人需要負責任;在迴圈政治裡,人人都是無辜的受害者,所以也沒有人能負起責任。
迴圈政治中的政治人物,操弄情緒、製造危機,用謊言混淆事實,讓公民交替體驗著暴怒與狂喜,以現在淹沒未來。2012年的俄羅斯選舉舞弊,普丁贏得大選,卻摧毀了法治。2014年俄國入侵烏克蘭,普丁卻宣稱這是西方意圖分裂偉大的俄羅斯文明。「讓事實畫下終點,就是永恆的開始。」而現在,普丁要將這套迴圈政治出口到全世界。
我們唯一能掌握的,唯有歷史與真相
當權力扭曲事實,歷史只為政治利益服務,我們將喪失的不僅僅是過去。在迴圈政治裡,人們會逐漸喪失思考的能力,一步步走向「不自由之路」。在這個充斥各種幻象、機器人與網軍的年代裡,史奈德透過回望歷史,剖析當代全球民主最深刻的危機。
他說,唯有追求真相,才能讓我們遠離不自由的道路;唯有喚醒歷史,才能在線性與迴圈中打開一道縫隙。「如果我們能誠實面對歷史,就能看到自己在歷史中的位置,知道自己可以改變什麼、怎樣可以做得更好。於是,也就不再無意識地從線性必然走向永恆迴圈,不再走著通往不自由的道路。」在這種情況下,責任政治才得以開展,而我們也將看見自己仍能有所作為,世界仍能被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