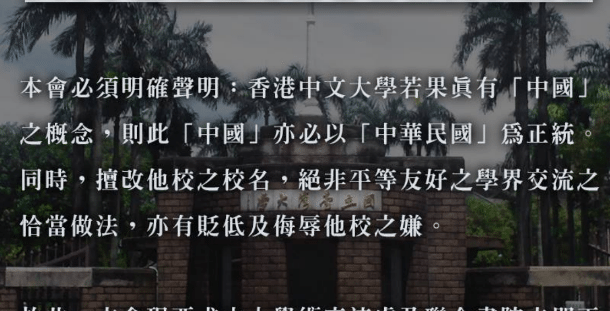當香港變成西柏林
香港抗爭陣營所作的國際遊說,非常有效地掌握了當下國際政治的主要矛盾,把香港問題放在全球政治的圖譜上,大大提升了香港抗爭的重要性,亦把運動帶領到一個新的方向。相較之下,香港政府在國際輿論上則完全落於下風。
歌手何韻詩七月九日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UNHRC)的發言,提出人權理事會應該把中國驅逐出理事會,她直接點出最主要的矛盾:中國正在侵害世界或西方社會視為核心價值的人權和自由等精神,這和西方社會的主流政治價值有所衝突。黃之鋒在九月十二日訪問柏林,爭取德國及西方國家支持香港,他將香港比喻為「新柏林」,站在對抗共產政權和專制統治的前線。
一星期後,黃之鋒、何韻詩、「中國人權」執行主任譚競嫦、學界代表張崑陽等到美國出席國會有關《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的聽證會,批評香港自由倒退、連月警暴、漸變一國一制,呼籲美國維護香港人權自由,以及盡快通過法案。十一月十二日,美參議員賀利呼籲參議院通過《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時,說:
有時在歷史的進程中,一個城市的命運可以定義整個世代的挑戰。五十年前是柏林,今天這城市是香港。

抗爭者遊說的話語,切合西方的主流核心價值,亦符合西方國家當下的現實政治需要。近年來西方民主國家逐漸注意到中國為首的不少專制國家(包括俄羅斯),在國際上擴張政治影響力,用各種方法散播反民主反自由的價值,並利用西方國家本身的自由民主環境(例如言論自由及商業自由),嘗試影響西方國家的民主體系運作,以及全球的民主發展,因而開始覺得有需要在各方面加以抗衡。
香港運動的論述自九月開始改變。香港的抗爭運動轉變為全球抵抗中國專制政體擴張的橋頭堡,因此香港的抗爭並不是單純為了自保香港一城的自由,而是代表全世界的文明社會抵抗極權擴張。以此角度看,西方社會就有道德責任聲援及協助香港。這種論述,蔡英文在 2020 年競選總統時及當選後亦有採用,同樣是把台灣定位為區域內守衛民主自由、抵抗中國專制力量擴張的重要堡壘。

這個國際化的角度令運動被重新定義,進一步面向國際。抗爭現場多了出現英文的口號「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以及面向外國的訴求口號「Free Hong Kong」。九月八日到美國領事館的遊行,有不少人手持及揮舞美國國旗,因為他們知道這樣可以吸引美國傳媒拍攝以及在美國的電視上出現,其後美國國旗在示威遊行現場出現的次數亦有所增加。
九月二十九日,本來由台灣發起聲援香港的「全球反極權」遊行,變成全球二十四個國家六十多個城市的「反極權」遊行,當日由銅鑼灣至中環的遊行隊伍中,有數十人分持不同國家的國旗前進,象徵這是和世界上各個不同國家站在一起的運動。
抗爭者亦更自覺地要爭取西方國家支持,及以西方制裁作為籌碼之一,八、九月開始有人呼籲多開英文推特帳號作國際宣傳,因為推特在西方社會中較廣泛使用(但香港較少人用)。後來圍攻理大之役,不少支持者便用推特轉發大量片段以向國際求援。

十一月二日,香港有人發起「求援國際 堅守自治」的維園集會,主旨是呼籲各國對香港爭取自由的運動施以援手,但由於警察反對集會,於是改為由一百多名區議會候選人發起在維園集會。集會開始約一小時即遭警察以武力驅散,接著警察在港島灣仔銅鑼灣一帶以水炮射擊及包抄圍捕,多人被捕,但同日世界上卻有十七個國家共四十八個城市集會聲援香港。
反之,香港政府和中國政府的國際輿論工作,顯得相當地被動和無力。中國政府對各國聲援香港言論的反應,通常都是說香港問題是中國內政,其他各國不得干涉。到了 CECC 通過人權及民主法案,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在九月二十六日的回應是:「該案罔顧事實,顛倒黑白,公然為香港激進勢力和暴力份子張目,粗暴干涉中國內政,中國對此表示強烈憤慨和堅決反對。」相對香港人的普世價值訴求,這種黨八股式的回應對西方輿論大概不會有效。
特區政府方面,大量的警暴鏡頭每週傳送到外國,已經在國際輿論上置其於不利地位。何超瓊和伍淑清曾經在九月到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發言,指摘示威者是暴徒,一小撮人不代表香港七百多萬人意見等。林鄭月娥原定九月到美國的探訪取消,又沒有主要官員針對《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到美國遊說,外訪的官員(如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長邱騰華等)都只是官式地強調香港的法治自由不變,一國兩制運作良好,經濟競爭力很好等話語,欠缺說服力和針對性。
官方發言和其後海外的報章廣告都是官樣文章,單調、缺乏設計意念和吸引力,相對於民間多樣且高質素的網上宣傳短片和廣告,官方在宣傳效應上完全落於下風,反映了與時代脫節的守舊政府,完全沒法與民間智慧抗衡。到了九月底,香港抗爭者已經在國際輿論戰中大獲全勝。
蝴蝶效應:NBA、暴雪及其他
香港的抗爭在不同層面觸發政治影響和關注,有些並非由香港抗爭者刻意發動,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 NBA 事件。
十月四日,NBA 球隊侯斯頓(休士頓)火箭的總經理莫利(Daryl Morey)在推特上發表了簡短的留言「Stand with Hong Kong」聲援香港,引來火箭班主(老闆)發言指火箭並非政治組織,莫利即刪除留言。莫利支持香港的留言被中國網民大肆攻擊,而中國籃總亦宣佈即時中止和侯斯頓火箭的合作關係,其後兩日NBA球隊在中國的表演賽轉播亦被取消。十月七日,莫利和 NBA 賽會均發表聲明無意得罪任何人,但仍招來內媒包括《人民日報》的批評,認為這並非真誠道歉。
中國的態度卻惹來美國政壇迅速和強烈的反應:議員如克魯茲、楊安澤(Andrew Yang)、卡斯楚(Julian Castro)等均公開表示美國人的言論自由應受保護,不應因商業利益而犧牲原則。NBA 總裁施華(Adam Silver)亦發言支持莫利應有言論自由,後來更透露中國曾施壓要求裁掉莫利,而他的答覆是這不可能發生,甚至連處罰莫利都是不可能的。中國國內其後自行降溫,就事件的評論迅速減少,也沒有進一步的施壓或杯葛行為。

這事件引來非常大的迴響,令很多可能不知香港發生什麼事或原本不在意的美國或全世界的籃球迷,一下子注意到香港的運動。對於熟悉近年中國政治發展或輿論策略的人來說,這類事情可說是司空見慣。不少藝人、商號或名人如果被內地官方或網民認為發表了「政治不正確」的話語,都可能招致官方封殺或網民狙擊和杯葛,嚴重影響其商業利益。
不少人為顧及中國市場,會在政治話題上噤若寒蟬或支持官方立場。NBA 在中國有數以億計的球迷,每年的電視轉播、商品銷售和市場推廣(例如球星做商品代言人)的收益極為龐大,特別是火箭隊由於當年有中國球星姚明,一直是最受中國國內歡迎的 NBA 球隊。
NBA 事件令不少美國人覺得中國的專制擴張已經威脅到美國國民和商業機構的言論自由,而言論自由是美國最核心的價值,正合美國政壇當下要抵抗中國的霸凌和專制擴張的主流,於是反彈強烈,不少政界人物和名人(包括部份 NBA 球星)質疑是否應為生意利益放棄言論自由,從而為香港的運動帶來更大的支持和同情。
NBA 事件令美國民間對香港的支持增加。有人發起在 NBA 球賽現場派發及穿上有「Stand with Hong Kong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字樣的T恤。十月十八日紐約籃網主場對多倫多速龍(暴龍)的賽事、常規賽開鑼戰快艇對湖人,以及在較多香港人聚居的主場球隊的賽事(例如多倫多速龍和金州勇士),都有數百名支持者穿起T恤聲援香港。最特別的是:整個與 NBA 有關的事件完全不是由香港抗爭者發起,卻因為中國政治運作的邏輯得到一個極有力的「助攻」。
同類的例子發生在電競商「暴雪」(Blizzard)身上。九月,國際電競比賽「爐石戰記」的階段比賽冠軍「聰哥」在獲勝後受訪時,帶上香港抗爭者裝備(防毒濾嘴和護目鏡),並高呼「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結果被遊戲母公司判罰沒收獎金及禁賽十二個月,引來不少電競選手不滿,並聲言杯葛暴雪。暴雪其後退讓為只罰「聰哥」停賽半年及發還獎金。十一月四日,暴雪總裁公開就事件道歉,但沒有取消處罰。
小結
總體上,2019 年的反抗運動把遊說西方政府(主要是美國)施壓為主要策略之一,一個重要的背景是抗爭者覺得單憑香港的力量難以影響中國政府,而抗爭者(甚至整個反對派)跟中國政府,也沒有任何的溝通或談判管道。當民眾覺得中國政府和特區政府都不會聽人民聲音,似乎唯一能令北京有所避忌、不敢強力鎮壓以至可能考慮讓步的方法,就只有借助國際社會的壓力,特別是美國的力量。
香港民意研究所在 2019 年十一月的調查反映,約 64%被訪者支持美國以《人權及民主法案》制裁警務署長,「以表明佢(他)要為所有違規濫用暴力嘅(的)警員負責」,反對的約 29%。這反映呼籲外國制裁有主流民意支持,亦反映了香港人對多月來警察暴力的憤慨。
這是香港抗爭運動策略上一個很大的改變。香港的民主運動多年來對是否遊說西方大國以政治手段支持香港民主自由,一直有路線上的分歧。部份政治領袖例如李柱銘或陳方安生一直致力到英美遊說,但不少民主派有所保留,一方面是覺得運動應該立足於香港,另一方面是害怕這會招來中國政府「引入外國勢力」、「漢奸」等指控,損害與中國政府關係,適得其反地令中國政府更加抗拒,反而不利對話或爭取民主改革。
在 2019 年反抗運動中,這方面的論述和策略完全改變,「求援國際」以及全球化抗爭被視為運動的一個重要部份,而國際社會的關注、同情及制約,被視為運動的最重要資源,原因之一應該是很多人覺得單靠香港人的資源沒可能成功,以及認定了北京要持續地打壓香港的自由、民主和自治,沒有什麼對話空間,只能用盡不同方法反抗。反抗運動亦因此積累了更多國際聯繫及組織資源,打開了一個新的政治局面。這配合了西方政界和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態度和策略改變,成為 2019 年運動帶來的最重要改變之一。

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可能制裁,對中國政府的對港政策應有一定影響。中國政府一方面要顧全一國兩制和香港作為自由城市的形象,不會動用解放軍以六四式的鎮壓解決問題,而只能倚賴香港警隊處理。在不願作出政治讓步以回應訴求的情況下,持續多月的警暴令民怨更深、政府和警察形象更負面,而驅使西方國家有更大壓力以具體措施回應香港的運動。西方可能會制裁此一因素,應該也影響了有關區議會選舉的決定。
在十一月間,不少西方國家都呼籲港府應讓區議會選舉如常進行,讓港人可以和平地表達意見。如果以 2016-2018 年的標準,很多民主派在 2019 年的區議會候選人(例如不少本土派候選人)都可能已被取消資格,但結果只有黃之鋒一人被禁止參選,相信港府已是顧慮了西方的壓力。當然,一個黃之鋒被禁參選,在西方傳媒和政界來說,已經是政府操控選舉的確證,同樣引起很多批評。
另一方面,美國直接介入以及把香港事務與貿易戰等掛鉤,還有香港政界直接遊說美國及其他國家制裁中國,必定令北京不滿,亦應該是推使中共在 2020 年五月為香港立國家安全法的重要原因之一。港區國安法特別針對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組織恐怖活動、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四個範圍,其中「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干預」為基本法二十三條原文所無,用意應是禁止香港政界遊說西方以及與「台獨」勢力聯繫。
人大通過國安法後,美國宣佈根據《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撤銷香港的特殊待遇,並啟動制裁。香港的人權、自治和民主發展,因 2019 年的反抗運動,變成中美外交角力上的一個主要項目,亦因此牽動不同國家與中國的關係。
.png)
本文摘自左岸文化出版《反抗的共同體:二〇一九香港反送中運動》
《反抗的共同體》詳述從雨傘運動到反送中運動的源起、過程與影響,擴及中共政權的因應、國際之間的角力(包括台灣),最終試圖逼近反抗運動如何形塑這一代香港人的身份認同,進而長出一個命運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