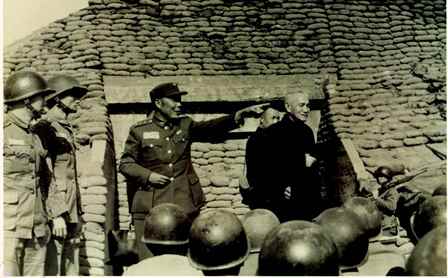本次對談中,兩位學者指出文化資產保存常見的迷思,分析糖業文資保存的可能性,並強調歷史事實不等於歷史價值,期許歷史學者於文資保存領域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只要值得被保存下來、傳承給下一個世代的東西,就是文化資產。
Q1 : 文化資產與它保存維護的核心是什麼?
榮芳杰(以下簡稱「榮」):
中文通常會叫文化資產或文化遺產。文化資產加上「法定」兩字,則專指《文化資產保存法》(以下簡稱《文資法》)定義中的文化資產。不過對我來說,廣義的文化資產包括法定身份跟無法定身份者,只要值得被保存下來、傳承給下一個世代的東西,就是文化資產。
文化資產保存的核心是要保存其「價值」,保存的條件在《文資法》裡面有很多類別,每一個類別在法令上有其定義和價值,這種是屬於法定的;沒有法定的,則也許基於情感、集體記憶,這種也有屬於自己的價值。
王淳熙(以下簡稱「王」):
我跟榮老師的認知非常接近。許多人會覺得某些舊東西有價值,所以應該成為法定文化資產,但依照《文資法》規定,當物件要進入給予法定身份的程序時,往往有很多問題必須討論。因為牽涉國家給的資源與限制,法定文化資產必須具備高度的公共性。
榮:
公共性經常被列為法定文資的考量條件,但我認為一般討論沒講清楚的是,當物件變成法定文化資產,從臺灣現行地方制度來看,它應該至少具備能代表「地方」的價值,如縣市定古蹟應該對縣市地區有意義;能代表「國家」價值的國定古蹟,就應該是對國家有意義。這個問題背後其實是文化資產的「價值」是否要分級。
例如最近臺靜農日式宿舍的問題,我們不能否認房子裡曾經發生過事情,關鍵是我們常常把歷史上發生過事情等同於有文化資產價值,忽略了當房子要變成法定的、國家的文化資產時,國家會注入資源,所以應該是基於它對這個地區或國家有重要貢獻。
名人故居的居民肯定是有名的人,但得釐清他的貢獻是什麼、是否能得到大家的認同。這些貢獻在現行國內的法令規章沒有適切位置,才會衍伸有人從建築物的角度看價值,有人從曾住在裡面的人的知名度看價值。
英國實行的 Blue plaque 計畫是我心目中很好的名人故居典範,他們談的是社會各行各業「人」的貢獻,而不是建築物的價值,特別要注意的是,他們是給這房子一個具紀念性的銘牌,而不是給一個國家法定文化資產的身分。

王:
這也是我最近跟學校歷史系老師在談的問題,我們常常面對的是歷史事實跟歷史價值之間的取捨,我一直想問歷史界的是,你怎麼看待歷史價值?雖然有辦法找出歷史事實,但是當要評價歷史價值,歷史學者常常不見得做得到。如果歷史學者都做不到,我們這些唸建築的來做,大家就很容易各說各話。
而且歷史價值確實因為不同時間、地點、族群及社群等因素造成評價的不同。像臺靜農的問題,或許某些團體給予高度的評價,可是跨出小圈圈不見得有很多人認識他。這是在價值上很容易卡關的地方。
另外,有些案例一部分是物件本身容易辨識的價值,一部分是事件衍生而認知的價值。如果要訴諸一般民眾能理解文化資產,或許從物件本身是最容易獲得認同的,例如外觀漂亮民眾會比較容易接受。大部分的人一開始認識的世界遺產價值,簡單來講就是四個字:高、帥、富、奇,超出這個範圍就要靠大家「心有所感」才有辦法理解。
我有一次去波蘭的奧斯威辛集中營(Konzentrationslager Auschwitz-Birkenau),發現去的人很多,但真正能理解那段歷史的人卻不多,大部分是去獵奇。當歷史事件要進化到歷史價值的討論,就必須放到更大的群眾體去看,一般人往往不容易理解事件的價值,除非價值的闡釋能做到讓人心有所感。
讓大家回到那個時空,認識生命經驗裡面遺漏的一塊時間,這就是世界遺產解決斷裂的辦法。
Q2:臺灣的糖業文化資產,和其他產業的文化資產有什麼不同,為什麼糖業的歷史記憶是重要的?
榮:
糖在臺灣的重要性,是因為它是跨時空的產物,從荷蘭時代開始製糖,到日本人來讓糖業變成一種工業,很多人投入其中。這個產業變成以糖廠為核心、在周邊形成生活圈,有生活圈就會有日常的需求,會有學校等等,最後糖廠的員工就幾乎遍佈在幾個重要的糖廠週邊,這個時空脈絡一直延續,但是現在產業式微所以不斷消逝。糖業是臺灣很多縣市過去都有的產業經驗,從空間的廣度來說當然很重要。
保存糖業文資能讓人在同個地點認識不同年代的製糖過程,但這是一個理想,目前糖廠的保存並沒有呈現這件事情。從第一題的角度來看,保存糖業文資的原因,不是因為那根煙囪漂亮,也不是因為五分車的鐵軌很厲害,而是因為糖可以串連臺灣過去幾百年來的歷史脈絡,假設把糖廠的內涵(content)和價值講清楚,就代表所有人進到這個場域,可以一次認識臺灣如何從以前發展到現在,未來如何繼續銜接。
王:
善化糖廠的煙囪對當地人來說是一種記憶,他們和長輩從小生活在善化,空間本身就是記憶所在。不過現在善化有很多南科來的人,他們沒有糖廠的記憶,所以看到運輸途中落下的甘蔗葉、糖生產時發酵的味道、糖廠煙囪冒煙,會當成是嫌惡設施。所以把它保存下來還是要問,這是「誰」認知的文化資產。
糖是生活必需品,但日常生活中大家並不怎麼關心,比如不確定自己吃的糖是不是臺灣原料生產的,台糖的糖只有自產二砂才是臺灣的甘蔗做的。我認為這也是現在談糖的文化資產價值時的一個斷裂點。

榮:
這個斷裂點就是剛剛提到的,應該是要讓下一個世代理解為什麼保存糖廠。剛剛王老師提到現在的南科人把它當成嫌惡設施,代表我們沒有讓他理解這曾經是臺灣人生活裡的一部分,沒有讓這個世代的人學會尊重歷史。這也是為什麼我認為臺灣的文化資產場域,應該要扮演超越課本以外的積極角色,讓更多人在文化資產場域裡學習認識與尊重歷史。
就像奧斯威辛集中營,觀眾最初也許覺得是過去死了很多人的地方,會懼怕等等,但如果認真了解故事,其實會感動波蘭人的寬宏大量。波蘭人願意開放這個地方,代表選擇用原諒的態度處理這個歷史事件,並且企圖讓參觀的人都理解。奧斯威辛作為世界遺產卻不收門票,目的就是要讓世人在這個歷史現場學會尊重與原諒。這些手法和動作都是為了填補像我們剛剛講的糖廠與斷裂點的問題。讓大家回到那個時空,認識生命經驗裡面遺漏的一塊時間,這就是世界遺產解決斷裂的辦法。
王:
透過這樣的操作和不斷的詮釋,其實就是試圖讓歷史學裡面講的歷史事實,有辦法轉換成歷史價值的關鍵過程。如果這件事一直沒有做,恐怕我們就會一直落入各說各話的情況。
榮:
我跟王老師都會關注「詮釋」(interpretation),「詮釋」通常會有主體跟客體的差別,從臺灣人的角度看糖業會有一個看法,從日本殖民者的角度可能又會有別的看法,所以理論上這樣的場所,特別是在殖民時期,應該讓糖廠成為一個中性的空間,裡面詮釋的內容要有不同角度,這樣在這個場所裡,當代的人才有辦法選擇自己的位置去理解歷史。我相信在歷史學門裡面,也有對於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立場的人,我認為文化資產是個很適合進行融合的場所,或是做各自表述立場的場所。
可以說糖廠設置幾乎是個複製的過程。
Q3:糖業最主要的所有者是台糖公司,他們怎麼處理糖業文化資產?臺灣糖業有很長的歷史,且涉及的空間區域相當廣,導致現在有很多「園區」。我們是否需要那麼多糖業文化園區,每個糖廠的地方性與獨特性又在哪裡?
榮:
早年台糖公司的官方政策,比較站在土地利用價值的角度而反對文資保存,主要還是民營化之後的財務壓力,但這些年台糖公司的觀念(循環經濟)開始有一些改變,所以會因為公司的政策方向而對台糖旗下的物業處置方式有不同的考量。對比之下國營事業的台電公司現在則是非常支持文資保存。
王:
關鍵是他們發現做這件事有其價值,或許對於企業社會責任有幫助。台糖雖然反應相對遲緩,但國營事業像台鐵最近也有台鐵美學,動了之後發現有正面反應,就有機會繼續動。
榮:
至於如果單純講園區規劃,那就只是台糖自己的經營策略。
王:
他們也想不到其他方法。有文資身分的文化景觀是花蓮、拆掉的斗六糖廠,而每個園區都有一些個別歷史建物。雖然每個糖廠生產的糖不太一樣,製程、設備還是會有一點差別,但差別很有限,整體流程是非常相似的。
糖廠廠區需要比較大的空間範圍,如果涵蓋甘蔗生產,臺灣中南部都是糖廠生產使用的空間。可以說糖廠設置幾乎是個複製的過程。既然空間型態相似、發展歷程也很接近,能變化的方式恐怕很接近,所以園區很多且缺乏特色恐怕也是非戰之罪。
榮:
現在我們講這個其實都有點慢了,假設一開始產業端就有文化保存意識,台糖總公司就可以針對各區處的糖廠做系譜化的比較,保存有特別意義的機具或空間。我當初進去看一些糖廠,機具設備都還在,但是這樣的空間沒有得到關照,現在有的設備已經丟了,所以台糖從保存的角度來看是比較沒有整體戰略的。
王:
對於是否成為文資,台糖是沒有想法的,沒有戰略所以變成走一步算一步,這點是比較可惜的。
在數位時代我們也不要排除數位保存的可能性。
Q4:傳統糖業目前還留下哪些有形與無形的遺產,而當新式機具與技術進入臺灣之後,面對臺灣的環境與人力訓練的特性,是否有在地化的情況?糖廠的廠房、機具、技術留存的情況如何呢?
王:
機具的部分,現在看到留下來還有在運作的就是善化跟虎尾,蒜頭剩不多,花蓮和橋頭留的比較多。機具在地化的問題比較看不出來,善化的機具還是昭和年間的,其他就不清楚。不過可以發現機具還是常常會更動,像發電機就比較晚期才有,但有些若沒有明確的銘牌就會比較難判斷。
產業遺產有個尷尬的情況是,如果要讓它繼續生產,但要求用古早的生產方式,是很不合理的要求。產業遺產必須兼顧兩個有點衝突的觀點:我們得承認舊的生產方式效率就是差,不符合時代的需求;但做為文資,我們卻又希望看到過去的樣貌。因此生產效率差的時候,可以思考的是是否有機會從文化端給予補助,彌補它的差,但這補助可能遠遠超過我們對建築類修復的經費。
榮:
技術製程的提升肯定是產業遺產必定面對的問題,假設我們要活的產業遺產,應該要給它活下去的生存空間。但是就會出現矛盾的問題,那傳統的東西要怎麼辦?這是可以討論的。我們可以從物件的存世必要性去討論該保存多少件,真無法實體保存的物件,在數位時代我們也不要排除數位保存的可能性。
西方國家的保存經驗已經告訴我們,文化保存是一個動態的過程與趨勢,保存過去,我們也必須考慮當下與未來。舉例來說,嘉南大圳的水圳溝渠斷面從 V 形改為 U 形,假設 V 形要被時代淘汰了,我們該做的就是講清楚為什麼需要從 V 形改為U形斷面,這是產業內部提升技術的關鍵點,面對文化保存議題就是想辦法做保存與紀錄,一百年後舉辦展覽,至少能讓人理解歷史上曾經有過 V 形斷面。我們不可能阻止人類進步,人類進步的過程如果能被留下證據,就盡量留下,不過不應該到停滯不前的地步。

如果我們已經回不去眷村,要傳承的眷村價值,應該是新的居住文化與舊的眷村文化融合的生活體驗,不該只有刻板的眷村展示館。
Q5:日治時期以來,糖廠社區多設置豐富的公共設施,包括學校、醫療所、郵局、理髮店、神社或寺廟等,這類規劃在其他產業社區也很常見。但隨著產業轉型而瓦解的產業社區,它的記憶與保存可以做到什麼程度?
榮:
歐洲有類似這種生活型態,把各種不同設施留下來的空間,有點像時空凝結的概念,可以讓大家體驗回到那個時空,但這不容易在臺灣活下去。臺灣的文化保存有個難題,是管理的動態性變化要存在,要讓大家進到文化場域就得讓它一直有改變,但如果讓糖廠回到某個時空凝結的狀態(就像是坊間的懷舊餐廳般),我想它會經營不下去。一次性的消費習慣,是臺灣的古蹟場所最不容易突破的經營困境。
如同現在大部分的眷村保存,都比較偏向用展示館、博物館的形式展示物件,沒有從生活面向進行保存,現在大家會去眷村的原因,是因為曾住過眷村的人和眷村還有連結,但未來這群人不在了,眷村就只會變成一個沒有生命的建築聚落。同樣的,糖廠已經不生產糖,所以周邊設施失去存在的必要性。以臺灣情況來看,它要活下去不太容易,更何況會牽涉到各種產權問題。
王:
剛剛這段是否可以有一個討論,會這麽說是因為我們沒辦法做類似民俗村經營的緣故,還是說這些空間不適合?
榮:
就跟眷村的本質是住宅一樣,糖廠週邊都是生活性的設施,生活性的設施要有活著的人存在才有意義,當活的人不在了,殼的再利用就會變成奇怪的東西。應該要思考的是如何把人的生活再放回空間裡面,唯有回到常民生活的一部分,聚落保存才能永續。
王:
那像鳳山黃埔新村被「以住代護」的政策如何呢?
榮:
臺灣眷村的保存政策還是無法擺脫眷村樣板式的方法,原因是沒有把「居住生活」的本質放在前面,而是優先考量建築物的使用性,最後空間就只是變成商業模式下的載體,以至於原本說好的眷村價值,最後都會被忽略。
「符號保存」容易引起共鳴,像是眷村菜、眷村文物等,但危險之處是符號只對經歷過的人有意義,其他人很難有共鳴。如果以住代護是長期政策,我會支持,但目前看來只是墊檔用,國防部尚未決定黃埔新村如何呈現所謂的旗艦型眷村博物館之前,以住代護就是臨時性政策。
現在進去以住代護的人本來對眷村沒有概念,但他們不管如何運用建物,會拉進一些眷村元素,已經開始跟房子產生當代的生活記憶,這是眷村的居住功能換手演出。如果維持原來居住機能,繼續以住代護,它會用自己的方法把眷村文化帶進來。如果我們已經回不去眷村,要傳承的眷村價值,應該是新的居住文化與舊的眷村文化融合的生活體驗,不該只有刻板的眷村展示館。
王:
糖廠有個更不一樣的事情是,糖廠跟當代人的接觸一直存在,至少人們會去糖廠買冰,這跟眷村在某個時間點以後被凍結,然後重新開展出一個新的樣態(例如以住代護),兩者的脈絡不太一樣,如果要再規劃後續居住使用時需要先理解這點。現在經常用的藝術家進駐是不是應該檢討了呢?
榮:
藝術家進駐通常是文化資產百廢待舉時的作法,某種程度是為了增加曝光機會,所以可以用這方式開第一槍,但是藝術家不可能一輩子待在一個地點,還是要有人接棒演出。現在新竹海軍第六燃料廠,也是交大用藝術進駐的方式,但走到某個階段後就差不多得思考下一步發展,下一步是最難的。

.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