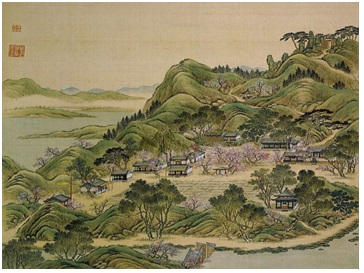《蒐藏全世界:漢斯史隆與大英博物館的誕生》(Collecting the World: Hans Sloan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British Museum)一書主標包含當前科學史研究的兩個關鍵詞:採集(collect)與世界(world)。就前者而言,一直到相當晚近,科學史家才開始關心採集。理由在於,當科學史這個學科於一九六○年代初具規模時,研究者關心者往往是抽象理論的突破;關於「採集」這種會把手弄髒之事,科學史家往往視之為枝微末節。
然而,自一九八○年代起,科學史研究迎來所謂「實作轉向」(practice turn)。研究者的焦點從科學家在想什麼,逐步轉移至科學家在何時、何處、基於何種理由、以何種手段來做科學。影響所及,實驗室、博物館、植物園、田野等科學地點(scientific site)逐步出現在科學史研究者的視野。
2000 年前後,研究者則體會到,如果說科學知識最大的特色是能放諸四海皆準,那麼,單單揭露科學知識的生產地是不夠的;如林奈、達爾文等為世界之運作提出解釋架構的偉大學者,他們之所以能辦到,不是因為他們與世隔絕地做研究,從而參透世界的真理,反倒是他們如何積極地與世界打交道。本書作者德爾柏戈(James Delbourgo)自己是這樣說的:
普世知識必須仰賴超越社會階級、橫跨各式文化的普世交遊
2004 年,劍橋大學科學史家塞科德(James Secord)發表 “Knowledge in Transit” 一文,呼籲研究者得將「交遊」(在臺灣,或許「交陪」是更為恰當的詞彙)放在科學史研究的中心。科學之所以能放諸四海皆準,關鍵不是四海遊走之人的心悅誠服,反倒是性格海派的科學家費心經營的結果。如此以「世界」取代科學之普世性(universality)的研究取向,研究者稱之為「全球轉向」。
《蒐藏全世界》可說是前述兩大轉向中最引人注目的作品之一。作者德爾柏戈於 1972 年出生於英格蘭,父母均為義大利人。在東英吉利大學(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劍橋大學與賓州大學接受訓練後,他於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師從著名英國史與全球史家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畢業後的德爾柏戈先至麥克基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任教,目前則擔任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大學的講座教授,同時也是哈佛大學科學史系的兼任教授。德爾柏戈長期關心採集與博物學史,亦為當今全球科學史研究的領軍人物。
有趣的是,德爾柏戈的第一本書其實是關於實驗科學史,且視角侷限在十七至十八世紀的美國。在這本題為A Most Amazing Scene of Wonders: Electricity and Enlightenment in Early America (2006) 的著作中,德爾柏戈娓娓道來一頁少為人知的電力文化史。我們都知道富蘭克林在雷雨中放風箏與發明避雷針的故事;但德爾柏戈告訴我們,在富蘭克林身處的美國,為電力著迷者絕對不限於自然哲學家,還包括魔術師、傳道者與醫生,均為電力所著迷,並藉此探索人類、自然與神聖間的關係。
按照德爾柏戈日後的說法,在他探討當時對電力感興趣的人們如何以原產自荷屬圭亞那(Dutch Guiana;今日的蘇利南)的電鰻進行實驗時,他開始對採集與全球科學史等主題感興趣。顯然的,要探討電鰻實驗,關鍵主題是電鰻究竟從何而來。然而,他發現,這顯而易見的問題竟然是當時科學史研究的最大盲點。他體會到,關於啟蒙或所謂「科學革命」的研究往往侷限在「物理科學及一小群在歐洲大都會活動的人物」,少有研究者願意將視線轉移到世界舞臺上,更別說把採集者、奴隸、殖民官僚、旅行者等不會出現在科學論文之作者欄、也不會現身研討會的行動者納入考量。
2008 年,他與麥克基爾大學的同事迪尤(Nicholas Dew)合編 Science and Empire in the Atlantic World,嘗試回應由電鰻引發的一系列思考。2009 年,他與劍橋大學科學史家夏佛(Simon Schaffer)等人合編 The Brokered World: Go-Betweens and Global Intelligence, 1770-1820 一書,集結對全球科學史感興趣的研究者,一同探討間諜、掮客、教會、翻譯者等「中介者」(go-between)在全球知識生產與流通的角色。2017 年,他出版《蒐藏全世界》,離他的第一本書已超過十年。至此,一度醉心於實驗科學與美國史的德爾柏戈,終於解決他的電鰻問題,蛻變為探討採集、博物學等主題、並以全球為尺度的全球科學史家。
***
《蒐藏全世界》以十七至十八世紀英國科學與醫學界動見觀瞻、權傾一時的漢斯•史隆(Hans Sloane, 1660–1753)為主角,探討這名來自北愛爾蘭阿爾斯特(Ulster)的貴族僕役之子,如何從當時英國社會的底層與邊陲力爭上游,於 1683 年取得醫學學位,在 1684 年被選為皇家學會會員,1687 年被選為皇家內科醫師學院(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會員,1693 年擔任皇家學會秘書(secretary),1727 年接替牛頓,成為皇家學會會長,且兼任皇家內科醫師學院院長,成為有史以來能將這兩個頭銜納入懷中的第一人。

1739 年,在飽受疾病折磨後,史隆著手草擬遺囑,表示國會若能出資兩萬英鎊,他就願意將價值八萬英鎊的博物學、書籍、古物、藝術等收藏交給國家,條件是國會不得拍賣或變賣它的收藏,也不得與其他收藏品結合。他認為他的收藏能彰顯神的榮耀,並反駁無神論及其影響;他希望他的收藏應對所有希望欣賞或參觀之人開放,且盡量為人所用,如此方能滿足人們的好奇心,並推動人類之進步。1753 年一月十一日,史隆撒手人寰,離他九十三歲的生日只有三個月。
經過一番激烈爭辯後,國會決定發行彩券,籌措史隆要求的兩萬英鎊——畢竟,在其遺囑中,史隆也註明,若國會未在十二個月內買下其收藏,他的代理人將會在聖彼得堡、巴黎、柏林、馬德里等地尋求買家。1753 年六月,喬治二世於通過〈大英博物館法〉;1759 年一月十五日,幾乎剛好在史隆過世的整整六年後,大英博物館開館,館址位於倫敦的大羅素街上。全球首間免費的公共博物館,於焉成立。
單看史隆的豐功偉業,讀者可能會以為,《蒐藏全世界》不過是另一本啟蒙或科學革命之科學英雄的傳記。實則不然,德爾柏戈筆下的史隆,絕對不是為真理而挺身對抗權威的伽利略或哥白尼,也非甘冒生命危險、在雷雨中放風箏的富蘭克林,更不是把手錶當雞蛋、不食人間煙火的牛頓。
在德爾柏戈筆下,或許可以這樣比擬:在高牆與雞蛋間,史隆會選擇站在高牆那邊;又或者說,史隆會仔細端詳那枚雞蛋,辨明其真偽、產地與性質後,構思如何以這枚雞蛋為敲門磚、墊腳石或支點,讓他得以翻過眼前的高牆,展望下一堵高牆。是的,對德爾柏戈而言,史隆能平步青雲的理由再尋常不過,跟你我在收集郵票、球員卡與寶可夢時所做的並無二致:採集。
故事來到 1687 年的倫敦。憑藉與他同樣出身愛爾蘭之自然哲學家波以耳(Robert Boyle)的交情,以及其高超的醫術,史隆成為牙買加首任總督的私人醫師。待在牙買加的十五個月間,史隆花很多時間在解決總督本人及英國殖民者的酗酒問題。與之同時,他也深刻體會到,如時人不無諷刺地點出的,為了促進自然哲學發展而設立的皇家學會,與當時負責奴隸貿易的皇家非洲公司(Royal African Company)堪稱「雙胞胎姊妹」(twin sisters),有幾任的皇家學會會長同時兼任加勒比海地區的總督。剛被選為皇家學會會員的史隆,決意證明這樣的觀察是多麼正確。
一方面,他協助當地的蔗糖莊園主,維持黑奴的健康,以確保正急遽工業化與帝國擴張的英國社會,能有源源不絕的碳水化合物來源;另方面,他也發現,對人類知識的發展而言,黑奴相當「好用」。他悉心收集黑奴的地方知識,採集他們的樂器與工藝品,莊園主用來懲罰頑劣之黑奴的刑具,並動員他們為其採集。這些自黑奴身體上與腦海中採得的知識,成為史隆日後撰寫兩大卷《牙買加自然史》(Natural History of Jamaica, 1701-1725)的主要材料。
回到倫敦後,史隆對採集的興趣並未稍歇。從後見之明來看,他最「划算」的收藏為一名叫做羅斯(Elizabeth Langley Rose)的寡婦。羅斯的前夫為倫敦市議員,同時也是牙買加的主要蓄奴者與蔗糖業者。兩人於 1695 年成婚,立即為史隆帶來一年三百萬英鎊的收入,以及一批能讓他持續收集牙買加自然史資訊的奴隸大軍。當史隆的口袋越深,他的視野也越來越廣。關鍵在於,史隆所置身的英國,也在這個時間點,經歷一陣陣激烈的轉型,「從一個以務農為主、飽受宗教與族群宗徒的多族群共同體,演化成一個更統一也更富裕的國家,並開始經營世界上幅員最廣闊的商業帝國」。區區牙買加的自然史已不能滿足史隆;現在,他要採集全世界。
有錢或許能使鬼推磨,但不見得能使人聽話。德爾柏戈指出,「史隆要向全世界收集珍品,就得收集同樣多種的人」。引用著名科技與社會(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STS)研究者拉圖(Bruno Latour)的 “assemble” 概念,Delbourgo 又說,「assemble一詞指涉建造某項物品,也有聚集人群之意,史隆能收集到何種物品,取決於他能集結到何等人物」。
確實,當史隆決議要採集全世界後,他所做的不是勸說皇家學會派出採集者,也非向政府施壓,希望政府能出面組織海外探險隊。他做的其實是寄信給英國的海外殖民據點,期待散落在帝國邊緣的墾民、奴隸商人、公司主管、投機客、探險家可以為其採集。要之,與我們比較熟知的深具官方或組織色彩的探險不同,史隆是以一介富紳之姿,編織出綿密的採集網絡。
在此網絡中流動的不只是金錢,標本也不只是商品,把人與人、人與物牽連起來的也非契約明訂的權利義務;支撐起這網絡的,德爾柏戈的分析顯示,更多是禮尚往來的人情與禮物交換。德爾柏戈指出,「這些網絡不僅是史隆事業的脈絡,它們就是他的事業,需要不斷地運作與協商」;在那個寫信還算是個奢侈之舉的時代,德爾柏戈估計,史隆的書信往來共有一七九三封。至史隆於 1753 年辭世之際,其收藏涉及的空間尺度已讓人乍舌:
世界有多大,史隆的收藏看起來就有多廣
英文中有個諺語:you are what you eat;在史隆的例子,我們或許可以說,you are what you collect。在經營他遍佈全球的採集網絡時,史隆也逐漸演化為德爾柏戈所說的「謹慎、嚴肅、又全無想像力的基督新教實用主義者」。雖說貴為英國學術與醫學界的龍頭,他無意如同時代的牛頓或林奈一般,為自然甚至宇宙的運作,提出某種普遍的理論;他樂此不疲的,是為他手中的藏品編目,並就當中特別怪異的收藏,撰寫描述性的文章。
可以理解,在那個後世稱為「科學革命」的年代,史隆的科學貢獻毫不起眼;確實,牛頓本人、同僚與粉絲就曾批評史隆的科學風格,認為這個靠砂糖與為名流看診而致富的暴發戶,毫無理論化與抽象思考的能力,收了一屋子的破爛還沾沾自喜。然而,德爾柏戈指出,史隆可說是英國最嚴格的事實查核者與謠言終結者;當他汲汲營營地為其收藏建立秩序的同時,他也是在為輪廓初具的大英帝國建立政治秩序。
身為新教徒的他,除了以其醫術幫安妮女王(Queen Anne)續命,確保新教的漢諾威選侯(Elector of Hanover;日後的喬治一世)可以繼位,杜絕天主教詹姆士黨人(Catholic Jacobites)奪權的希望外,更以其收藏為基石,輔以一則一則的藏品目錄與描述,為英國社會展現一個政治正確、吻合新教教義、且可通過經驗檢證的世界。這個世界容不下奇蹟、怪力亂神與道聽途說;站在這個世界的中心者,是如他這樣知所進退、腳踏實地、靠己身能力站上社會高層的富紳,而非他曾在牙買加目睹的不知節制、放縱、喝酒喝到喪命的王公貴族。
臺灣的讀者或許樂於知道,1697 年,有個自稱為喬治・撒瑪納札(George Psalmanazar)的傢伙出現在倫敦,宣稱他是來自福爾摩沙,並一路招搖撞騙。當時挺身挑戰撒瑪納札者便是史隆。再者,曾任荷蘭東印度公司醫生、派駐長崎的坎普法(Engelbert Kaempfer, 1651–1716),身後留下的龐大日本收藏與手稿,曾面臨遭到後人拍賣的危機;是在史隆的奔走下,坎普法對日本的第一手觀察方得以保存與出版,奠定歐洲日本研究的基礎。在其著名的關於巴斯德的研究中,拉圖曾言,「給我一個實驗室,我將舉起全世界」;他的意思是,實驗室給了巴斯德一處支點,讓他可以借力使力,以一系列精巧設計的實驗,為世界帶來莫大改變。在史隆的例子,或許可以說,十八世紀上半葉,當年邁的史隆思索他可為後世帶來的貢獻時,他心裡吶喊的是,「給我一個博物館,我就給你全世界」。

***
《蒐藏全世界》為德爾柏戈帶來國際聲譽。BBC、NPR、New York Times、New York Review of Books、New Republic等媒體均出版書評或專題報導。評論者盛讚德爾柏戈試著重建一個「有血有肉之史隆」的努力。以德爾柏戈的話來說,史隆可說是「成名與失憶兩症合發的特殊案例」;他的意思是,即便史隆之名似乎無人不知,甚至「史隆遊俠」一詞也被發明出來,以譏諷那些住在倫敦史隆廣場周遭的有錢人,但具體來說史隆是誰,卻無人知曉,甚至也沒人關心。
科學史家則認為德爾柏戈賦予「科學革命」更豐富多元的意涵。關心科學史或STS的朋友一定知道謝平(Steve Shapin)與夏佛(Simon Schaffer)的《利維坦與空氣泵浦:霍布斯、波以耳與實驗生活》(英文版出版於 1985 年;中文版出版於 2006 年),《蒐藏全世界》關心的也是同一時代,甚至也是同一個社會。並置兩書,我們可看到,如果說波以耳等實驗科學家試著以實驗得到的「事實」來建構自然界的秩序,從而描繪出一個理想的政治秩序,史隆要做的並無二致。
當謝平與夏佛引用維根斯坦之語,表示實驗是種生活形式(form of life),德爾柏戈則告訴我們,採集同樣也是。不同的是,當謝平與夏佛關心的生活形式多少還是侷限在倫敦中的都會區,且實踐者不過是一小撮自認為紳士的實驗哲學家時,德爾柏戈的視角早已跨出倫敦,「從西非的奴隸碉堡延伸到北美的殖民聚落,從加勒比海延伸到東印度公司散佈在南亞與東亞的商館」。採集作為一種生活形式,是帝國的,且沒有放在帝國的脈絡中,便不能妥善理解。
***
完成《蒐藏全世界》的德爾柏戈目前正在從事多項研究計畫。一者為深海探險的文化史;當我們提到探險時,思考的軸線往往是二維的,對於深海探險這樣涉及垂直維度的科學活動,理解相對有限。二者為採集的暗黑史:顯然的,如史隆這樣把採集、帝國與奴隸制結合在一起的科學工作者,既非前無古人,更非後無來者。第三則為「知的世界」(the knowing world)之教學與研究計畫。
在一篇發表在 History of Science 的文章中,史隆回顧他從「採集全世界」至「知的世界」的心路歷程。他表示,全球科學史的研究者要做的既非把科學放在全球脈絡中理解,也非探討科學在旅行;研究者有必要汲取過去被視為區域研究者的心血,探討過去數百年來與科學共存、交流、激盪且相互傾軋的知識體系。對德爾柏戈而言,在花費十年以上的光陰為讀者建構一個史隆曾活過且參與打造之世界的同時,這個世界也改變了他。
Collect 的拉丁文為 colligere,意指把物與字詞聚集(gather)在一起。因此,閱讀一本書,其實也是在做個「採集的動作」;我們進入作者費心建構的世界,同時也採集作者的概念與語彙,從而學到一個新世界的建構方式或建構世界的新方式。
過去的臺灣為採集者的天堂,而晚近公民科學在臺灣的蓬勃發展,也意味著採集這種生活方式從未離我們遠去。德爾柏戈這本書就如佈滿著發亮貝殼的海灘;在此邀請各位在當中徜徉,採集當代一流科學史研究者所用的概念與語彙,從而建構一個足以描述臺灣之過去與現在的概念博物館,讓歷史上與當代曾在臺灣自然史上扮演關鍵角色的採集者與博物學者,在德爾柏戈之「知的世界」中留下屬於臺灣的地位。

★收藏博物學家的博物學家,如何串接起東西方的採集網絡?
當今的大英博物館收藏了人類過去的寶藏,但是在它誕生的時刻,卻是探索新世界的前沿基地。它的奠基者漢斯.史隆,為博物館的庫房藏量和定位,立下了第一個里程碑。他過世後,後人根據他的遺囑,成立世界上第一個「公共博物館」。
本書首次運用史隆的標本與物件、還有他的「物種目錄」所寫成。史隆的遺願是維持收藏的完整性,結果卻被現代學科專業化的趨勢所沖散,變成植物標本歸於自然史博物館、書信手稿歸於大英圖書館、其他物件與圖冊歸於大英博物館。作者試圖將完整的史隆拼回來,也讓我們更加認識帝國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