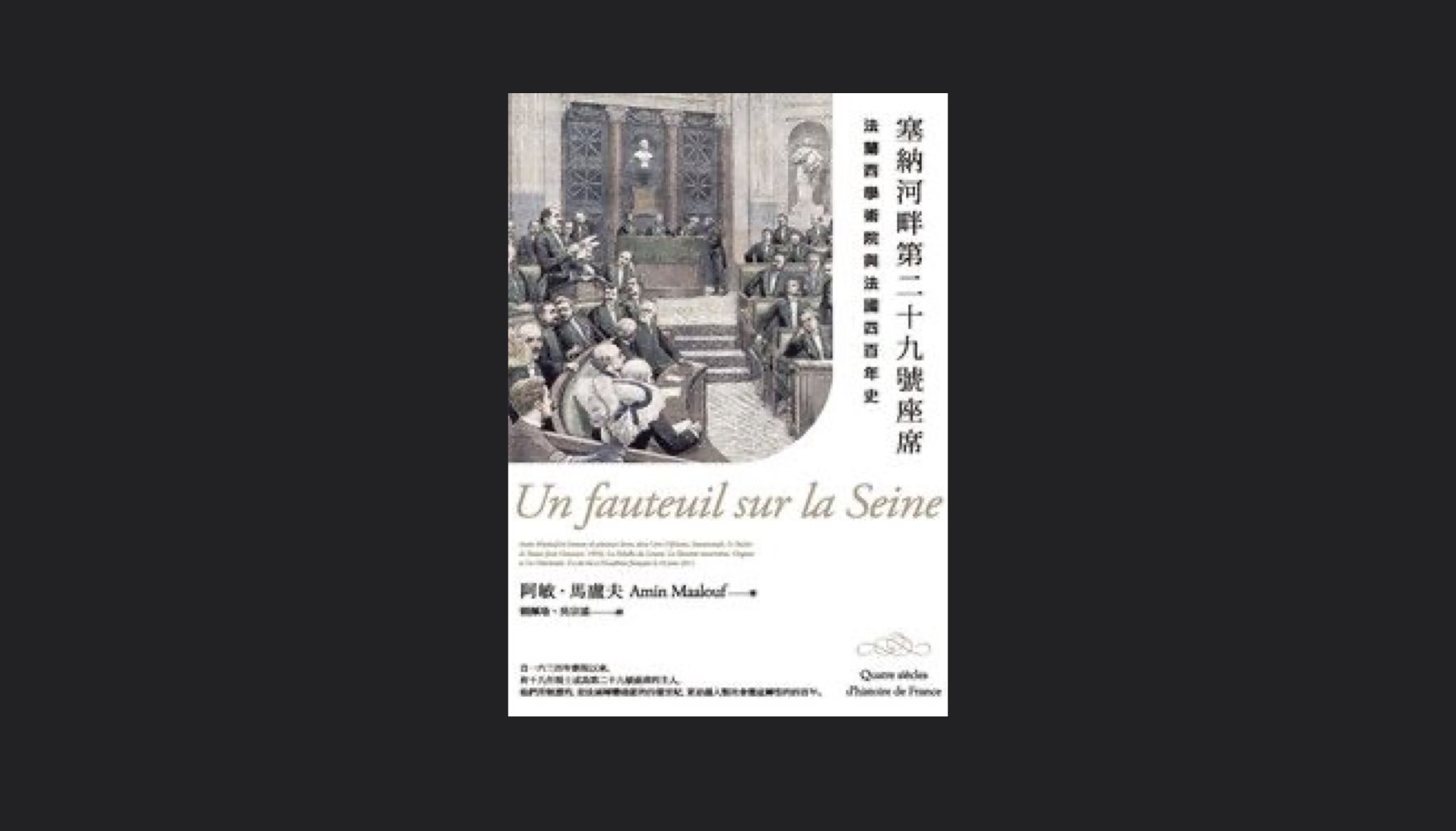從某種角度來說,今天繁華的台北,不單是成功的人、有錢人的台北,也應該是挫折的人、貧窮人的台北。
是全人類的責任,
也同樣是行政與立法者的責任。
願意為了最窮困的人,
而更新其文明型態、文化及精神生活,
這當然是出於愛,也出於我們的責任,
而將自身最深刻的信仰理念及紮實的安全感,
分享給最貧窮的人。
──若瑟.赫忍斯基神父
若瑟.赫忍斯基神父直接向一些朋友要求分擔責任,
這些朋友來自非洲,
1981年他們聚集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及第四世界組織總部,
他們在自己的國家為最貧窮的族群投身,
同時也是第四世界的通訊會員。
親愛的朋友們:請允許我以國際第四世界運動的名義歡迎您們,同時謝謝您們願意來到我們這裡。由於您們接受邀請,來到這個屋頂下,所以我大膽地稱您們每一位為朋友。事實上,您們回應了我們的召喚,您們以朋友的情誼和我們相交,您們信任這個來自男人與女人的召喚,這些男人與女人需要和您們建立友誼與團結關懷的聯繫。該如何向各位表達我們深沉的謝意呢?
您們的大師 Amadou Hampate Ba 告訴我們:「人們只能以另一個信任來回覆一個完全自發的信任。」為了答覆您們對我們的信任,我要大膽地向您們吐露:在這個第四世界運動中,我們是什麼?我們是誰?我們力圖成為什麼樣的人?

不久前,Hampate Ba 大師在阿比讓(Abidjan)接待我們中的一位到他府上時,曾如此說道:「你看,為了歡迎一個客人來訪,我們可以宰殺一頭牛;我們也可以和客人分享自己的歷史、自己的生命歷程。」
也因此,我們要和您們分享第四世界運動的歷史及生命歷程,來回報您們的信任。唯有透過歷史,我們的運動才取得意義,而且這段歷史是屬於我們的公民中最貧窮者的歷史,是他們將他們的歷史交付給我們:他們交付他們知道的一切,及他們親身經歷的種種。他們允許我們和他們一起將這段歷史分享出來。
要知道,當他們接受將自己的歷史交付給我們,將他們身上、心上所懷抱的一切傳達給我們時,他們也讓我們有了深層的改變:改變我們的人格,讓我們轉化為另一個人。第四世界的子民陶成我們成為我們之所是,而我將透過第四世界家庭的歷史,試著向您們描述我們是誰?
和我們敬重的賓客分享最珍貴的東西

為了描述第四世界的歷史,較為容易的方法是向您介紹幾個簡單的事件,例如:我們的運動在 1957 年誕生於法國,後來逐漸在西歐各國擴展開來,然後延伸到美國、加拿大、拉丁美洲、遠東以及非洲。
我們也可以很簡單地說它是一個團結關懷的組織,一個和世界上最受排斥、最被拋棄的家庭共享共思共行的運動;它的行動計畫和研究觸及幼兒、孩童的就學、青少年及成人的職業訓練、社會和政治的參與。
我們可以向您描述我們在住宅及家庭收入方面所做的奮鬥;我們也可以告訴您我們如何一步一步地取得各種政府機構的承認,並且在歐洲及世界上的國際性組織贏得諮商地位。
這是大部分的人常問我們的問題:「具體而言,您們做什麼?您們在官方有什麼地位?您們的經濟來源為何?」在回答這些問題時,我們絲毫沒有提到我們自己:使我們生存、成長的是什麼?給我們勇氣、希望、信任和愛的是什麼?然而,正是這些東西使我們和他們站在一起,分享他們的絕望並和他們一起改變。我們願意給我們的非洲朋友更多──因為您們當中沒有任何人問我們這些不實的問題。在問我們做什麼之前,您們是否願意知道我們是誰?我們深切尋求的是什麼?
您們的盛情使我們想以兄弟的情誼回報您們,和您分享最深、最隱幽,也最不容易描述的一段歷史。
一段誕生於孤單與痛苦中的歷史
首先,必須憶起我們的運動及其志願者聯盟的誕生,那在當時需要許多的勇氣與愛。我們的運動誕生在痛苦、焦慮及孤單中,周圍的人不瞭解它;總之,它誕生在一種毫無權勢、完全喪失眾望的情況下,當時我們赤手空拳,什麼也沒有。
1957 年,在最富裕的西方國家之一的法國首都──巴黎南郊一個貧民窟的核心誕生了第四世界運動。我們隨後發現,這個被稱為諾瓦集的貧民窟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貧民窟還要糟,住在這個貧困區裡面的,有法國家庭及出生在法國的移民後代。這三百個家庭住的地方就像人們在郊區蓋的豬棚一樣:陷在污泥中,沒有電、沒有衛生設備、只有一個給水龍頭(需供水給 1800 人);既沒有垃圾車來收垃圾,也沒有郵差來分送信件。
這些家庭在當時完全和這個世界隔離。他們甚至不被當做窮人看待,而是被視為不適應社會生活、不能被社會接納的人;他們成為施捨、救濟的物件,他們的孩子被系統化的強制寄養,而這些在救濟教養機構長大的孩子很快又淪為慈善單位接濟的物件,他們所生的孩子又再一次的被寄養……。不要忘記當時西歐正因自己在經濟及社會立法方面的進步而自豪,他們相信貧窮已不復存在;如果你仍陷於赤貧中,一定是你心甘情願,要不然就是你樂在其中。
然而,我自己和我的母親、兄弟及小妹從極端的貧窮中生活過來,加上教會對我的陶成,我知道,這些人、我的兄弟們,在他們的最深處,他們不願意過這樣的生活,他們所等待的不是公眾的施捨。即使赤貧的烙痕深刻在他們的外表和行止中,他們所等待的,是別人能夠穿透這一切,認出他們的尊嚴。親身經歷而得知這一切是一個優勢,這個優勢改變一切。因了這層瞭解,使我在轉向周圍的世界尋求協助及團結關懷之前,先向這些家庭請求協助。第四世界運動的特色就在於:它的第一批創立者、它最初的成員就是赤貧者本身。
也就是和他們一起,我們才有了第一個極重要又有象徵意義的舉動:請那些含有救濟性質的組織離開貧民窟,讓圖書館取代施湯站、以一個衣物合作社取代免費贈送的舊衣物(合作社的衣物仍然是舊的,卻能相稱地裝飾人的身體)。
在這個被稱為「法國城堡」(Château de France)的痛苦之地,事情就這麽簡單又有象徵意義地開了頭。繼第一個努力之後,緊接著是永久性志願者團體的形成及教堂的建立。我們想表達的是:赤貧是全人類的責任,也同樣是行政及立法者的責任,它是一件愛與分享的事,這件事要求我們和最貧窮的人分享我們最深的信仰與安全感,並且願意為他們爭取一個文明、一個文化、一個更新的精神生活。
當然,一些實際的服務隨之而來,但是這些服務都是以上述的信念為基礎,這些舉動和信念在當時很不容易被瞭解,不只是輿論界和政府部門,就連赤貧家庭本身也不習慣;他們馬上相信了我們,但還無法承受改變所帶來的後果。就如同您所知道的,生活在赤貧中的人不斷被排斥、不斷被周圍的世界(如市政府、學校、醫院、公安單位等)所輕視、羞辱。這情況一旦超過了界限,會促使人們力圖拯救自己而排擠他人,促使他背棄他的鄰居,他可能重覆的對願意聽他講話的人說:「我不認識我的鄰居,他們很壞、又懶惰,他們是小偷⋯⋯,我?我才不是那種人。」他知道自己說的不是實情,但是由於在這個社會,生活在赤貧中變成一件可疑、丟臉的事,他不得不這麼做以挽回自己的尊嚴。
第一批志願者在面對這些願意改變,卻不敢馬上轉彎、不敢完全改變的家庭時,難免感到無力。對這些充滿恐懼、不安的人來說,他們不時有彼此背棄、爭吵及相互輕視的誘惑,您可能會懷疑:他們真能成為比他們更窮、更被輕視的鄰居的護衛者?當然,這需要一種非常的勇氣。
任何人都會想要逃避這樣一個根本的改變,而社會服務部門、市政府當局,甚至中央政府就以此潑我們冷水,有好多年,他們以這些無法為自己辯護的家庭為口實打擊我們的士氣:「看清楚,你們錯了,這些家庭根本不理睬你們,你們最好離開!」
如果我們沒有離開,如果我們沒有停止成長,這都要感謝最貧窮的家庭。因為我們生活在他們中間,他們常常在夜裡跑來告訴我們他們白天不敢對公家機關說的話。我們因此知道,他們對尊嚴的渴望和對自來水的渴求一樣多,甚至更多;我們因此知道,他們不願一代又一代的接受救濟、被領導、管理、被視為劣等人、被視為施捨的物件。相反地,他們渴望得到職業訓練、他們渴望求知、和別人一起思考並表達自己。
是這些使我們堅持下去。當我們急切地想要逃避這個勝算渺茫的戰鬥時,是這些家庭的痛苦及希望使我們堅持下去。希望有一天,這些痛苦能轉為喜樂。而事實上,當我們回應他們對尊嚴與學習的渴望時,他們自己也投入這場奮鬥。

將赤貧者被排斥的事實彰顯出來
對我們來說,第四世界的家庭所走的歷程,遠比輿論、政府單位及政治領袖的歷程重要。然而有很長一段時間,這個重要的歷程卻不被輿論界、政府部門及政策的領導者所注意。
是第四世界的貧窮家庭本身在這方面逐漸前進,這個進展在當時可說是歷史性的一刻,因為在 1961 年,我們在諾瓦集接待了另一個貧民窟的代表,這個叫做康波(Campa)的貧民窟位於巴黎北方一個偏僻的角落,那些貧窮家庭的代表要求我們說:「到我們那裡去吧!我們處於絕望的邊緣,我們所需要的正是你們!」一個巴黎北方的貧民窟的居民怎麼會認識我們呢?他們怎麼知道他們所需要的正是我們?只有一個可能:那就是唯有窮人才知道的耳語、他們口耳相傳的秘密,他們之間互相交換訊息:「和志願者一起,我們可以生活在榮耀中,而不是依賴或求乞。」
我想,1961 年這一天,是赤貧家庭給我們的最美的禮物之一,這一天,我們的歷史有了轉變,這轉變使得不久後,巴黎市政府及他的社會服務處前來要求我們的協助。市政府邀請我們進入另一個貧困區,在那裡,市政府的社會服務部門一籌莫展,連分送牛奶給新生兒都變成一個棘手的行動。在那裡,有百分之八十的家庭沒有工作,除了公共救助外,沒有收入。
他們因為被安置在這個像集中營的貧民窟而感到羞辱,好像他們自己把自己關起來似的。他們辱駡過往的行人,往路人身上丟石頭,大家都怕他們,而且已無計可施,為此,人們才向我們求助。這個呼救像是人們最後的嘗試,而我們接受了這個召叫。在起初,這些家庭也向我們丟石頭,但是,他們看到志願者不但不害怕,還留下來承受這群絕望子民的拳腳,最後終於接受了志願者。
我們從一開始就體認到:如果我們把雙腳踏在諾瓦集的泥濘中,我們所護衛的已經不只是諾瓦集,而是全部的法國赤貧家庭,我們護衛他們的榮耀,他們在居住、工作、受教育及參與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權利。如果有人反對我們,我想那是因為在有意或無意中,他們也清楚在諾瓦集貧民窟背後,還有許多分散在法國,甚至歐洲各村落、各城鎮的赤貧族群。當我們出發到其它貧困區或其它國家去建立新團體時,全世界赤貧子民存在的事實也就逐漸彰顯開來。
獻出自己的生命,向他人證明他也能,他也是共同負責人
事實已彰顯出來,但既尚未被承認也未被接受。
有很長的時間,在法國和西歐,所有工業化國家都仍陶醉在自己的經濟成就裡,他們忘記一個富裕的國家並不等於一個懂得分享的國家;而大部分人的富足並不意謂著所有的人都分享了成功的果實。
事實上,那些被認為對財富的創造沒有貢獻的人被遠遠地拋在後頭。還需要一段很長的奮鬥,大家才會承認在最現代化的國家中,貧窮繼續存在著。我想跟您們談永久性志願者聯盟,他們為摧毀赤貧而投身,為了讓這群被捨棄的子民所隱藏的希望能夠實現,為了造一座橋,讓這群人民能夠和比他們幸運的同胞相遇。
把自己的生命獻給最貧窮的人,這件事的必要性及象徵意義是窮人親自教給我們的。對窮人來說,證明自己的存在已是如此的艱難,進一步要他們一起站起來,一起脫離赤貧,甚至走向比他們更被排斥的家庭,這些要求使他們慌亂不安,他們知道這是很大的冒險。然而,諾瓦集的家庭很快就明白:必須帶動其他貧困區做相同的改變,但,這是多大的冒險啊!然而,諾瓦集、康波及其他貧困區的居民開始說:「站在一起,我們將會更有力量!」
在這些臨時搭建的木棚區內,在這些被戲稱為「桃花源」,卻充滿髒亂的貧民窟中,在這些因赤貧而聚集在一起的族群中,必須敢於相信,必須有一些男人和女人以他們的生命為擔保,以實際的行動來證明,才能使人信服他們的話:「如果你要我,我選擇跟你一起生活並和你同步前進,因為我相信你,而且,當我知道你生活在痛苦和別人的嘲笑中,我無法再安心地過我自己的生活。」
必須瞭解窮人生活在什麼情況中,他們一代又一代,由父到子,不斷的受屈辱、不被看在眼裡,被迫接受別人的決定──社會服務機構及慈善組織「為了你的好處」所做的決定;別人從來就不問你的意見,從來不曾試圖去認識你真正的歷史及你的人性尊嚴;人們從來就沒想到要協助你完全脫離困境、讓你獨立自主,成為自由的人。因為你是窮人,你被定義成失去各種關係的人,你失去扮演一個角色所需要的各種憑藉,儘管這個角色在別人眼中非常微小。
這些貧窮的夫妻、父親和母親受苦于種種的否定。和別人相比,他們感覺到自己沒有價值、一無是處,甚至在他們自己的族群內或家庭中也逃避不了這種深刻的感受。總之,到最後連他們自己都相信自己沒有用,鄰居和鄰居之間也沒有什麼可說的,生活中的爭吵、暴力、混亂、嘈雜使他們成為彼此的負擔。這一切不是他們的過錯,然而赤貧者的痛苦就在於:這一切使他們在旁人的眼光中,成為可恥和丟臉的記號。
當長期的失業支配了整個家庭,當你無法保護自己所愛的人時,所有的愛似乎都成空,夫與妻也成為彼此的負擔。連孩子都是負擔,因為社會服務部門的人就是以孩子為由來批評甚至威脅你:「如果你們不工作,不改變你們的生活,你們就沒有資格保有你們的孩子!」
在西歐,第四世界的母親所流的淚水可以彙聚成一條河流,他們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孩子被強制寄養到別處。在同樣的情況下,第四世界的父親大聲辱駡的怒吼可以使整個富裕的社會震動起來。然而,她們的流淚,我們沒有看到;他們絕望的怒吼我們沒有聽到。因為在我們的國家,我們曾細心地把這些家庭驅逐到城市與村鎮的邊緣。
在我們的國家,無產階級以下的赤貧家庭被完全地排斥在群體生活之外;經濟和社會的排斥到最後也成為一種形體上與地理上的排斥。「第四世界」這個名字,是我們的運動給赤貧家庭的名字,一方面為光榮這群子民,聲明他們的尊嚴;另一方面為他的犧牲者辯護並證明排斥的存在。「第四世界」這個詞彙,無論在過去或現在,都清楚的說明我們曾經把我們最貧窮的兄弟驅逐到另一個世界去,在那裡他們才不會打擾到我們。
這些家庭不僅在物質上一無所有,更糟糕的是:他們連用來尊敬自己的可能性都沒有。他們真的需要有人來告訴他們:「你們是完全值得尊敬的,你們可以團結起來,我們將和你們站在一起!」當然,光說是不夠的,必須以不可辯駁的行動來證明,以整個生命的投身來證明。
今天,我們的組織成為一個國際性的運動,它總是去那些沒人願意去的地方,因為這正是排斥的記號。我們是否還需要赤貧的犧牲者來告訴我們:他們需要的不只是我們的援助和計畫,而是我們、整個的我們。我堅持這點,因為這個想法不是我們自己發明的,這個想法首先來自窮人本身。最貧窮的人是我們的導師。

最貧窮的人是我們的導師
他們首先教給我們他們的歷史。如果我們不明白赤貧子民的生命經驗:他們的父母、祖父母及祖先傳遞給他們的經驗,我們無法分享他們的生命;同樣地,如果這群子民本身對他們自己的生命經驗模糊不清,他們也無法長久接受我們。如果無法彼此瞭解,我們就仍然是陌生人,無法像兄弟一樣的生活在一起;因為當我們不明白一個族群真實的生活情況時,我們也無法瞭解他的思想和行為。
當然,在這方面,我們可以用很學術性的方法跟您說明我們的運動針對貧窮的歷史所做的研究。但是,在此我想對您說,這一切發生在極簡單的情況下──有一天,在巴黎近郊的一個貧民窟,有一小撮的男人和女人開始跟那些家庭說:「為了離開這赤貧的泥濘,只有你們和我們,如果我們不彼此幫助的話,沒有人會幫助我們。但是為了從赤貧中走出來,首先必須彼此瞭解。為了改變未來,必須瞭解過去,及這個過去所造成的現在。所以請同我們講述你們的歷史。」
不夠認識我們的人可能認為這是一種教育方法或是某種行動策略,但,都不是。我們沒有所謂的技巧或方法,赤貧者真實的生活情況已超過一切的行動方法。我們萬分需要瞭解這些家庭的歷史,需要讓我們自己進入他們的歷史,為了一起承擔這些痛苦和教訓,特別是盛接他們所懷抱的希望。對我們來說,如果有所謂的方法,它的基礎在於共融與愛。
「在我們的歷史中尋找」
我可以跟您說我們在 1960 年的那一天、那一刻開始了這場歷史性的探索。那一天,天色已經很晚了,我們在號稱「法國城堡」的諾瓦集聽一個家庭的父親講話,他叫做波納佛(Bonavo),這位先生告訴我們:「你們問我怎麼會來到這裡?我們怎麼會走到今天這個地步?很簡單,我們在這裡,因為我們從來就沒有度過另一種生活。從孩童開始,我就是個窮小孩,當時我父親已經是個沒有工作的男人……。」
也就是在 1960 年,我們的朋友,波納佛先生告訴我們這些話。他因為缺乏食物而顯得異常消瘦,特別是他佝僂的背、向前縮的肩膀、及總是低垂的頭,他的眼神老是盯著地板,好像不想再看到身邊任何瞧不起他的人?他讓我們醒悟到:在富裕社會的核心所存在的貧窮並不是一個偶然,並不是一些意志薄弱或缺乏道德觀念的男人與女人在生命路途中所發生的意外;也不是一些孤立的個案或是突然被失業或疾病所打擊的家庭。總之,他告訴我們,西歐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在工業化、都市化及教育制度與農業的現代化過程中,繼續把赤貧家庭拋棄在後頭。
事實上,必須意識到從一開始,最貧窮的人就被西歐引以為傲的工業化所遺忘、排斥。今天,西歐國家終於承認這點,並開始以電腦為輔助做艱深複雜的研究,以便對這個被稱為「持續赤貧」(La pauvreté persistante)的現象做解釋。然而,這位我們在大學裡從未提到過的波納佛先生,是他要帶領我們,他終將帶領整個歐洲走入正確的路徑,他說:「不要針對我們個別的個性做研究,也不要針對我們今天的生活方式下功夫;卻要在我們的歷史、我們的祖先裡尋找,是他們將他們的價值觀、他們的痛苦和絕望傳給我們。唯有如此,你們才會瞭解我們。」
另外,也許要補充說明:現代的研究很依賴資料和電腦,他們可能永遠不會觸及到今天的赤貧家庭真正要表達的是什麼。然而第四世界的家庭和志願者,日復一日,耐心的建立起數千份貧窮家庭的歷史資料,這些卷宗記錄著他們及他們的父母、祖先的生命。這群子民的歷史被鎖練銬在工業國家社會階級的底層,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的志願者聯盟不只是一個行動的聯盟,同時也是一個聆聽與探索的團體。
那些投身在現場的志願者有義務在每天黃昏寫下所有他們在白天所看到、聽到和學到的一切。他們寫的不是他們做了什麼,儘管他們也該重視這點。他們記錄,首先是為了讓這群子民的歷史存留在人類的記憶中,為了默想所有這些家庭對他們的談話,這群子民整個的生活及他們所表達的一切。
為理解而寫
這個為理解而寫的熱情,及因這個熱情而對歷史提出的詢問使得貧窮家庭本身也投入其中。
首先,他們終於有機會傾訴所有,並藉此而理解一切,這成為他們得到解放的第一步;他們終能從沉重的歷史負擔中解放出來,從他們原本已相信是一段羞辱的歷史中解放出來,終能告訴自己這不是恥辱,並因此而找回榮譽與自由。不僅學習整理生命的經驗;他們終於能夠發言、解釋自己、並知道自己有話要說,而且這些話只有身歷其境的他能夠說,並且,這些話對別人很重要。所有這一切象徵著被承認、重新找到一個位置、一個角色、一個用處。由於這一切,這些被社會認定為無藥可救的家庭才開始讓自己發言、並彼此聚集、參與一個共同的奮鬥、護衛他們的孩子的權益。
大家可能認為我暗示著這一切都隸屬於一種教育學或方法論,或者人們會想:總之,我們可以將這一切在學校裡教授給學生,這樣一來,我們就有了一種有效的方法來解放窮人……。這將是一種最根本的錯誤!我們和歐洲赤貧家庭的歷史證明:要解放窮人,一開始只是一個愛的嘗試,一個走向赤貧者的嘗試,尊敬他們的痛苦,並且熱切的願意與他們交談、分享,和他們一起往前走。否則一切的努力都將被打折扣,而簡約成一種教育學、一種行動的技巧;所有的努力將變成一種新的操縱方法、一種我們自以為對窮人有好處的管理及教育策略。然而,教育窮人完全相反於志願者所要的,何況,他早已選擇了最貧窮者、最受輕視者為導師。
以這些面容被赤貧所毀損的男人和女人為人性的導師?這是一種怎樣的嘲弄?然而,這卻是千真萬確的,並且是一個雙重的選擇:給後來者首位,以最貧窮者為導師。我切願我們的志願者永遠不要放棄這個信念,必須盼望、幫助他們。然而,除了您們,誰會幫助他們呢?
交付一個秘密,意即分享一份責任
如果我將這些東西交付給您們,我已經說過,那是因為我們願意和您們分享真實、珍貴又秘密的東西。但正如 Hampate Ba 大師有天跟他的朋友 Modibo Keita 先生所說:「某方面來說,跟別人分享一個秘密,同時也是交付給對方一份責任。」
您們可以用同樣的方式跟我交談,也許您們寧可聽別的東西:認識第四世界組織所領導的各種行動:我們在文化、醫療、社會方面的計畫;我們和政府部門的各項合作,甚至是我們在聯合國的諮商地位等。
但是,這些都屬於公共領域,您們可以在正式的報章中看到、讀到。如果在我們的組織、在我們所願意成為及我們試圖去做的過程中,有什麼真誠實在的東西,有誰比您們更能認出它來?有誰比您們更能瞭解:自己的歷史、身份及個人和整個民族不可剝奪的財富被輕忽意味著什麼?有誰比您們更能瞭解為何世上最貧窮、最被排斥的人,需要有人跟他們一起重建他們的歷史、聆聽他們?不是因為我們要教育他們,而是因為我們需要接受他們的陶成。有誰比非洲的男人和女人,更能成為所有被排斥的族群及各大洲的志願者聯盟的護衛者?有誰講話比您們更有權威?更有經驗?
為此,我們才轉向各位。別人談論著要幫助您們、帶給您們他們的技術和智慧。您們有時痛苦煩憂,因為您們眼見族人被迫要跟那些幫忙他們的人彎腰道謝。我們的運動沒想過要幫助您們,反過來是我們有求於您們,是我們要伸出雙手為能接受一些東西:為能得到您們的信任與智慧,而且── 如果上天願意──您們的友愛,為使有朝一日,最貧窮的人終能得到解放。
1. 10/17──世界拒絕赤貧日
2. 貧窮只因不努力?有一種窮是被困在低薪與非典型就業,他們難以穩定向上爬,卻老是踩空往下摔
3.「有工作沒照顧,有照顧沒工作」──社工眼中的貧窮孩子與貧窮家庭
4. 將窮人視為導師──在臺灣的「第四世界運動」
若瑟.赫忍斯基神父(Père Joseph Wresinski)簡介
若瑟神父於1979年被提名為法國經濟社會理事會的委員,1987年2月11日,他在該理事會發表了「極端貧困及經濟社會的不穩定」報告書,這份報告被視為對抗赤貧的重要參考文件,它不但影響了歐洲其它國家的反貧窮行動,也在國際間得到愈來愈多的迴響。同年10月17日,十萬人聚集在巴黎自由人權廣場,當天在這個廣場上,若瑟神父為全世界赤貧的犧牲者立了一塊紀念碑,碑文上寫著:「那裡有人被迫生活在赤貧中,那裡的人權就被忽視、剝奪,團結起來為使人權受到尊重,是我們的神聖義務。」1988年2月14日,若瑟神父病逝巴黎,並遵照他生前的要求,葬在第四世界總部(Méry sur Oise,法國),為了向赤貧家庭及所有為窮人投身的朋友表達他不變的忠信。
1992年12月,聯合國大會宣佈每年的10月17日為世界根除貧困日。之後並決定1997年至2006年為聯合國消滅貧窮十年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