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沒看見玻璃窗片的人本身並不知道他忽略了什麼。—艾莉絲.楊
傳統的性別差異與社會角色變遷
性別的不平等,可以從貧窮的「女性化」現象說起。
根據 2009 年主計處的統計資料,我國由小學至大專院校女性在學率為 96.4%,略高於男性的 94.2%,然而申請就學貸款的女學生明顯多於男學生;在人力資源方面,女性的勞動率快速成長 2009 年已達到 49.5%(未婚),但是一旦進入婚姻,男性的勞動率快速往上升,女性則轉折下降;除此之外,民國 100 年女性聲請拋棄繼承遺產的比例為 63.3%,遠遠高於男性的 36.7%,申報遺產稅的繼承人中,女性繼承人僅占 34.1%,男性占 65.9%,幾乎是女性的兩倍,這些數據顯示的是:有遺產者以男性居多。
更重要的是,這些數字告訴我們:兩性之間仍然存在著某種不平等。問題在於,不平等的根源存在於何處?
行政院性別平等委員會 2016 年的報告顯示:自我國 2007 年加入「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以後,政府已經在追求性別平等的目標上,做出了顯著的努力,不僅修正了《家庭暴力防治法》,擴大了受保護對象的範圍,也強化女性生產方面的國家救濟管道。
此外,我國《民法》中對性別平等的重視與改善也顯而易見──傳統民法中男尊女卑思想已修正許多,往昔規定「妻從夫居」、「妻冠夫姓」以及婚後財產均歸夫所有,離婚時對女性權益保障也多欠缺,例如子女監護權歸夫、父母行使親權時以夫優先等等──當前的法律則以性別平等為目標,大幅修改《民法親屬編》的規定──妻不再從夫居,居所由夫妻雙方約定,如約定不成則由法院裁定;離婚時,子女監護權不再歸夫,而是以子女利益為依歸等──然而性別平等這個「普世價值」是否已經徹底落實?判斷性別平等實踐的程度涉及許多問題。
首先,性別平等指涉的究竟是兩性享有「相同待遇」,或是「差別(優惠)待遇」?優惠某一性別的同時,是否會有「逆向歧視」的可能?最核心的問題也許在於:男女兩性之間究竟是「同」或「異」?
關於這些疑問,美國二十世紀下半葉女權運動的發展歷程或許是一個適切的例子。1972 年婦女運動爭取加入性別平權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 ERA),「里德訴里德案」(1971 Reed v. Reed)宣告愛荷華州規定遺產管理由男性優先的法律違憲。然而當時有些婦權運動人士反對提供女性優惠待遇,因為「優惠待遇」本身似乎就代表某種「不平等對待」。

在 1976 年關於雇主與雇員傷病保險的著名案例「通用電器公司對吉爾柏特案」(General Electric Company v. Gilbert)中,法院認為:雇主若將與懷孕相關的健康狀況排除於原本雇員可享有的失能給付計畫之外,也就是不將因懷孕相關傷病列入失能給付範圍之中並不是性別歧視,因為「懷孕本身」與「性別因素」無關,而將懷孕看成個人選擇的結果,因此依據懷孕因素所做出的差別待遇便不違反性別平等。這樣的結論自然引起各方面的反彈聲浪,有大法官在不同意見書當中表示,懷孕應當視為男女兩性最明顯的差異之一,因此應當屬於性別因素,根據性別因素所做出的差別待遇便是性別歧視。
然而,男女兩性究竟是「相同」還是「不同」?生理差異到什麼程度才是「異」?
關於這個問題,第一個會提到的應該就是懷孕與生產方面的性別差異。然而在其他的例子當中,差異則似乎沒有這麼明顯。以過去有陣子網友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上倡議女性也應當履行兵役義務的事件為例,該提案認為《兵役法》中僅規定男性當兵是某種性別不平等,國民義務不應當因為性別而有差別對待,因此女性也應該當兵。
這個提案引起了許多討論,值得注意的部分在於:如果女性因「生理差異」而無法履行兵役義務,那麼「哪些差異」才是與制度差別對待相關的差異?這些差異之中如何劃出界線?一方面,女性在體力上似乎確實無法與男性匹敵,因此在運動賽事中會分男女組別;但另一方面,不能否認也存在著身強力壯的女性與體力並不出色的男性。
許多人針對兵役制度與西方作比較,如以色列就是舉國皆兵不分男女;實際上我國也存在女性志願役制度,這是否表示就服兵役所需的能力而言,男女之間並沒有實質的性別差異?或者這只是表示:從「相同」或「相異」的角度來檢視平等與否,本身可能畫錯了重點。也就是說,男性與女性的相同或相異處本身不應該成為性別平等的重點,重點應當在於:兩性之中,是否有人在現存的制度或遊戲規則當中遭受壓迫,性別平等應著重在制定規則與參與話語權方面的平等。
一個相關的案例「普萊斯.瓦特豪斯對霍普金斯案」(Price Waterhouse v. Hopkins)極有啟發性。安.霍普金斯(Ann Hopkins)在會計事務所中表現出色,然而她申請成為合夥人卻遭到拒絕,安於是控告該會計事務所有性別歧視的嫌疑。該事務所否認,並解釋拒絕的原因在於其他同事認為安「個性太強硬,具侵略性又很難相處」,換句話說,在這個個案中,安.霍普金斯看似面臨一個兩難──一方面,為了在職場上表現良好,她個性強勢並果決,即「像個男人」;另一方面,她又因此無法獲得同事們的認同,因為安「不像個女人」。
然而,倘若我們深思這個「兩難」處境,著名的女性主義學者麥金儂(Catharine MacKinnon, 1946-)認為:重點不在於如何解決這個看似互斥的兩個標準(事業成功的標準是表現得像男性,被職場同事認同接受的標準是行為似女性),問題在於這兩個互斥的標準實際上都是由男性設下的「男性標準」。
作為女性的當事者,在這個既存標準與規則面前陷入了進退維谷的處境,但原因並不在於她的表現是否與男性同事「相同」或「不同」,而在於這個規則的制定過程中女性並沒有話語權,換言之,女性雇員在這個制度下遭受壓迫。
積極平權或逆向歧視?
面對原已遭受不平等的女性職場處境,很直覺的反應是在法規上給予特別保障,例如單身條款、禁孕條款在臺灣各行業中曾經相當普遍,認為女性雇員一旦結婚或懷孕便會增加雇主的成本,因此產生了這類的歧視條款。
目前我國的《性別工作平等法》保障女性的工作權,不僅限制前述的單身、禁孕條款,也增加協助女性育兒的相關規定,包括生理假、產假、流產假與育嬰假等,某種程度來說,這類法規似乎大幅減輕了因男性與女性之間的重大生理相異處所導致的職場負擔,然而政策上追求平等的舉措也引起一些雇主的抗議。讓我們思考以下這個事件:2017 年有一名懷孕媽媽在「新竹爆料公社」中指出被面試的上司在LINE訊息上口出惡言,引來網路上一片批評聲浪。
但值得注意的後續發展是,在著名的 BBS 站批踢踢實業坊上,有類似經驗的網友從不同角度提出了反思,貼文者自稱「奉行勞基法的覺青所轉職的魯蛇慣老闆」,在面試雇員時遇上一個孕婦,因為該雇員在面試時承諾可以負擔一般勞力工作,但在正式上工以後不僅經常請假,產前請假安胎,產後亦請育嬰假,因為法規緣故,老闆不能以懷孕因素在薪水待遇上差別待遇,否則屬於性別歧視,然而該雇員在六個月育嬰補助後,便以必須照顧家中嬰孩之故而辭職,貼文者的結論是:因為該雇員經常請假,所以老闆必須經常額外支出加班費以補充人手,一年下來粗估約損失十幾萬人事費用,對中小企業而言造成很大的負擔,換言之,政府追求性別平等的法規似乎導致了某些人的額外負擔。性別平等的提倡者應當如何回應這類事件呢?
值得注意的是,這樣一個事件在網路上引出了另一種對追求性別平等的批評,亦即認為:女性經常聲稱「男女平等」,應享受平等待遇,但唯有在對己有利的情況下才會強調女性與男性之不同(尤其關於女性懷孕或育兒方面),因此被批為「女權自助餐」,認為支持女權的人隨心所欲挑選他們所欲享受之優惠,如同在自助餐店挑選自己喜歡的菜色一樣。換句話說,號稱支持性別平等的「女權主義者們」,支持的只是對女性的特別優惠待遇,並非真心挑戰當前存在的不平等父權制度與文化。
這樣的批評衍生出另一個名詞「父權紅利」,意思是雖然女性在傳統父權文化下受到重重限制,並被要求符合父權眼光中「溫柔順從賢慧小女人」的形象;然而從另一方面來說,男性在這個對應的「堅強果斷大男人」形象之下,也承受不遑多讓的枷鎖與限制。
例如這個父權社會雖然重男輕女,然而通常也要求男性負起養家的責任,因此成年男性若是無法買車買房,擁有一定經濟資本,便會受到女性的輕視,被認為是失敗者;又因為男性被視為經濟上主要行為者,在男女生約會階段時,不論兩人經濟狀況孰優孰劣,均認為應當由男生付錢,否則便是不夠「紳士」;同時男性也被要求不能輕易表露情感,不能「如女性般」示弱。

主張女性獨享「父權紅利」的人批評:相對於被層層要求的男性,女性在父權文化中享有許多優待與權利,然而在號稱追求兩性平等的當代社會中,女性似乎只想取消傳統父權社會的義務與負擔,卻仍然要求保有傳統父權下享有的權利與優待,這樣的訴求對於被認為是優勢性別的男性是不公平的。
上述的批評是否合理?我們可以發現,儘管法規與日俱進,所謂追求性別平等的社會仍充斥平等假象──如女性參政比例偏低、婚後女性從職場消失等──更值得注意的是,前述這些男性所遭受的壓迫與不公平──所謂的提供父權紅利、女權自助餐──事實上也是來自於結構的壓迫。換句話說,正因為同一個壓迫女性的結構存在著不平等的規則,男性也遭受到相應的壓迫與不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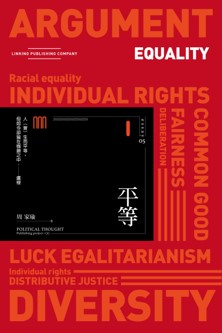
社會這柄天平兩端垂掛著極端立場,你我都必須選擇。
但要怎樣才能找到居中支點,真正走向平等、邁向共善呢?
平等可以保障所有人的權利,人人得以自平等受惠,是基礎而又普世、建構現代社會的必備條件,但為什麼我們總是在爭取、訴求平等?我們所處的社會,真的有迎來一切平等的可能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