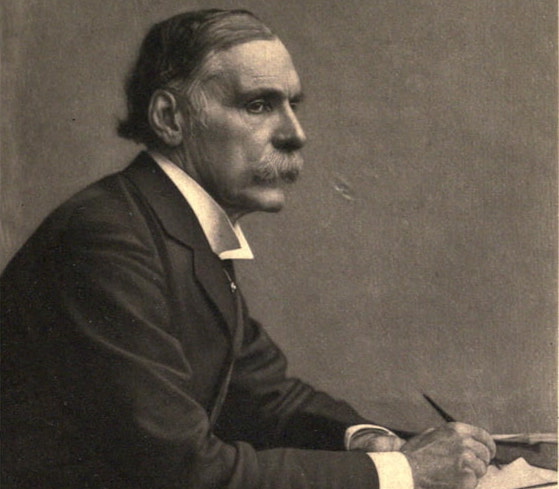這類小本經營的帶貨商人,從民國時期開始被稱為「水客」,他們主要在沿海地區活動,尤其是廣東地區,乘珠江及南中國海交通網絡之便,謀求生計。水客長期在海關低稅率的情況下(1842 年至 1930 年前),替旅居或僑居海外華人帶信送錢及貨物回鄉,並帶領商客到外地謀生。他們雖然只是一群寂寂無名的商人,卻無意間把外來的思想和貨品帶回家鄉,改變了粵港澳的社會面貌。
行走在如蜘蛛巢穴般交錯的貿易網絡上的水客
水客,亦稱作「巡城馬」,「巡城馬」與快遞有類似之意。水客一詞最早可見於晉代左思《蜀都賦》中的「試水客,艤輕舟」詩句,後來逐漸演變為專門到處採購貨物及替人帶信送款的商人。
水客以廣東水客最多,這與香港的發展有密切關係。19 世紀時,香港已成為全球名列前茅的貨物集散地 (Entrepot),當時中國超過一半的出口、超過三分之一的進口,都經由香港轉運。[2]日據期間,日軍南支總局對珠江三角洲曾一度有以下評價:
如蜘蛛的巢穴,又或如網孔般縱橫不斷地交錯流著的珠江三角洲地帶的水路,不僅是極奇特的地形;亦擁有異常的經濟價值。[3]
龐雜的水道網絡、大量各式各樣貨物的集散與供應,均是造就水客眾多的原因。此外,也出於珠江三角洲大量移民人口帶動的需求,水客活動便能跨越地域的限制,足跡遍佈世界各地。
水客的各項服務
水客除了帶信送款、帶貨回鄉鎖售之外[4],也會帶領商客來往各地,順道在商客的目的地採購貨物,其足跡遍踏整個南洋[5]。帶領商客時,南洋地區還依前目的地不同,對帶領商客的水客有不同稱呼,赴星洲(星新坡)者是「騎客」;赴緬甸者則原用水客一稱。雖同為帶領商客往南洋,但騎客與水客兩稱確有絲毫之別。騎客是旅店指定在輪船沿途招待乘客膳宿,任何人都可以擔任,而水客則需取得當地僑民及同鄉的信任,並持有特別證明才能擔任。
此外,水客另一重要服務應為輪船公司開拓客源及招股。例如在 1930 年世界經濟大蕭條之前,輪船業務競爭激烈,各公司都依賴水客代招搭客;四邑輪船公司招集股本時,亦依靠水客代為招股,各水客便以此為功,曾聯合起來向輪船公司領一牌照,每年納港銀 15 元給輪船公司,而公司方面則豁免他們船腳(即現今的船票或船費)。基本上,水客就是穿梭於各地域和水域的小商人,主要以個人經營為主,但他們與走私客有何分別呢?
水客和走私客,只有一線之隔
事實上,水客與走私客同樣是帶著貨品穿梭於各地,兩者的不同只差一線。
走私客通常是集團,以瞞騙或逃避納稅的方法私運外貨;而水客大多以個體為主,在商品免稅額度的範圍內,多次往返兩地,運帶貨品。雖然兩者目的相同,但手段大為不同。走私客是明確地逃稅犯法;水客則是利用法律的漏洞,從事買賣。
不過,水客的商業行為是否完全合法,則有待商榷。各地海關及郵政機構對個人攜帶的信件、款項及貨品都有限制。信件方面,香港政府規定信件必須貼上郵票 (郵票當時稱為「士擔」,STAMP 的音譯),不得私帶,否則會被罰款,因為郵票發售與營運經費。[6]而除此之外,二次大戰期間,為防止民眾傳遞消息,香港政府嚴厲執行禁止私帶書信,中國郵政局亦不許「巡城馬」私帶信件,如果被郵政局檢查員發現,即送警察局處理。
中共建國初期,廣州市郵局為了取締民間私帶廣州、內地與香港來往信件的「巡城馬」,阻止偷漏郵資等不法活動,在 1950 年 7 月 12 日成立郵件緝私組,會同市公安機關在各內河輪渡、碼頭、車站進行檢查,共查獲地下郵局 11 家,罰款 65 宗。從這例子得知,私帶信件在民國時期亦為普遍,但這是兩地的郵政局都不容許的事。
不只信件,當時香港政府對貨物及銀元進出口都有規定。乘客須在船上的艙單列明自己所攜帶物品,如果被發現無正當手續辦理的物品,會被沒收。但在 1934 年情況較為特別,當時受世界經濟大蕭條影響,香港政府體恤水客、小商人之血本,所以在出入口署向水客發還被沒收的銀兩,因為這些水客與香港的商務有密切關係,且中國內地尚未有匯款機構的地方,仍需要水客代勞。
根據《增訂中國旅行指南》所示,香港海關約在 1915 年已規定港埠酒及違禁品,切不可隨身帶入境;凡火柴及利器之物,以及新製衣服寇屐、書籍、地圖及有彩色之圖畫等,不可多帶。但事實上,不時出現水客因從內地帶私煙到香港而未納稅,於是被拘返中央警署及罰款的新聞報導。
換句話說,在各地方海關及郵政局的限制下,水客的生意規模不可能太大,即使是攜款帶信,也隨時會被沒收、罰款或被徵稅,他們只算得上是在法律中的灰色地帶謀求生存空間。



這裡便延伸出一個問題,像批信局這類用來處理通信、匯款業務的私人機構已經貫穿了亞洲經濟圈,但為何海外華僑仍把款項交託水客,而不採取更安全的滙款機構呢?原因有兩個。一、國內不是所有地方設有批信局;二、僑滙機構手續費高昂。這也是廣東省政府在 1940 年創立華僑匯款網的原因,希望減低華僑們的匯款手續費,減低華僑滙款成本,吸引華僑們資金。在這兩種情況下,水客於是應運而生。
無疑是高風險的生意
從事水客生意的風險其實不低,隨時有可能在入境中國的河道上遇劫,珠三角地區一帶尤為嚴峻。1928 年的《粵海關統計報告書》指出,廣東省內土匪風成熾,在這危機四伏的環境下,水客的貨物及金錢隨時會被劫。
曾有一名水客李氏,早上由香港乘輪船由香港返回廣東省,身上帶有現銀 (中央紙) 及代客攜帶之貨物,到達廣東省後轉偏電船 (汽油推動馬達的船隻),當時電船上有七人,駛至招商局碼頭附近海面,兩艘小艇駛至就搶劫了他們。不僅如此,生意的順利與否還取決於各地政府對關稅及關卡的態度,水客難以掌控,所謂今天不知明天事。
1930 年代中國海關的加稅政策
由 1928 年起,南京政府幾經波折,逐步實現奪回關稅主權。像是 1928 年與美國簽訂中美關稅條約,美國承認中國關稅主權;在 1930,與日本簽訂日中關稅協定等。中國海關總稅務司 (Inspector-General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IG of CMCS) 梅樂和 (Frederick Maze) 於 1929 年就任,亦與當時仍未知勝利與否的國民黨達成共識,停止委任外籍人士為海關職員,以換取海關能繼續為中國服務。[7]為了達到國家財政收支平衡、清理國家債務、保護國家經濟等目的,南京政府與各國 (包括:英、美、日) 簽訂協定或條約換取關稅增加,由過去 70 年 (由晚清海關始) 的一律 5% 增至 1929 年 8.5% (普通貨物),在 1936 年稅率更高到達 30% (普通貨物)。[8]
除了提高關稅外,中國海關亦刻意加強執法,專注於逃稅行為,防止糖、煙、棉等日常生活物資被偷運逃稅。1929 年前,中國海關人員只檢查貨物,對貨物徵稅,甚少向旅客個人行李內的常用物品徵稅。自從關稅提高後,即使是零碎雜物,如衣料等,因其稅額高達 1 元以上,故只要是攜帶皮箱、槓箱之旅客,亦須對其行李搜驗無遺。
例來說,1929 年前,海關人員甚少向旅客已裁剪的衣料或小量布疋課稅,加稅後凡足夠做一件衣服的碎衣料或新購的氈毯,即使是自用,亦常被要求納稅。因此,現在凡有托帶雜物者,多不敢代勞。

迫於生活只好轉型
大家可能會認為,關稅提高後,走私客應該會有相當程度的減少?實際上,正好相反,走私客活動自加稅後有增無減。正如梅樂和在 1933 年對中國海關加稅後之影響預測一般,部分水客在關稅大大提高後,加上海關嚴厲執法的情況下,轉為走私客。
當時的香港成為南中國的走私中心。一來是因為香港是自由港口;二來則是香港有治外法權,中國海關無法干預,最後一個原因則是,香港的生活用品的價格比中國境內低,部分商品價格相差可以很大。廣東省政府也抵受不住這商機,主動參與走私活動。
在 1934 年,廣東省政府主席陳濟棠派遣手下到香港,向香港太古煉糖有限公司 (Hong Kong Taikoo Sugar Refining Company Limited) 以每擔 8.4 元的價錢購入大批細砂糖,再用桅船運出。為了逃避南京政府的食糖進口稅,又改用緝私艦把太古白糖從珠江口運回廣州,再轉到番偶的新造糖廠卸貨。卸下後,即把太古砂糖換入蓋有「五羊牌新造糖廠出品」的商標的麻袋,每擔以 19 元出售。由於當時新造糖廠尚未建成,故有「無煙糖」之譏。
關稅提高後,許多水客轉為走私,原本的水客減少,輪船公司收益減少,導至香港江門輪船都計劃對水客船費減半,以增加客源。1936 年,來往省港各輪相繼加入減價競爭。[9] 除輪船外,內河船亦減低船費,以爭取客源。結果,各地失業農民遂出去廣東省、香港、江門作水客,被稱為「野雞式水客」。
當時的中國雖然在 1930 年初廢除部分稅項,像是子口稅(1931 年 1 月 1日廢除)、複進口稅(1931 年 1 月 1 日廢除)等,但在中國境內仍有不少稅項在 1930 年代中或更後時段才被停徵,如:統稅 (1935 年 10 月 1 日停徵)等,而最具爭議的厘金 [10] 則在民國時期內一直存留,因這關乎民國地方財政。因此,相對私人攜帶而言,貨物進出口的成本仍然高昂,而且在國內還有其他關卡,估計市場對水客應該仍有一定需求。

.jpg)

穿梭於法律灰色地帶的帶貨人
在歷史上,水客一度仿如「人肉」快遞般穿梭於各地法律的灰色地帶,不惜冒險,為顧客提供相對便宜的貨品及便利的服務。水客得以生存及發展,主要來自各地居民有信件、金錢及貨品運送的需求外,無疑與經濟不景氣、各地關稅高低、中國境內外的貨品價格差異以及船公司的資助有莫大關係。時移勢易,相信現今水貨客較少,甚至不再需要帶信及金錢,但所攜帶的貨物種類卻有增無減,繼續以螞蟻搬家的方式推動著貨物流轉。
歷史上的水客與當今水貨客最大分別,應該是在於所持的支援及工具。過去的水客主要靠自身的體力、人際關係以及船運公司的資助;當今的水貨客就是透過網路及資訊科技。網路的巨浪雖將不少實體店送進歷史,卻前所未有地擴大了水客生意的門徑,常常在網路平台上看到的代購,可以說是水客與網路的結合,再加上資訊科技,甚至發展成有組織的代購集團,能迅速地因應客人個別需求在全球搜羅貨品,不經中介、代理,直送到府上。
相信在 COVID-19 肆虐全球,各地封關的狀態下,對無法外遊人士來說,水客顯得特別重要。由於他們規模之大,不只是在香港,在世界各地都引起不同的迴響。如此來看,水貨客目前需要應付的不再是生存空間的問題,而是社會大眾的爭議。
[1] 例如:〈【1.5 上水遊行】水貨客問題上水蔓延粉嶺 上街居民促降旅客數目〉,載《HK01》,2020 年 1 月 5 日。網頁: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417880/1-5上水遊行-水貨客問題上水蔓延粉嶺-上街居民促降旅客數目
[2]https://storystudio.tw/article/gushi/guangdong-hongkong-macaogreaterbayarea/
[3] 南支総局資料室:《珠江デルタ実地調査報告》(昭和 18 年 6 月 5 日)。參考編號:C13032364800. 藏於支那-參考資料-129 (所蔵館: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4]《香港工商日報》(1932年11月3日)。
[5] 《香港工商日報》(1933年2月22日)。
[6] 《香港華字日報》(1918年11月19日)。
[7] Hans van de Ven, Breaking with the past : th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and the global origins of modernity in China(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218-219.
[8] 王爾文:《晚清商約外交》(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c1998),頁 270;《走向自立之路: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中國的關稅通貨政策和經濟發展》,頁 4,194;<粵海關民國 18 年華洋貿易統計報告書>,載《近代廣州口岸經濟社會概況》,頁 777。報告有以下記戴:「查民國 16、17 年間,海關進出口稅,凡從價貨物,系值百抽 5;從量貨物,則按進出口稅則徵收,按其貨值,亦約為值百抽 5。惟自民國 18 年 2 月 1 日起,土貨出口稅及土貨複進口稅,均加徵附加稅值百抽 2.5。洋貨進口,按照同日頒行之新進口稅則條例,加徵新增部分,由 2.5% 至 22.5% 不等。」
[9] 《香港華字日報》(1936 年 5 月 28 日)。
[10] 厘金:中國自清代至中華民國徵收的一種商業税﹐因其初定税率為 1 釐(1%)﹐故名厘金。又稱釐捐、厘金税。在全國通行後,不僅課税對象廣,税率在各地極不一致,且不限於百分之一。有的高達百分之二十以上。
- 久保亨著,王小嘉譯:《走向自立之路: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中國的關稅通貨政策和經濟發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2004)
- 天光報》。1930年代。
- 王爾文:《晚清商約外交》(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c1998)
- 《香港工商日報》。1930-1940年代。
- 《香港華字日報》。1910-1920年代。
-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編纂:《增訂中國旅行指南》(中國:商務印書館,1924?)
- 連浩鋈。<軍閥與商人:陳濟棠與廣東省糖商個案研究>。載《東方文化》(2005年6月),第39卷,第一期。
- 《越華報》。1930年代。
- 楊萬秀、鍾卓安主編。《廣州簡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
- 廣州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廣州市志‧卷四‧郵政志》(廣州:廣州出版社,1995-2000)
- 濱下武志著,朱蔭貴、歐陽菲譯:《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 南支総局資料室。《珠江デルタ実地調査報告》(昭和18年6月5日)。參考編號:C13032364800。藏於支那-參考資料-129 (所蔵館: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 Hans van de Ven, Breaking with the past : th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and the global origins of modernity in China(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4).
-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03-1950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