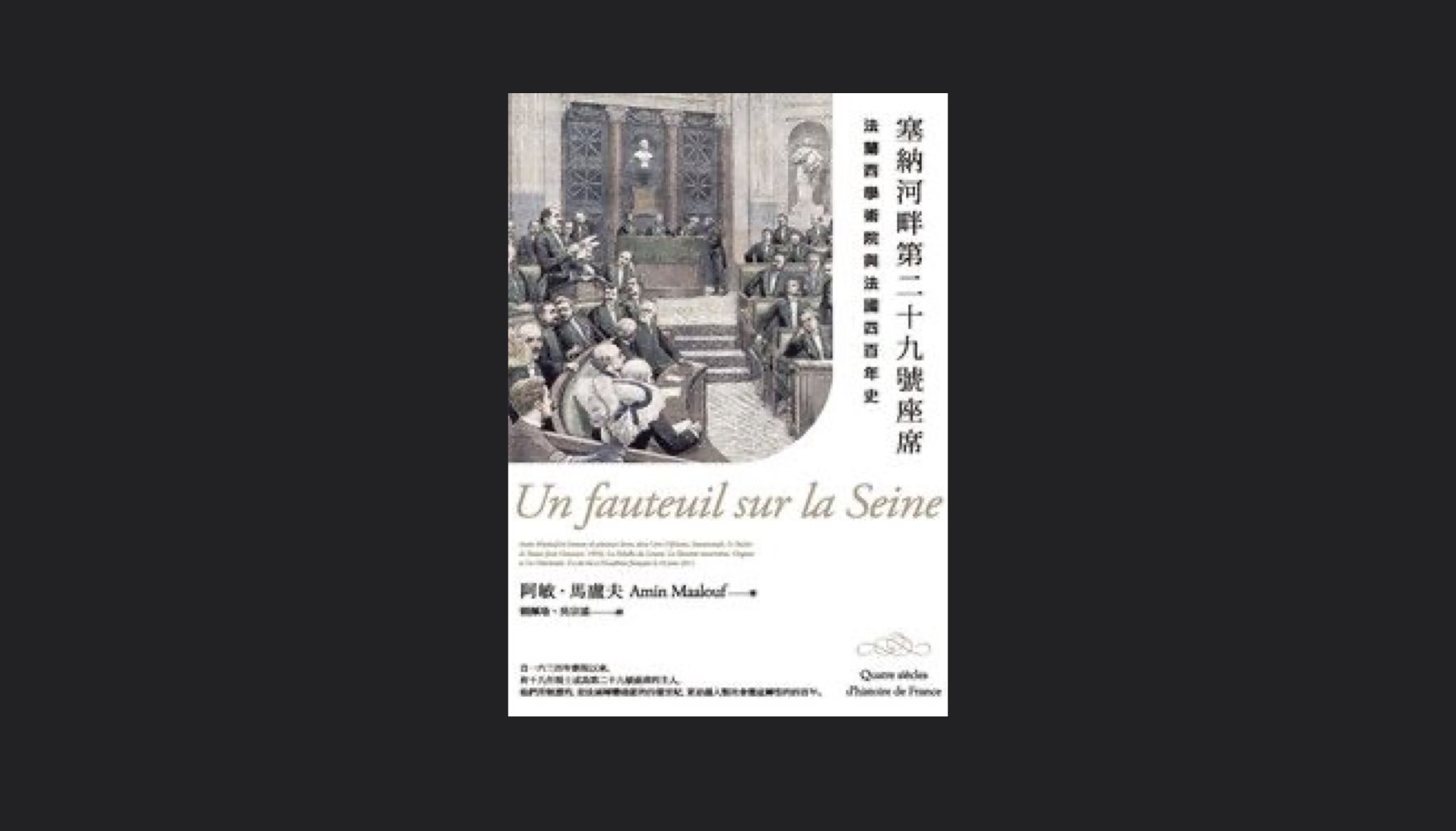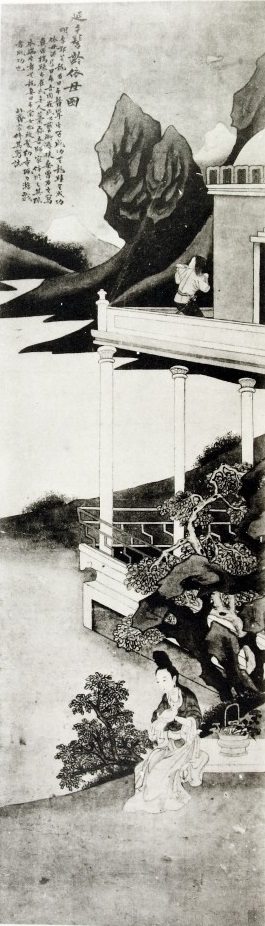試著追尋過去有著難以否認的好處。這裡說的不是歷史學科中,可能會提到的「邏輯思辯」或是「鑑古知來」等,那種有實用功能的理性事物,而是某種更接近人類本能與情感的東西:滿足好奇心。
對過去的好奇心,讓我們看清自己站在哪個時間或空間向度上,進而與過去連結,知曉這個世界並非充滿著虛無與巧合。無論意識形態、教育水平或階級地位,人類總是有意無意地藉由挖掘過去填補自己的疑惑,數千年來始終如此。
《塞納河畔第二十九號座席:法蘭西學術院與法國四百年史》(Un Fauteuil sur la Seine,以下簡稱《塞納河畔》)的作者阿敏・馬盧夫(Amin Maalauf),即為追尋過去的探索者之一。
法蘭西學術院(Académie française)是法國學術界的重要機構,自 17 世紀創設至今,多位法國最優秀的知識份子都曾為其中一員。按照傳統,當每位新進成員正式加入學術院時,都要為該席座位的前任已逝成員,發表一篇具有紀念性質的演說。
2011 年,阿敏・馬盧夫接替著名學者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坐上第二十九號座席。為了履行義務,他開始深入認識李維史陀的人生,並「好奇」地看看在李維史陀之前,更早一位院士的故事,然後再更往前下去。
馬盧夫最後發現,法國史上最聰明、最有貢獻,甚至是最有爭議的人,都曾坐過第二十九號座席。不過讓他最有感觸的是,這個過程使他與過往院士有了情感上的連結,即便彼此間完全沒有血緣關係,他說道:
這些人從此與我有著某種精神上的聯繫,我想好好認識他們;同時企盼當中有人帶給我的悸動,勘與我對(歷史學家)米修懷有的感情相比。我並未感到失望,一路走來不斷有新發現、驚喜連連,因此,我很快就決定,這部作品不僅獻給一人,而是獻予一整個傳承。
《塞納河畔》基本上是一部傳記形式的作品。全書共分十八個篇章,代表著曾坐在第二十九號座席的十八位前院士;十八段人生故事,共同串起法蘭西學術院的歷史,以及法國過去四百年來的發展。
法蘭西學術院在一開始,只是一群知識份子的私人秘密聚會,但當時的法國樞機主教,同時也是實質上的掌權者黎胥留(Armand Jean du Plessis de Richelieu)得知此事後,決定將其任命為官方正式機構。雖不甚情願,不過成員們考量到惹腦主教的可能下場後,還是向他獻上奉承的回應,法蘭西學術院自此正式誕生。

接下來的四個世紀,法蘭西學術院經歷了法國史上的各重大時期。像是路易十四的浮誇政治氣氛、路易十五的改革,而後動盪的法國大革命,或是 1870 年代高漲的國家主義,以及後來的兩次世界大戰和戰後重建。第二十九號座席的歷代成員不見得都是政府核心要員,但他們的人生故事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大時代的縮影與省思。
例如第十一世院士、歷史學者喬瑟夫・米修(Joseph Michaud, 1767-1839),本書作者形容他是「兩度被判死刑的人」。在大革命初期相當活耀、積極的米修雖認同自由主義,卻傾向於推動君主制,而非接受已然成為事實的共和制。在那個越來越激進的年代,光是如此便足以當作處刑理由。
後來,他在友人幫助下,很幸運地逃離政府追捕,親眼見證拿破崙時代的到來。不想繼續躲藏的米修,決定投身本來就相當感興趣的歷史研究。他不斷累積學術成果,最後以學者殊榮進入法蘭西學術院。直到今日,包括本書作者在內的許多研究者,仍受益於他的十字軍史相關研究。

另外,1879 年坐上第二十九號座席的十三世院士厄尼斯・赫農(Ernest Renan, 1823-1892),也反映了大時代的縮影,他必須正面回應民族主義者的期望。當時,法國正瀰漫在十年前慘敗給普魯士(後來的德意志帝國)的悲憤情緒中。他的接任致詞針對當時的低迷士氣,向全法國人民呼籲應該想起尚存於法國文化中的光榮、歡樂與自信元素。
他的思想充滿愛國精神,卻對那個時代的種族主義保持一定距離,如同他也說過:「一個國家的建立,不是因為講相同的語言,不是因為屬於同一個種族,而是在過去共同成就一份事,並希冀在未來能共同延續下去。」
但他一生中最出名的,也引來最多爭議的,還是他將耶穌視為人的作品《耶穌的人生》(La Vie Jesus, 1863)。赫農並不打算藉此顛覆基督宗教,也無意反對耶穌;他所做的只是用現代理性、科學方式重新檢討當時的文本和歷史背景,進而讓信仰不會在物質文明越來越昌盛的環境下,陷入毫無生氣的一攤死水。他的學術成就,見證了基督宗教在 19 世紀末時,與現代社會異常複雜的關係。

閱讀《塞納河畔》會發現,分析式的論述固然一再出現,尤其是法蘭西學院與整個法國在過去四百年的歷史,但作者最想表達的核心內容,始終是他所認識的前十八位院士,以及已然串聯起來的深層情感。不過這種相當個人性的情感卻不會過度矯情,因為作者一步步地隨時間推演,用著介於隨筆與學術之間的口吻,慢慢敘述出他認識的前任院士,情感真摯又不失親切。直到最後才借用李維史陀的說法,完整顯露自己的感受:
對每一位學院的成員來說,我們從此就嵌入一個連綿不斷、從三個世紀半前便開始構築的廣袤系譜中,我們將與之禍福與共。這讓每位坐於扶手椅上的人,都感到無比光榮。這是一部由沒有血緣關係的兄弟們,跨越時空,所構成的一部半虛構的系譜。
追尋過去,不僅使作者彰顯二十九號席座十八位前任成員的故事,也為他帶來出乎原先預料的滿足感。作者在本書最後一句話如此說道:「就在決心陳述這一切的瞬間,我才真正感覺到,這次終於輪到自己,安坐在這張扶手椅上了。」單獨視之,這句話平淡到沒有值得一提的地方,不過只要跟隨作者的文字經歷這段過去,就能品嘗到相當濃厚的餘韻,讓人由衷感到羨慕。